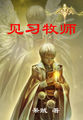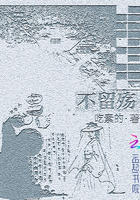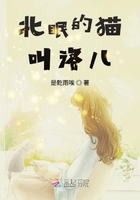但是,董仲舒在吸收百家之长基础上“独尊儒术”,就使得调和压倒了斗争。不过,一直到唐代,儒道佛之间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儒道佛三教的融会合一,从此不再争斗而专注于调和,是直到宋代才得以完成的。宋代的道士杜光庭说:“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各分别,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为尊,亦不以象教为异,亦不以儒宗为别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这就是说,儒、道、释是混而为一的,而且在真理面前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事实上,宋代以后的所谓“三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鲁迅在讲到“神魔小说”时说:“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凡有新派进来,虽然彼此目为外道,生些纷争,但一到认为同源,即无歧视之意,须俟后来另有别派,它们三家才又自称正道,再来攻击这非同源的异端。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出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神魔小说。”这种模糊的似是而非的信仰,不仅神魔小说中有,而且源自宋代的其他话本小说中也有。讲史话本《水浒传》中的那群“妖魔”,却变成了侠客(武松、石秀等)、和尚(鲁智深)、道士(公孙胜)。小说反复宣讲“三教同源”、“三教合一”,然而这个武士、儒生、和尚、道士能够和谐相处、精诚团结的啸聚山林的集团,却是一群劫富济贫、打家劫舍的绿林豪侠,他们都是从天上下凡的星星——天罡星和地煞星。如果要从宗教的角度看《水浒传》,那么无论你怎样费尽心机也难以将其中的宗教内涵说清楚。甚至对于鲜有宗教色彩的宋江,从文化承担的角度也难以解析明白,你说他是个儒家,他又具有仗义疏财、犯上作乱的侠客品行,你说他是个侠客,他后来又讲忠孝并为朝廷效力。因此,在《水浒传》中,是各种学派和宗教的含混不清的合一。即使是纯然出自文人手笔的小说如《红楼梦》中反复出现的“一僧一道”,也说明作者将僧与道看成是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当然,《红楼梦》中的佛家色彩是强烈的,但其道家意识也不难分析出来,而张毕来从贾宝玉对《四书》、孔、孟、程、朱的矛盾态度分析,认为贾宝玉的观点“并未跳出儒学的基本圈子”。
中国文人不以信仰为重而善于调和的心态,使得中国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也就是说,中国文人有时可以为家国社稷的兴亡而献身,但很少有人为一种主义、真理或信仰而献身的。就其优点而言,中国对于信仰问题历来都是持宽容态度的,来自异域的佛教能够在中国扎根,就是这种宽容态度的明证。但是,中国的宽容只是对于宽容者的宽容,而且还要有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而对于不宽容者以及可能煽动社会动乱者则采取一种不宽容人的态度,中国文人对于基督教的不宽容态度就是这样做的。
当然,当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初来中国时,是受到了一些中国文人欢迎的。其原因有三,第一,利玛窦等初到中国的传教士在对中国文化分析之后,认为要“归化中国”不可操之过急,不可在民间传教,而要在某种程度上向原始儒学认同,利用中国的上层文人自上而下地“归化中国”。所以他们只攻击佛、道和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明代后期一些厌恶理学的文人,致使信教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上层著名的士大夫。第二,初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为了能够在中国传教顺利、自觉地学习中国文化,而且由身着和尚服改换儒生服,使中国文人感到他们与“蛮夷”不同,而是一些“聪明特达之士”,譬如利玛窦,除了其渊博的西方学识之外,还熟读《四书》《五经》
并能够随时引用。第三,是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自鸣钟、望远镜等等,而且还帮助中国人修订历法、制造大炮,至于西方的数学、逻辑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科学,就更令中国文人耳目一新。因此,虽然大部分文人一开始对基督教就无好感,但对这些能够“立竿见影”的科学技术还是欢迎的。而且,即使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著名弟子徐光启、杨廷筠等中国文人,也不是什么纯正的基督徒。谢和耐指出:“徐光启所宣扬的并不是纯粹的基督教教理,而是一种儒教和基督教的大杂烩,与16世纪在儒教和佛教之间的混合物相类似。”
徐光启在为《秦西水法》一书所作的《序》中说:“余尝谓其教(基督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杨廷筠则试图调和儒、道、佛和基督教“四大宗教”,使之混而为一,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世界调和起来。因此,如果西方的传教士以徐光启、杨廷筠的方法来传播福音,那么,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首先关注的就是信仰。且听耶和华是怎样说的:“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若是不专一地信奉神,神会怎么办呢?“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其父必有其子”,耶稣也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而且“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甚至信徒与血亲也要生疏,因为“爱父母”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从亚伯拉罕欲杀子以奉神,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为人类赎罪,基督教开创了一种以献身殉道为至高美德的传统,基督徒以教堂是殉道者的血凝成的而自豪。因此,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刚刚落脚,就力排佛道,并猛烈攻击主宰当时中国的理学。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发其端,龙华民的《灵魂道体说》步其后,因此,尽管他们的中国弟子在接受上出现了“误读”,但是,这些传教士却是专一而不妥协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就表明了其决不妥协的立场,他坚持反对折中调和,并从逻辑的角度分析“三教合一”的谬误。利玛窦认为,或者三教均为伪宗,俱该抛弃,或者一真二伪,抛弃二伪,或者三教均为真宗,但在此情况下只信一宗就足够了。而后来的传教士连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也不讲了,他们不仅在民间传教,而且公然攻击儒学,甚至欲使中国的孔孟等圣贤坠入地狱,因为孔孟都是不信耶和华和耶稣的异教徒。即使传教士想以一种灵活而不放弃教义的策略方式来传教,也得不到罗马教皇的允许。教皇格勒门第十一多次召集各流学者进行研究考索,终觉儒家的“天”自然物质的成分太多,于是连儒家也成了异端邪说。在教皇的谕旨中,禁止中国的教徒敬天、祭天、祭孔否则即为异端。而这样一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末日就降临了。
虽然基督教对儒、道、释等“异教”的排斥和传教士的坚信精神使其在中国陷入了被排斥的“异端”之列,但是这种排斥并非来自民间。
在民间,中国老百姓对基督教的礼仪和圣像发生了极大兴趣,并以一种接受传统的迷信和巫术的方式加以接受,由此其信徒日益增加。
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的排斥主要来自中国文人和统治者。开始,中国文人以一种谨慎的态度看待基督教,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一教派与所有折中调和的教宗不同而以一种惟我独尊的执著态度出现于中国时,就竭力加以排斥了。《破邪集》是中国文人排斥基督教的真实纪录,而杨光先、许大受等中国文人则是反基督教的急先锋。特别是随着传教士在民间传教并以“巫术”赢得许多民众时,排斥基督教的声浪就更加高涨了。因为传教士以“妖术”惑众,就会煽动愚民而破坏国家的安定。于是,利玛窦想打通中国上层进行自上而下的传教没有成功,而中国文人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拆教堂、赶走传教士却成功了。到乾隆时代,由于私自入华传教者要被处以极刑,基督教在中国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中国文人自觉地向西方学习,西方的殉道精神和坚信精神也为一些中国文人所接受。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西方的坚信精神与中国民间的殉道精神结合之后,就获得了在本民族扎根的土壤。于是,李大钊从容就义,“左联”五烈士宁死不屈,瞿秋白用俄语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而红军也有那种“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但是,深一层看,中国文人即使在“五四”之后,也还是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信仰之上。这不同于民间的调和论,譬如民国时悟善社里的神主就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五块。这也不同于一些借学说以利己的文人,譬如鲁迅揭露的那种想求人帮助就标榜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想拿人东西就标榜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的文人。这里的意思是,即使那些让人坚信某种思想主义的文人,也还是认为之所以要坚信某种思想主义,就因为它能够兴国救民族。归根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与西方文人“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有很大差异。罗素说:“追求真理如其是全心全意的,就必须撇开道德方面考虑。我们事先不能知道真理在某个社会里会不会被认为是有建设性的。”
中国文人这种似信非信的信仰典型地表现出似是而非的宗教心态。中国文人对于神、鬼、来世、彼岸世界、天堂、地狱等等,几乎都是不排斥也不真的信从的,或者说,他们似乎相信一切,其结果又好像什么也不相信。因此,从根本上说,不是宗教的来世和彼岸世界,而是伦理的和审美的现世,才是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安栖地。由于执著于现世的伦理教化和经世致用,而又对于鬼神、来世无法证伪而采用了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所以中国文人对于任何来自民间和异域的宗教,几乎都采取了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只要“怪力乱神”不破坏儒家建构的伦理系统,并于经世致用有益,中国文人就会批判地从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中国文人的这种宗教心态其优点在于,中国文人和统治者对于宗教信仰有一种宽容的精神,不至于为了信仰去烧杀异端,也不会走火入魔去狂热地信奉什么东西,而是能够根据现世的利害对一切加以冷静的分析。因此,中国文人在排斥基督教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多少狂热,相反却对基督教的狂热不满,并加以排斥。然而,中国文人的这种宗教心态却有着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一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固然,坚信不移与谬论结合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真理往往是在谬误碰得头破血流后才会显现。人们现在都说布鲁诺宣扬的是真理,但是,布鲁诺为了坚信真理宁可被宗教裁判所的火烧死,不正是基督教坚信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吗?否则,在一种明哲保身的文化里,谁肯牺牲生命去换取真理呢?
(第六节)中国文人的想像力与宗教意识
翻开西方文学史,从但丁的《神曲》、雪莱的《伊斯兰的起义》、拜伦的《该隐》、歌德的《浮士德》,一直到叶芝的诗歌、萨特的《苍蝇》,无束无拘的庞大的想像力已成传统,而这一传统显然是与基督教有关的。向外,基督教的末世论或者说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使西方文人艺术想像的触角飞向天堂中玫瑰色的花环,像天使一般自由驰骋,或者飞向地狱,洞见种种怪异和罪恶;向内,基督教的善恶论外化为神与恶魔,并在人身上二分为灵魂和肉体,于是,人本身就成了神与恶魔的激烈战场。中国文学想像力不丰富,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学没有这种对彼岸世界的真诚向往,而是满足于此岸世界的身心合一。如果说这种比较涵盖整个中国文学尚有偏颇的话,那么,用来解释中国的文人文学则是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中国文人是在伦理和审美中求得超越的,所以中国文学基本上是执著现世而甚少世外之音,偏于儒家一派的文学就尤其如此。
儒家讲“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而不讲神魔等世外之音如何。因此,中国正统文人艺术想像的翅膀都落在现世事务上,如颂祝主人,媚悦豪富,感时忧国,伤春悲秋,悲慨世事,感怀前贤,亲朋赠答,天伦悲喜,故人别离,沙场征战,等等。
中国文人的想像力就感觉而言是相当敏锐,他们“遵四时而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他们对家国社稷的安危就更关注,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感时忧国的精神。但是,中国文人的想像力很少穿透时代,追求一种超越现世之变的无限绝对的永恒性,在苦难与救赎中表现具有本体意味的人性的罪恶和善良。
道家一派的文学想像力较儒家一派要丰富,特别是那些由道家而迷于仙道的中国文人,就更是如此。大诗人杜甫和李白,就分别代表着儒道文学之想像力的差异。杜甫执著现世,感时忧国,而李白想像的翅膀则上天入地,有时飘然遗世,飞向朦胧在仙气之中的蓬莱、昆仑。
《楚辞》想像力之丰富,是由于楚国国有的原始宗教、巫鬼文化尚未被中原文化的理性精神消融。不过,中国文化即使经过孔子的理性传述与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巫鬼文化的势力在中国民间还是很强大。这使得儒者虽“不语怪力乱神”,但民间的“怪力乱神”仍在满天飞。从《搜神记》到《聊斋志异》,鬼神故事仍活跃在中国文学中。当道教将远古的巫鬼文化、方仙之说以及道家哲学等等一并纳入其宗教武库的时候,与道教有关的中国文学之想像力就显得神奇瑰丽。而且道教的影响并不限于《封神演义》、《西游记》、《三遂平妖传》等神魔小说,对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亦影响甚巨。
不过,基督教文学庞大的想像力总具有深在的道德象征意味,而中国通俗文学中的想像力却没有道德意味,其眼花了乱的“怪力乱神”只是满足了中国百姓的神话心理,加之人们又并不当真以为存在那些鬼神,称作神话小说是再合适不过了。需要指出的是,神话小说有道教的影响,但佛教的影响亦甚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佛教的激发,单靠中国本土文化,产生这些神话的可能性就是一个疑问。
中国人执著现世,注重实用,中国文人的想像力也捆绑在实用的铅坠上不能起飞。梁启超之所以说《山海经》不是中国书,其实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是因为这本书怪异的想像力在他看来不是中华民族所有的。基于同一理由,陈寅恪赞同胡适的说法,认为孙悟空不是“国货”,而是由印度进口的:中国虽多猿猴故事,“然以吾国昔时社会心理,君臣之伦,神兽之界,分别至严。若绝无依藉,恐未必能联想及之”;而“印度人为最富于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话故事多起源于天竺”。
佛教对中国文人想像力的影响,是具有道德意味的,而并不仅限于神话心理的满足。明清的人情小说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这样一种叙述模式:先讲一个人怎样怎样好色,喜欢许多漂亮女人,其后悟到“色即是空”,然后出家当和尚。《续金瓶梅》第四十三回说:“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自果报,转入佛法。”事实上,《金瓶梅》本身也表现了这一叙述模式。西门庆爱潘金莲、李瓶儿等许多女性,并与之纵情恣性,小说结尾,西门庆的遗腹子孝哥明觉到自己是西门庆托生的,便看破红尘而皈依佛门。明代许多人情小说,如《肉蒲团》之类,采用的都是这种叙述模式。甚至清代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也不例外。贾宝玉爱黛玉、宝钗、袭人、晴雯、湘云等许多女孩子,但最终觉悟到“色即是空”,出家当了和尚。因此,虽然《红楼梦》与《金瓶梅》有重情与重肉的差别,但是其在佛教影响下所形成的叙述模式却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