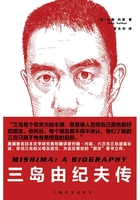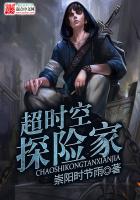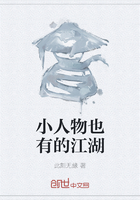再往城南走几趟,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这里是夫子庙和秦淮河,属于古都的细部,城市的细节在这里得以明晰地呈现。乍一看,无外乎是小桥、流水、人家。朱自清对“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极尽赞赏之能事,可是朱自清很假,他在浮夸。明眼人一打眼就知道,秦淮水从三四十年代就没清澈过,它不美,不配赞赏。客观地说,南京不算个旅游城市,人们来南京“旅游”,为的不是欣赏美景,而是怀旧。于点点滴滴之中,找寻这个城市两千多年来兴亡的痕迹,看着时间、历史、才子佳人……怎样从这城市浮现,消失,再浮现。它们留下了印迹,这印迹残留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这印迹躲在这城市的空气里。嗅一嗅,这空气里仿佛真有隐约的脂粉香,这香是李香君的香,是柳如是和马湘兰的香。
这城市如果有过繁华,多集中在这些娼女身上,她们体现着古都最物质、诗情的那一面。多少膏粱纨绔一掷千金,纸醉金迷;多少士大夫理想,随着末世的国都一点点地丧尽。
浆声灯影现在还有,只是不见旧“画舫”。现在的南京太过平淡,只剩下了古都的影子。这影子仿佛是假的,而从前是真的;其实从前也是假的。此情已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秦淮河附近,有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叫洪武路,这里曾经是南唐故宫的遗址。至于瑶光殿,红罗亭,现在也仅留下了名字——可正是这些地方,是才华绝代的李后主和大小周后恋爱过的地方。遥想后主当年,何等的富丽风雅,“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可是江山不久易主,连凭栏都由不得自己了。——沿着秦淮河畔走,于夫子庙的内脏有一条普通的巷子,窄而短而嘈杂,这是著名的乌衣巷。我第一次走进这巷子,不能相信这是乌衣巷,荒寂失落,可是想想也在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吧?
做为一个古城,南京两三千年来盛名不衰,除了断断续续的末代王朝在这里建都多而繁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缘于“词人凭吊吟咏,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倘说这是一个躺在线装书和旧诗词里的城市,倒也不为过。南京向来是风雅之地,适合文人骚客花前月下,弄些“轻浪萍花”、“断魂杨柳”等曼妙词句来,这一路的文风自然比不得汉唐之风,倒也纤巧哀伤,典型地体现了废都之风。南方文人多秀弱敏感,这是地气所致;一个文人哀伤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一个城市里,历代所有文人都哀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城市已形成了它的整体格调。
我不是个“历史癖”者,事实上,我对南京的历史知之甚少;所说的这点细枝末节,对于南京这个两千年来的“文明古都”,实在是沧海一粟。我也不敢附庸风雅,不过私下底确实以为,南京的历史味要多于它的风物美。
而现在的南京,老实平淡的日子遮住了过往的辉煌,这跌落是如此之大,好比从前是门庭若市,现在是朱门深锁。可是市民阶层不太去注意这些,他们永常地生活着,紧凑而安康,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任由自己往时间的深处迅速滑落。那过往的辉煌是如此满溢,一点一滴的常常从最不经意的地方漫出来;夕阳照在古街巷上,满地森森的树影子,人们不以为这也是从前的那个太阳;远古的风吹开了一户人家的窗户,在屋子里留下了沙尘,人们关上窗户,擦去风尘,继续吃饭。吃的是盐水鸭,茶泡饭,几根酱菜,一盘清炒芦蒿,
这是南京普通人家的生活,不感伤,不回忆,不期盼。他们不想知道这城市的历史,点点滴滴的细节——也不想知道,徒伤悲;也无从知道,因为他们也少读书。这才是真正的感伤,这个伤不疼痛,可它确实是一种伤,它潜藏在这个城市的血肉里,是麻木,无力,服从,是静静的一天天往前走的惯性生活。
第七章 街景;午夜里的露天小吃;卖报的男人;死;太平南路上的男人;贴身的南京
有一天,我走进宁海路的一条小巷,去看望一位女友。那是一条普通的巷子,沥青铺就的路面,也不是很宽。巷头有一截低矮的黄泥土墙,凭空地立在那儿,大约有很多年了;有几个老人就坐在这矮墙下晒太阳。
他们安静地坐在太阳底下,呈一字排开。他们大约正在交谈什么,说一些空洞的话。有的吃吃的笑出声来;有的呢,圆睁着眼睛,很吃惊的样子,又郑重地点点头,大约最终是弄明白了。
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八九十岁的样子,正在给旁边的一个老太太梳头,她把簪子衔在嘴里,一双手很麻利地把头发卷起来,盘成鬏,又直起身子认真地端详着。
有一个老年男子,坐在她们旁边,他把身体伏在膝盖上,头探出来看着。他在看她们梳头,脸上浮出隐约的笑容。他在笑什么呢?那一刻,他会想起什么呢?很多年前,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也常常看小姑娘编辫子吧?也常常会有这样的笑容吧?
这几乎是孩子气的笑,单纯的,茫然的,今生今世的。人老了,大约都会有这样的笑容吧?刚吃完了饱饭,脑子很空洞,人恹恹的,光只是想笑。这中间隔了成长,世故,肉体的衰老,琐碎的一生……从前的笑容又回来了。简单的思想,不多的一点回忆,人生中最紧要的那部分都被掠去了,单只剩下这酒足饭饱后的微笑。
我喜欢这微笑。
我后来常常把这一幕讲给许多人听,也不知为什么。我很愿意用照相机摄下这一幕,那鲜活的一瞬间里,所有明朗和麻痹的东西,所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那背后的东西。我想把画片的名字定做《南京》,或者叫做《市井》,或者叫做《生》。
我想它一定很美,因为这画面里有我所珍视的东西:老人,街巷,日常生活,正午的阳光,微小的影子……一切都是含糊的,带有寓意的,可又结结实实。
那些露天小吃只在晚上才出来,因为市容管理队下班了,没有人罚他们的款,砸他们的锅,追得他们满街乱跑。他们大多是些流动摊贩,没有卫生许可证,没有营业执照。这样的摊贩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夕阳西落的时候,他们像蚂蚁一样地出动了,拖家带口的,把锅碗瓢盆放在一辆破板车上,还有小电风箱,几张桌椅……总之,我猜想,那是他们的全部家什,除了床。
男人前面拉着车,女人后面推着。他们的身后或许还跟着个孩子,五、六岁的模样,是学龄前儿童,闲着没事,也跟出来帮忙。
他们大多是卖馄饨饺子的,炒凉皮米线的,烤羊肉串的,炸臭豆腐的。他们做的是小本生意,赚的是辛苦钱。“一天就二、三十块钱收入,也不容易,”有一次,我听见他们对市容管理队的人哀求着。也许他们是隐瞒了些数目的,总之,做这行的,虽不容易,也有他们的狡黠之处的。他们哀哀地笑着,以求得别人的同情。
那些市容管理队的,穿制服戴大盖帽的,他们可管不了这许多。他们操着纯正的南京话说:“我们是执行任务,啊是啊?你们不要让我们太为难。”也有的不由分说,就把他们的家什往卡车上搬的。
我还见过一次,那是在汉口路上,已近傍晚了,市容管理队突然来袭击,只听一声“警察来了”,所有的摊贩都抓起家当,夺路而逃。我在路边看着,虽是平常的一幕,可是在那仓惶的一瞬间,生的艰难,也自惊心动魂。
只有在午夜,他们才是安全的。城市安静了下来,人们都睡去了,他们在路灯底下摆起了夜摊小吃,几张桌椅,简单的家什,白钢筋锅里冒着水蒸汽;煤气烧得很旺,火苗像盛开的蓝菊花。
午夜的街头是那样的寂静,梧桐树的影子一片片地打在人行道上。有几辆出租车从路边驶过去了,还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影子在街头拉得很长。
我真是喜欢南京的午夜,因为有梧桐树,阔朗的街巷,少数不明身份的夜游人,还有夜摊小吃。是它们,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背景,让我觉得温暖,有所依托。我从这其间走过了,走了很远,还会回头看着,心里有小心翼翼的欢喜。有时候,走在午夜,随便看见一处风景,我就会放慢脚步,我知道那一刻的自己是谨慎的,认真的。我用手指点着,对朋友们说:“你们看……”
他们说:“你看见了什么?”
我说:“夜摊小吃。”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因为怀疑自己是有点小布尔乔亚的。我不能跟他们说,我看见了最底层的人们,他们艰难,奔波,动荡,可是在午夜的夜光下,他们是安宁的,有尊严的。他们端良地工作着,在某一瞬间,也许能感觉到幸福和茫然。我看见了生的明丽,在午夜,在艰难的外壳底下,于街头静静地盛开着。
我自己也常光顾夜摊小吃。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跟我说:“我对吃不讲究,可是一定得干净,舒服。”我以为自己没那么娇气。坐在午夜的街头,随便要一碗鲜肉馄饨,一块钱一碗,我吃着,心里没来由地感到温暖和踏实。
我看着身旁的摊主,一对中年夫妇,系着白围裙,一身干净利落的打扮。女人立在案边包饺子,男人弯腰到案洞里够着什么,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话。我猜想,他们一定也觉得温暖和踏实了。
我还看见了一个中年男子,从衣着上看不出身份来。他坐在隔壁的一张桌上,跷着腿,很自大地吩咐着:不要加香菜和辣油。这话他连说了两遍。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是穷人吗?他觉得无聊吗?他快乐吗?为什么深夜不回家,在深秋的街头,单单要一碗小馄饨?
我吃着馄饨,一边看路边的街景,也看着他们。有一瞬间,我几乎是埋下头,大口地吃着。汤汁的热气像雾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觉得自己快要哭了,然而没有。我只是平静地吃着,很平静地知道,我只是对他们充满了感情。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卖报的男人,那是在鼓楼广场,靠近丹凤街的一个十字路口。有很多车辆停在那儿,等绿灯通行。那个男人就穿行在这车队里,他拿着报纸一个车窗一个车窗地走过,大约也没人买,他总是很耐心地,探头张望一下,就走过了。
他看上去很年轻,大约有三十岁左右吧,戴着眼镜,穿着白衬衫,像读过书的样子;我总想着,他应该是公司的小职员,坐在空调房间里,为经理起草一份文件,或者很无聊的,坐在桌边翻看一本画册。
他卖的是《扬子晚报》,我很少看晚报,也绝少买;可是有一天深夜,我参加一个聚会回家,在路边等车时看见一个老人,在路灯光底下托着一撂报纸,用很纯正的南京话叫卖着,他说,扬子,还要扬子?
那是冬天了,已过凌晨,我还能记得;他穿着军大衣,棉围脖遮住了脸,单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那天他卖得不好,我猜想,数量还没有完成,所以刻意地选一个闹市区(也是鼓楼附近),非卖完不可。
我隔一些时间就要看看他,希望能有人买报,我也在犹豫着,是不是也去买一张,可是我不想被我廉价的同情心所左右,那是没用处的。我后来不再看他,一会也打车走了。
但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着,为自己;我偶尔买报,也愿意去那种有固定摊点的报亭,那样我觉得平等,看完报就扔了,也不觉得疼惜。
还有一次,是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卖报的男人(为什么都是男人在露头露脸),他的样子我不记得了。我坐在车末一排,看见他上来了,扶着把手,游走在人群里,也是轻轻地叫问着,可有人买扬子?从车头一直问到车尾,所有人都很冷漠的,也不看他,光只是想着心事,也有的说着话的,他的声音被淹没了。
就这样过了两三站,他就下了。
这一幕我曾在小说里描述过。
那时我还在上学,在汉口路附近租住了一间民房。我的邻居是一位老人,八十多了吧,从前是个捡破烂的。是个怪人,另一些邻居告诉我说,他年轻时就离了婚,有一双儿女,大约关系没处好,也极少来看他。
他住这里很多年了。屋子里很脏,光线暗淡。仅有的家什除了木板床,就是几张桌椅,还有一个煤炭炉,大约锅碗瓢盆也总还是有的。虽是身体羸弱,他也坚持每天清晨起床,生炉子做饭。看得出来,他做这些吃力得很,弯着腰,不停地咳嗽,把点燃的碎木片塞进煤洞里,满院子的青烟一团一团的,也有的跑进了他的眼睛里。他蹲下身子,很艰难地,拿手撑住地,另一只手遮住了眼睛,那样子就像在哭。
他很少出门。因为没有抽水马桶,他准备了一个塑料便盆,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把小便泼进门前的煤渣里。是个邋遢的老头子,虽然困顿,门前有尿臊味,可是我并不觉得嫌恶。
我也不愿意见到他,能躲由躲;他大约也意识到了,绝少和邻居们搭讪。他住在一个死角,每天从他的窗户里可以看见一部分青灰的天,也有成群的鸽子从低空下飞过,我知道,因为从我的窗户里,也能看见青灰的天和一群鸽子。
他是个尊严的老者,贫困,卑贱,一生默默无闻,老来病体缠身,气力从他的体内一点点地散发了,只剩下一具躯壳。对于这个世界,他是个累赘,他希望被忘却。
有一天,我在门前偶然碰上了他,他在燃炉子,侧过头来看我一眼,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我也笑了笑,便走进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