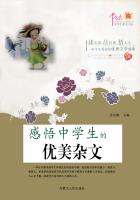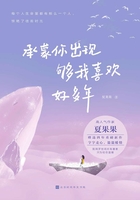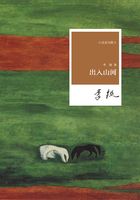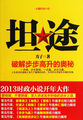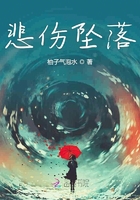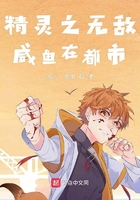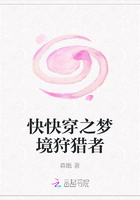上篇 大陆与台湾文学语言比较论
受不同历史语境的影响,大陆与台湾当代乡土小说的语言显示了明显的差异。受持续半个多世纪大众语运动的影响,大陆作家更重视语言的口语化、大众化,强调语言与生活的贴近与相似,希望用语言直接还原生活场景。台湾文学则更多地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传统,同时较多地受到方言的困扰,其语言与口语有较大距离,更多地凸显了书面语的特点,台湾乡土作家在开掘汉语书面语表现功能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第一节 历史语境的差异
20世纪初以来,大陆与台湾因为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其文学语言也显示了不同的特点。
与台湾相比,对大陆文学语言影响最大的是贯穿了大半个世纪的语言大众化运动。自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作家就开始倡导大众语,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左翼作家都参与并推进了这个过程。抗战爆发后,在延安和解放区,文学语言大众化的口号中渗入了很多政治诉求,赵树理、马烽等积极实践毛泽东在《讲话》中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略,语言被要求更多地口语化和大众化,人物对话被要求毕肖于大众的口语,过多地使用欧化语和文言则会受到严厉批评。1949年以后,语言大众化被作为“人民文学”的主要策略,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大众语运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有正与负两个方面。就其正面影响来说,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文学初期过分欧化的倾向,同时对克服“五四”以后新出现的“言”“文”分离的倾向、推动新文学的普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众语运动过多地迎合工农大众的欣赏趣味和审美要求、过度强调口语化则背离了由“五四”文学开启的文学语言向复杂、精密和诗化的发展道路,更多地拒绝了西文与文言的养分,使语言变得越来越浅俗、直白,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大陆文学语言也更多地选择了一条向低端发展的道路。
与大陆文学语言相比,20世纪台湾文学语言的演变则经历了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对台湾文学语言建设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20世纪前半叶它经历的从汉语到日语、再从日语到汉语的两次语言转换;这两次转换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台湾文学语言走向成熟的进程。日据时期,殖民当局一直蓄意通过对汉语的限制切断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如果说日据初期,殖民当局语言政策的实施尚不是十分得力,但是到了后半期,殖民当局对日语的推行逐渐加强,至“二战”结束,台湾日语普及率已达70%。1937年日本当局强令废止台湾报刊的汉文栏,其后,《台湾新民报》被禁止使用中文,而像《台湾新文学》这样的刊物则被迫停刊。
1945年台湾光复,其文学语言又经历了第二次转换。台湾文学回归汉语文学的母体自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这次语言转换还是造成语言传统的再次中断。日据时期有一些作家曾过度依赖日语,光复以后就几乎停止了创作。例如张文环光复前是“台湾文学的中坚作家”,光复以后,“一向用日文写惯了作品的他,蓦然如断臂将军,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得不将创作之笔束之高阁”[31]。光复以后,很多台湾作家都经历了一个重新学习祖国语言的过程。台湾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本来就不长,再经过两次深层次的语言转换,其语言建设的进程自然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1945年台湾的光复本来应当是两岸文学、语言交流的很好的契机,但是出于政治原因,国民党曾严禁阅读“五四”以后的大部分白话文作品,在两岸文学与语言的交流方面设置了很多障碍。台湾作家不能阅读“五四”以后优秀的白话文作品,对台湾文学语言的提高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诗人张香华说:“这一代台湾的诗人,面对一个事实,那是很不幸的,由于政治因素,在成长的期间,接触到中国大陆本土的新诗非常有限。因为根据当局的规定,凡是1949年,没有跟随国民党迁移到台湾,而仍留在中国大陆的作家作品,一律不准阅读。”[32]
与大陆文学相比,台湾文学语言建设还有一个不利的条件是它较多受到了方言的困扰。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陆与台湾在文学语言建设方面都曾受到方言问题的困扰,但是这个困扰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大陆有百分之七十属于官话区,就是说“言文一致”还是有比较广泛的基础。而台湾光复之前,除了少量原住民以外,主要语言为闽南话和客家话,而这种语言基础的差异给白话文的推广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20世纪20年代在张我军等倡导白话文时他们就受到了更多的质疑。1925年,陈福全在《白话文适用于台湾否》一文中就指出:台湾300多万的人口中,懂得官话的人万人难求其一,“如台湾之谓白话者”,“观之不能成文,读之不能成声,其故云何?盖以乡土音而杂以官话”。所以“苟欲白话之适用于台湾者,非先统一言语未由也”。[33]另外,台湾作家在学习和使用白话时也遇到了更多的问题。吴浊流曾感叹过学习白话新诗的难处:“余数年来对此(旧诗)怀疑抱憾,遂息吟哦,懒咏律绝之诗,思却转向已久,惟欲新体白话诗,奈不善中国原音,终难白话诗之奥妙,故日疏诗界。”[34]钟理和说:“我的国文又是无师自通,用客家音来读的,便是这二点使我后来的写作尝到许多无谓的苦恼,并使写出来的文字生硬而混乱。”[35]赖和曾谈到,他的创作往往是先以台湾话思考,再转换成白话文书写。[36]
台湾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环境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这个优势主要在于,台湾人口较少,近代以来,特别是光复以后经济实力快速提高,于是大众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这些条件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其次,虽然1949年以后台湾文学也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国民党当局试图把文学当作反共救国的工具,但是台湾的反共文学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也不是太深,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主发展。另外,当代台湾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交流比较多,这对推动台湾文学与语言的提高都是比较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 语言态度与策略的差异
因为社会与历史语境的不同,大陆与台湾当代乡土小说的语言显示了较大的差异,而这个差异主要是在作家的语言态度和策略上表现出来。
大陆作家对白话文的把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多年语言大众化的实践使很多人在语言的口语化、生活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们在语言上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自信;作家与语言亲密无间,于是他们在创作中就更倾向于直接表达自己的生活经验。然而,正是因为作家对语言的“熟”,在许多大陆作家看来,语言与生活似乎是同一个东西,人似乎可以透过语言直接把握生活,于是在很多人看来,熟悉生活就是熟悉语言,了解生活被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语言则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工具,因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语言的存在。
而台湾作家经历了50年的异族统治,白话文在日据时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光复后因为政治原因又有一个与大陆文学的阻隔,而且大部分作家还有着方言的障碍,因而很多台湾作家表现了对现代白话文的“生”。而这种“生”的结果是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语言的存在,意识到“语言”与“生活”的差异,因此更依赖语言,在创作中力图通过对语言的修饰和锤炼尽量准确表达自己的感觉与经验。大陆与台湾当代乡土作家这种在语言态度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在语言使用上的不同,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
1.大陆当代乡土作家更倾向于用生活化的口语直接还原某个生活场景,台湾作家则倾向于用描述性的语言转述某个场景。
王安忆曾拿自己的《小鲍庄》与宋泽莱的《打牛湳村》在叙事方式与叙事语言上做了一个比较,通过比较她认为:“大陆的小说具有人物演出的性质,叙事者与作品的人物是一体的,或者说,没有叙事者,只有人物在舞台上自行活动;台湾的小说则有明晰的叙事者身份,自始至终地与故事中人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客观地描写人物事件。”[37]
大陆乡土作家做出这种语言选择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很多年来,大陆文坛一直强调文学贴近生活,而文学最能贴近生活的方法就是让人物直接表演自己的故事。其次,这也与作家的语言态度有关。事实上,让人物“现身说法”对语言有更高的要求,作家必须高度熟悉某种语言,才能用语言想象人物的一颦一笑、一招一式。当代作家梁斌曾经用“擦得亮”来形容这种语言,就是说这种直接展示生活的语言必须具备明快、洗练和性格化强的特点。
而台湾乡土作家因为方言的限制,以及与白话文传统的隔膜,他们更倾向于用“讲述”的方式表现生活。所谓“讲述”,与让人物现身说法不同,它更多的是间接地把人物的故事讲出来,把人物的活动转换为讲述与叙事。使用这种方式其实是扬长避短,就是它既可以避免台湾作家在语言生活化方面的不足(人物的方言很难直接转换成相应的普通话),同时又可以通过对叙事语言的修饰、提炼,通过释放语言的能量,找到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方式,依靠叙述语言创造与大陆小说不同的叙事效果。
台湾乡土作家这个方面的探讨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宋泽莱的《打牛湳村》是台湾乡土小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小说的副标题是“笙仔和贵仔的传奇”,从题目看,它显然是一篇以塑造人物为主旨的作品。然而与大陆小说更倾向于让人物登场表演显示自己的性格不同,《打牛湳村》更多的是通过“介绍”说明主要人物的特点。在小说中,肖笙的特点是心宽体胖、对什么事都有傻乎乎的乐观;肖贵则是眼高手低,总是感叹世道黑暗与别人的低能,但他自己却也是一事无成,无论做什么都是以失败告终。然而在这篇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更多地都是被叙事人特别地指点出来的。小说开始,有相当篇幅是介绍肖笙、肖贵的家庭,他们姊妹四人各自的特点,作者甚至分1、2、3、4介绍了肖笙、肖贵在村子里显得不寻常的原因。从篇幅上说,直到三分之一以后,才开始进入“现在时”,让人物上场演绎自己的故事。但是在这个“现在时”中,作者仍然倾向于“讲述”。
王安忆在拿自己的《小鲍庄》与《打牛湳村》比较的时候就注意到,宋泽莱即便在“场景”描写时,也更倾向于讲述,即倾向于把事情的原委特别地指出来,而不是让人物现场表演。例如“瓜仔市风云”一节写的是肖笙卖瓜,这本来应当是肖笙的“现身说法”,但是在这段中作者用的也是说明与讲述。小说中有一个场面是,一辆游览车撞翻了一车梨仔瓜,于是农民与司机发生了矛盾,车辆堵塞,秩序大乱,警察过来干预。其后的描述是这样的:“有人熙攘起来了”,“便开手站在车前来挡住”,“警察开始挥动警棍”,“把车移到一边去,但又被旁的车挡住了,旁边的人又要移开”,等等。这段文字主要都是对人物行为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的动作,还有像“咒了三字经,还要他来赔偿”,也无具体的描述,只是一个内容提要。另外有一些比喻,像“车就像一只游不开浅水的大肚鱼”,“哨声像一支射人的箭”,“游览车上坐的人仿佛都是绅士小姐们”,则都是对对象作抽象的状态的描绘的比喻。大陆与台湾作家这种叙事态度的差异主要还是源自语言态度的差异,台湾作家要通过语言的雅化与技术化弥补生活化的不足。
当然,以“讲述”的方式表现生活是指台湾当代乡土小说的一种总体趋向,而不是说所有这类作品都采取这种方式。例如,王祯和就是一个努力用“展示”方式表现生活的作家。王祯和大学时代曾熟读西方现代派作品,对尤金·奥尼尔和田纳西·威利斯的戏剧更是情有独钟。于是他后来在创作中特别注意将戏剧的手法用于小说创作中。他说:“我觉得西洋戏剧中对人物、场景直接明快的表现手法是一般中国小说所最缺乏,也是我最想学的地方。”[38]他说:“我觉得小说的进行,最好是行动,而不是说明,只有行动才会深刻引入,说明常常是很无力的。”[39]
但是王祯和在实践“生活戏剧化”的主张时也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概括起来就是,他很难处理人物语言在方言与国语之间的转换;就是说,他在处理人物语言方面,面临着一个这样两难选择:在作家记忆中,那些乡间的小人物是讲着方言的一群人,如果让他们一出场就满口国语,会导致作家记忆和想象的严重失真;然而,如果作家做另一种选择,即基本保持自己的记忆,让人物出场后,满口方言,这样又会导致交流上的严重障碍。王祯和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基本采取了在人物口语中大量使用方言的策略,在《鬼·北风·人》、《快乐的人》,特别是在《嫁妆一牛车》中,他比较多地使用了方言俚语。例如,“干伊娘,给你爸滚出去”,“干伊祖父,我饲老鼠咬布袋”,“干……伊祖啊!向天公伯借胆了啦!”“三五不时地,阿好也造访姓简底寮。”等等。但是,大量使用方言一方面导致了交流的障碍;另外也产生了一种杂乱感。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将不同的语言掺杂在一起,产生的往往不是美感,而是生涩与混乱。因此,台湾批评家对王祯和的语言也有“国文不及格”的看法。[40]
事实上,王祯和面临的困境也是多数台湾当代乡土作家面临的一个普遍的困境,即因为方言与普通话的隔膜,作家的乡村记忆无法直接转换成一种普通话叙事,特别是人物语言无法实现从方言到普通话的直接转换;而这种转换的障碍,使他们不得不用“讲述”代替“展示”,更多地依靠“讲述”表现生活。
2.大陆当代乡土小说更倾向于使用口语,台湾小说则更多地使用书面语。
大陆当代乡土作家总是追求语言的生活化,即便是叙述语言也追求毕肖声口、让语言充满生活气息;评价语言的优劣也主要以是否像生活为标准。而对台湾当代乡土作家来说,与生活的相似不是他们最重要的追求,他们更重视语言独立的意义,有更强的语言意识,他们除了注重语言的清楚、明晰,还要求语言有味、耐咀嚼,给人以回味的余地;希望释放每一个词的魅力,让每一个汉字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台湾作家有更强的“修辞”意识,在表意上更多地依托于文字。
拿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语言做一个比较,能够看出,它们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大陆小说较倾向于使用灵动、明快的口语,而台湾小说更倾向于使用新奇、绚丽、意蕴丰厚、修辞意味特别强的书面语。李乔是台湾光复后乡土小说第二代作家,他的小说语言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台湾乡土小说重书面语的特点。其代表作《那棵鹿仔树》,写的是一个离乡多年的老人回到家乡以后的所见、所闻与所感。在这个小说中,李乔高度关注修辞的作用,尽量选择新奇、绚丽、具有陌生化特点的词语,力图用语言创造出风景画一样的乡村图景,为小说的怀旧主题提供良好的铺垫。小说起始,作者就从老人的视野写到家乡美丽的景物:
山,尖尖利利的,像倒过来的大锯子的齿,一棱一边,转直角,切一块,削一片,劈一刀;上面的树木桂竹林,密密团团的,像老母鹅肚底绒毛那样,葺葺蓬松。远看是淡蓝,再远是渗上淡紫,再过去就和天空接合着;走前去,是满眼青青黑黑,再前去,人自己也映印成青绿色的小点点。
这段话或写对象的形状或写颜色都力求新奇、准确;句子翻过来、倒过去,力求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观察对象。第一个复句中,两个分句都用了比喻:山像倒过来的大锯子的齿;树木、竹林像老母鹅肚底的绒毛。经过这样的描写,人物眼中的大山像一幅高清晰的图片被置于读者面前。
王安忆在分析《打牛湳村》的语言特点时指出,宋泽莱的小说特别有一种注重修辞,即语言技术化的倾向,他一直致力于“熟词生用、旧词新用,常有变通”[41]。王安忆注意到宋泽莱用这样的句子刻画肖笙的形象:“头上披着一丛金色细腻的头发,讲起话来也是细致的。”她认为:“丛”是指物聚集在一处的状态,往往用作草和灌木的形态或作为其量词,而在此修饰头发,是“取其抽象的规定意义”,“我们以‘丛’字出发,可清晰地想象那披在头上的发的形状,……”而作者用“细腻”描绘头发,用“细致”修饰讲话也都体现了熟词生用的特点。[42]
王安忆在拿自己的《小鲍庄》与《打牛湳村》做过比较以后指出,大陆与台湾小说在语言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大陆作家的小说往往能越过语言直接展示画面与人物的形象,而台湾作家的小说则是真正的语言创造意义上的小说,交给读者的是文字和语言,再由这些文字和语言告诉读者什么样的背景与什么样的故事以及什么样的人物。大陆的小说具有身临其境的画面感,而台湾小说则具阅读感。”“大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这口语因带有极强的地域特征,因此也更加方言化与俗语化;台湾小说语言则是汉语技术化,即是语文化或书面化。”[43]很多台湾当代乡土小说中甚至人物对话也有很强书面语化的特点。在《打牛湳村》中,一个梨仔瓜贩子在劝诱瓜农卖瓜时说:“一定有人的,比如有一些人自觉到种梨仔瓜没有意思,还会引起他的忧愁的,这种人干脆把田来交给我们办理。”这句话中,“比如有一些人自觉到……”应当不是口语的句子,像“忧愁的”也不像是口语词汇。肖贵在向妻子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时说的是:“阿凤,你不了解啊,你不了解。”阿凤给肖贵的回答是:“什么我不了解?”“我比你自己知道得更清楚。你总想当名人对不对,不愿来做俗人,别人能做的你就不做,故意抵抗别人,到头来你得到什么?你成了名啦!你是伟大的人啦!”在这段对话中,“你不了解啊,你不了解”根本不是一个农民的口吻,而“我比你自己知道得更清楚”等更不像一个农妇的话。
台湾乡土小说中人物语言的书面化本质上还是源自一种语言记忆的阻隔;很多作家的生活积淀是乡土的,如王祯和所说:“我是花莲人,从小在花莲长大,……我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那个时候印象深刻的人、事、物的累积”[44],然而因为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作家记忆中人物的言谈并不能移植到作品中来,当作家无法确定人物语言的用词、口气和语调时,只好选择书面语予以替代。
陈映真曾对大陆小说语言的“自然亲切”印象深刻;王安忆接触了台湾小说以后则感叹:“汉语能有那么多种多样的运用方法”,同时她也意识到:“我们已将汉语本身的功能忽略很久了。”[45]大陆与台湾文学是汉语文学的两个支流,因为历史语境的差异,它们分别开创了汉语文学语言的不同传统;这两种语言传统积累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以实现两者的互补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