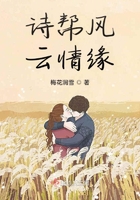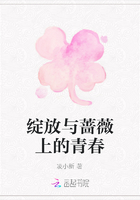以地域分今、古文经学的思想创自廖平。廖平在其代表著作《今古学考》中,以鲁学为今文经学,以燕赵学为古文经学,而以齐学为“参杂于今古之间”。他说:“鲁为今学正宗,燕赵为古学正宗。……齐学之参杂于今古之间。”蒙文通对此思想加以发展,并提出己见,而倡鲁、齐、晋之学。他说:
在这里,蒙文通把其师廖平所说的以燕赵学为古文经学的观点改为“古文乃梁、赵之学也”,而认为今文学来源于鲁学、齐学,是合鲁、齐之学而成;古文学依据三晋学而立,来自晋学,所以对今、古文经学均要超越,以复先秦齐、鲁、晋学之旧。他在《经学抉原》一书中具体作了论述:
今文之学源于齐、鲁,而古文之学源于梁、赵也。……古文之学来自梁、赵,孔氏学而杂以旧法世传之史,犹燕、齐之学,为孔氏学而杂以诸子百家之言,其离于孔氏之真一也。……井研先生以今学统乎王,古学帅乎霸,齐、鲁为今学,燕、赵为古学,详究论之,赵魏三晋为古学。……今文之学,合齐、鲁学而成者也,古文学据三晋学而立者也。今古学门户虽成立于汉,然齐、鲁以并进而渐合,晋学以独排而别行,则始于秦。言今、言古,终秦汉以后事,皆无当于晚周之旨也。
蒙文通发挥师说并加以一定的修正。廖平以鲁学为今文经学,以燕赵学为古文经学,齐学杂有今、古文经学。廖平这一以地域分今、古文经学的思想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他以齐鲁之地的鲁学、齐学为今文经学,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但以燕赵为古文经学之地,却少有根据。如燕人韩婴传《韩诗》,广川人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皆为今文经学。蒙文通将其师说“详究论之”, 而将“燕、赵为古学”,改为“赵魏三晋为古学”。这一改动虽与廖说有异,但却体现了蒙文通所主张的超越秦汉之后的今、古文学,直求晚周儒学之旨的思想。蒙文通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的思想,其重要目的还在于“由明经进而明道”,通过探明地域流传的儒学流派,来分辨孰为孔孟正宗、孔学嫡传,推本邹、鲁正学之宗以明道,修正齐、晋派及受其影响的汉人之今、古文经学“离失道本”的偏差。他说:“孟子是邹鲁的嫡派,他说的礼制都是和鲁学相发明的,《孟子》和《穀梁传》这两部书,真要算是鲁学的根本了。……孟子以后还有两个大儒,便是荀子、董子。荀子是三晋派的学问大家,董子又是齐派的大家,他们是齐、晋派里面讲孔学的特出者,但是于道之大源不免见得不很明白,便也是齐、晋两派不及邹鲁嫡派的地方。汉人的今文学是齐派占势力,古文学是晋派占势力,孔学的真义自然是表现不出来的了。也和《左传》、《公羊》杂取霸制,不及《穀梁》独得王道的一样。今文派是主《公羊》,古文派是主《左传》,这哪里还见得出什么王道来!”在弄清今、古文学的地域思想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超越今、古文学,复归孔学正宗,以明经学之道,这即是蒙文通当年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思想的重要目的。
蒙文通认为,鲁、齐、晋之学虽都是孔学的流派,但由于流传和地域文化特色的不同,其所形成的派别及其学派特征亦不同。其中“鲁学是六经的正宗,孔子的嫡派,是醇正谨守的”。而齐学则是孔子六经传到齐国稷下,与诸子百家之说相互混合所形成的流派。晋学则是孔子学说传到三晋,与三晋古史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流派。蒙文通借庄子对当时学术的分类,把鲁、齐、晋之学各自的学派特色作了一定的概括。他说:
庄子把当时的学术平行记述,分为三类:旧史为一类,《诗》、《书》、《礼》、《乐》为一类,百家为一类。《诗》、《书》自以邹鲁为嫡派,旧史恐怕就算三晋了,百家之学恐怕齐为最备了。是鲁学、齐学、晋学三派,就是《诗》、《书》和百家和古史三派了。邹鲁派的学术传到齐国,便和百家言淆混起来,于是便有齐学;邹鲁的学术转到三晋,便和古史派淆混起来,于是孔门便有晋学。孔子的学术,除一个嫡派鲁学外,又有两个支派,一个便是齐学,一个便是晋学,三派各有他们的本来面目,分户别门,真是离之则两美;到他们都与孔学混合,古史、百家二派便渐渐的湮没,孔经的本来面目亦被他们混乱,便分争不休,这真是合之则两伤。齐人百家言与孔学淆混便成了齐学,后来齐学又和鲁学结合起来。
由此可见,蒙文通倡鲁、齐、晋之学,是以鲁学为正宗,为谨守孔子思想的嫡派;而齐学则与诸子百家之学混合起来,齐学和晋学一起构成孔子学术的“两个支派”。“鲁学是谨守师传的,齐学是杂取异义的,齐学自然不及鲁学醇了”。齐、鲁两派的不同特色是,“鲁学是谨守旧义的,齐学是博采杂说的,一个纯笃,一个浮夸,这便是他们的大区辨了。”鲁学的醇正与齐学的驳杂形成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蒙文通认为,齐学之所以驳杂,是因为齐为百家所聚萃,齐学涵盖了诸子之学,儒学仅其一,齐学在来源上并不仅为孔子之学,而是包括了百家。他说:
言六艺者,鲁人之学,非齐人之学也。以稷下先生考之,齐人之学,本以诸子为最盛。孔氏之徒,孟子、孙卿之列,偶有厕身其间者而已。《史记》言:“齐自威王、宣王之时,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髠、接予、田骈、慎到、環渊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不治而议论,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则齐学尊百家言可决也。考稷下先生之可见者约十数人,以司马谈所列六家分隶之,曰邹衍、邹奭,此阴阳家也;曰孟子、荀卿,此儒家也;曰宋钘,墨家也;曰尹文,名家也;曰慎到、田骈,此法家也;曰接予、環渊,此道家也。惟田巴、徐劫、持说不可知,儒家鲁连、名家兒说,亦在稷下。明齐学备六家,而儒其一耳。孟子为卿于齐,荀卿三为祭酒,郑氏《书赞》谓:“先师棘下生亦崇此学。”孔氏之学,于时遂流入于齐,别为齐学,与鲁人六艺之学有别。
蒙文通对稷下学者加以考察,指出其中的邹衍、邹奭为阴阳家;孟子、荀卿为儒家;宋钘为墨家;尹文为名家;慎到、田骈为法家;接予、環渊为道家。可见齐学备六家,而非儒学之一家。在这里,蒙文通一方面认为孔子之学流入于齐,为齐学,齐学是孔子学术的一个“支派”;另一方面又认为,齐学涵盖了诸子之学,而儒学仅是其中的一派,齐学在来源上并不仅为孔子之学。这两种看法似乎有些矛盾。然而蒙文通是站在整个先秦、秦汉文化的角度来讲齐学、鲁学的。齐学是诸子学的聚萃,儒学仅其一,其所谓齐学并不单纯是儒学、儒家经学之一派,而是诸子之学。把诸子之学的齐学与作为孔学“支派”的齐学相提并论,由此与作为孔学正宗的鲁学形成对比。这是从更大的视野讲广义的经学。
蒙文通认为,孔子学术的另一个支派便是晋学。晋学的特点是与古史派混淆起来,其原因在于“晋国的学问,根本是古史,孔子的弟子后学如像子夏、李克、吴起一般人,都显重于魏,孔子的学问自然也就传到魏去。在这里,二者便化合起来,这一派的孔学,便又不是纯正的孔学,孔子的学问里边混入了许多古史的说法。其实,孔氏之学是和古史不同的”。也就是说,邹鲁派的学术传到三晋,与古史派混淆而成为晋学。与今文学为糅合齐、鲁两学而成不同,古文学则是依据三晋学而立。他说:“今文之学,合齐、鲁学而成者也,古文学据三晋学而立者也。今古学门户虽成立于汉,然齐、鲁以并进而渐合,晋学以独排而别行,则始于秦。言今、言古,终秦汉以后事,皆无当于晚周之旨也。”认为今、古文学之分,是秦汉以后的事,而齐、鲁、晋之学则是晚周流行的学派,所以对今、古文学均要超越,以复先秦齐、鲁、晋学之旧。晋、鲁之学的区别在于,“三晋以史学为正宗,鲁人以经学为正宗”。以重视史学与重视经学把晋、鲁之学区别开来。齐、鲁、晋三学相比较,“齐人之学,尚与鲁近,而晋、楚乃绝异也。此秦、汉之并取齐、鲁,而独排他方者耶?”认为尽管齐、鲁之学也有不同,但两学尚比较接近,而与晋、楚之学则相差甚远。所以这也是在秦汉之时,并取齐、鲁之学而排斥古文晋学及其他学派的原因。由此,蒙文通叙述了晋学在秦汉时遭排斥的情形。他说:
今文一派,是从秦起的。秦始皇最排斥的是那一派呢?……这样看来,始皇最疾恶的是《周官》,是古史的一派,就是最排斥的是三晋派。《诗》、《书》、百家语,秦是不曾焚的。汉时传于民间的古学一派,便是始皇所最排斥的那一派。今、古两派之分,就是从始皇起的,汉朝不过是随着他来罢了。讲今学、讲古学,是汉人的说法,是秦以后的说法,是讲不到六国时的。因为汉学的根本只是沿着秦而来的:六国的学术,只有汉初诸王那里还有些,但是都被朝廷压抑下去了。三晋一派古史的学术,河间献王那里尽有,他还立了《左氏》、《毛诗》博士。到献王遭武帝忌刻忧死以后,毛公、贯公这批人也就散在民间,《周官》一派的书,也就没人传习了。
认为秦始皇最疾恶就是三晋古史一派,对其代表作《周官》加以排斥。而汉朝对流传于民间的晋学古文的排斥也是继承了秦始皇。并认为今、古文两派之分,从秦始皇就有了,汉代讲今、古文学的对立,也是随着他而来,以致《周官》古文派的书无人传习。不仅秦始皇排斥晋学,而且蒙文通也认为“三晋的学问正是和孔子背道而驰的”。蒙文通关于今、古文两派之分及今、古文经学的对立始于秦始皇的说法,与学术界在此问题上一般认为的观点有异。学术界一般认为,在西汉末以前,并无所谓今、古文之争的问题。到了西汉末,刘歆才提出“古文”一词。与“今文”相对应,于是有了今、古文经学之争。西汉学者治经,以今文为主,即使东汉初所立的十四博士,也均属今文。而古文经学所依据之古文经书在西汉时,藏于秘府,少有人知,亦说阴行于民间,其后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秘书,才得以传出,依据这些古文典籍,才形成古文经学。这一见解与蒙文通的说法存在着差异。
不仅如此,蒙文通还提到了汉代很受尊崇的学术是申公、穆生一批经学家,枚乘、邹阳一批辞赋家和道家,却不提最受尊崇的董仲舒的齐学。他说:“当时的学术,只有在楚的申公、穆生一批经学家,和在吴梁的枚乘、邹阳一批辞赋家和道家,这几派很受汉朝的尊崇。在汉一代,只有他们是很盛的,别的学术都一齐绝灭了。”这里提到的申公为西汉今文诗学《鲁诗》学的开创者,鲁人,受学于齐人浮丘伯,后任楚王太子刘戊师,戊不好学,恨申公。刘戊为楚王后,申公遭腐刑。申公归鲁,以《诗经》故训教授学者。其弟子王臧、赵馆被窦太后逼自杀。申公亦病免归。其弟子为博士者多人,唯江公能尽传其学。虽然申公在当时影响较大,受到一定的尊崇,但蒙文通却不提更受尊崇的董仲舒及其《公羊春秋》学,或是认为鲁学比齐学更为纯正。
蒙文通对鲁学、齐学的划分,不限于传经者是否为齐、鲁之士,而以治学旨趣来区分。他说:“齐、鲁治学,态度各殊,《公羊》、《穀梁》、《易》、《书》之学,在汉传之者非特齐鲁之士,盖以合于齐人旨趣者谓之齐学,合于鲁人旨趣者谓之鲁学,固不限于汉师之属齐、属鲁也。”以治学态度、旨趣来区别齐、鲁之学。这个治学旨趣在蒙文通看来,即是齐学杂取异义,而鲁学笃守师传,齐学不如鲁学之纯正。蒙文通自认为,他的这一划分是与近代讲经的先生不同。他说:“齐学、鲁学的划分,我上面所说很和近代讲经的先生们大不同。他们的划分虽然各人不同,但大都是根据汉初经师是某地域的人来分划的,但完全这样分却未必得当。……任他哪一种学问,从六国传到汉初,没有不经过几国人的手的。我辨别齐鲁学是从他学问起源的地域分,根据他的主义来分,而不问在汉初是某国人传出来的。”这是以学问起源的地域与其主义的性质相结合来划分齐学和鲁学,既不完全取决于地域,也不是不讲地域,而是以该学术的旨趣、主义来自于何地,来认定其学为何学。
蒙文通在经学研究中,倡鲁、齐、晋之学,根据各派所传之学的源流地域及治学旨趣来探讨和划分鲁、齐、晋学的性质、特点及相互关系,这对于丰富经学发展史的研究内容,拓宽研究领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三)内学
所谓内学,指谶纬之学的别称。谶纬之书多有图画,故又称图谶。谶和纬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所区别。谶和纬虽分别产生较早,但谶纬之学作为一种儒学与神学相结合的学术思潮形成于西汉末年。内学的产生及其影响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谶作为一种宗教迷信预言,源起于秦汉之际,当时的方士不断造作谶语,以“预示吉凶”,然其言简短不成文。至西汉成哀之际,出现谶书的造作,其后王莽、刘秀、公孙述各自制作谶书、谶语,为自己夺天下制造舆论。由于汉代盛行天人感应说,谶托名天意,因而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纬相对于经而言,是用谶的宗教神学来解释附会儒家经典。受谶的影响,儒家学者托名孔子,制造与谶相类的纬书而出现在西汉。东汉光武帝时又编成《七经纬》三十六篇,以谶纬都出自孔子,提高纬书的地位,并诏令天下,成为内学,盛极一时,其地位有超出经学之上的趋势。纬书地位的提高,与西汉统治者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书的地位大为提高有关。于是,神化孔子和经书,附会经义的纬书也应运而生。
蒙文通对纬书虽不完全排斥,并时有所征引,但对谶纬之内学也作了认真考察,在他的重要经学著述《经学抉原》中专辟“内学”一节,提纲挈领作了论述,并探讨了谶纬之学对经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见其对在经学发展史上与经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谶纬之学的重视。
蒙文通认为,内学之所由立,与汉师传经时并传灾异之说有关,而灾变说自董仲舒始言。他说:“经师而言灾变,自仲舒始也。……汉师传经,虽并传灾异五行之说,经则遍授弟子,灾变实不以遍授弟子,故仲舒箸论,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此固内学之名所由立也。”所谓灾异之说,指天通过发生特异的自然现象,如水灾、地震、日月食等,对人示警或惩罚。即上天对人,经常通过自然界的灾异变化来进行谴责,以示警告,使其符合天意。灾异说通过迷信的方式把本不相干的自然灾变与社会人事混为一谈,以说明天与人事有着必然的联系。灾异说与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说相关。蒙文通指出,汉师传经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所有的弟子都传经,二是在对所有弟子传经的同时,只对部分弟子传灾异之说,故有的弟子并不知道其师还另传有灾异说。就灾异说只是对部分弟子传授而言,称之为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