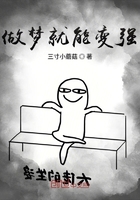袁敏
当我哥哥从被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第一次劫难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帮造反派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这个字眼。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打上鲜红的大字,挂在墙上的那部黑色老式电话机被掐断了电线,话筒拖着电线耷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的父亲突然间就变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绍兴话和自己干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做长篇报告并博得阵阵掌声的母亲,为什么一夜间就沦为了“假党员”?但很奇怪,那时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面对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兴奋。
然而,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那样的恐惧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时一瞬间从后脊梁上蹿上来的。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还叫我们不要紧张。但他们抄家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让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我们解释抄家的缘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绍信和他们身上威严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们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亲被从家中带走后紧接着就进行的,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和征兆。“****”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击****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来找父亲的人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父亲没有任何怀疑,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我想,父亲一定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一定想当然地认为组织部找他谈话也许和他久久的等待有关。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父亲当时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出门时,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父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母亲感到不安。母亲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觉得这么热的天却要父亲带一件外套很不正常。
我安慰母亲,叫她不要神经过敏,但事实马上证明母亲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我远远无法企及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到晒台上,从那儿我们清楚地看到楼下路口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父亲上车时回头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当年同样也是老地下党员的他是否这时也意识到这次离家也许就回不来了,但我相信他这一回头一定是在寻找我和母亲,他想应该要和我们告别一下。
抄家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抄家者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母亲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敌人往往想不到的。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乎乎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生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讯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从1月8日周总理去世,到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为周总理的灵车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谁都感到了一种压抑已久、火山即将爆发的潜流。那一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时刻关注着天安门的动向。我断定我哥哥一定穿梭在天安门的人群中,我的心终日里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宁。4月5日晚上9点30分,开始了对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的镇压,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也开始了。
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显然有别于1967年夏天造反派虚张声势的抄家,它是一种更官方的行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母亲始终沉默着,冷眼看着凌乱不堪、像遭强盗抢劫一般的家,始终没有问抄家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丈夫被从家中带走、抄家的规模及其深入仔细的程度、儿子出门近三个月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这一切,其中的勾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严重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位当年穿行在我党浙东交通线上的老地下工作者曾经经历过太多的风霜血剑,面对这样的搜查,你从她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青年女工,抄家的这天我正好应该上中班。望着家里一片狼藉的样子,我不忍心离开因心脏病和腹水而刚从“五七干校”被送回家治病的母亲。母亲平静地要求我去工厂上班,我说:“我可以请假,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放心得下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呢?起码也要等姐姐下班回家陪着你我才能走。”(我姐当时已从插队的东北病退回杭,在一家炼油厂当搬运工。)母亲不同意,固执地将我送到楼梯口,还说:“没事怎么好请假呢?”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从来不肯因为私事而耽误工作。我只好忐忑不安地上班去了。走出家门时我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小楼,小楼上绿色的布窗帘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扑到窗外。我哪里想得到,就在我走后不久,下班回家的姐姐,也被那些便衣警察以“谈谈”的名义从家中带走了,而且带走后和父亲一样从此杳无音讯。
上班后,师傅问我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我摇摇头说没什么。
好不容易熬到深夜11点下班,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夜宵,而是径直回到宿舍蒙头就睡。当同室女工吃完夜宵回来,三三两两地上床睡觉,宿舍开始安静下来时,我依然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我总觉得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没过一会儿,门外就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袁敏住哪个房间?”
“袁敏下中班后有没有离开工厂?”
……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我知道事情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
宿舍的门被重重地推开,门外走廊上的灯和屋里的灯被同时打亮,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穿好衣服,撩开帐子,从上铺爬下来,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白警服、红领章、大盖帽。我什么也没说就跟他们走出宿舍,我知道外面一定会有一辆警车等着我,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依旧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经历了“****”中的种种遭遇,我也已经习惯于不问为什么了。
果然,在花草如茵的厂部庭院里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和带父亲走的那辆一模一样。闻讯从各个宿舍赶来的工人们把吉普车团团围住,和我一个车间的师傅们挤在最前面。我那身材矮小的师傅钟凤英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和不解:“袁敏,他们为什么要抓你?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走?你一个刚刚满师的学徒工能犯什么法?”
我看着师傅满脸焦急和惊恐的模样,看着越围越多的工人们拦住警察不让他们带走我的阵势,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说实话,自从我高中毕业分配到这个工厂,我从来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人生的新起点,我总觉得自己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不定哪天我就会远走高飞。面对那些对我们这批高中生充满殷切期望的工人师傅们,我的心总是游离在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然而,这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心和他们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对我的关爱让我热泪盈眶、刻骨铭心。
吉普车驶出工厂大门的时候,漆黑的夜空中落下了丝丝细雨,我看到钟师傅一直追着吉普车喊:“袁敏……回来……”她那花白的头发被夜风轻轻吹起,抚慰着我惊悸的心。
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母亲没有睡觉,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坐着等我姐姐回家。看到我,她很惊讶地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没有说话,回头看那两个公安人员。送我回家的两名公安人员都姓陈,一名瘦小的要年长一些,态度和蔼,但目光很锐利;年轻些的那一名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但对我们的态度也同样和颜悦色。
他们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说了一些话。事隔三十年,我已记不清文件的具体内容和他们说的原话,但有两个关键词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是“总理遗言”;一个是“保护性审查”。这是两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这两个名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但只要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恐怕只要一看到这两个专有名词,都会被唤起久远的记忆。
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还牵涉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学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儿的父亲,杭州第一医院的院长;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年长的陈公安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到工厂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顾你妈妈。工资照发。”年轻的陈公安告诉我:“你姐姐是我见过的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假如不是你姐姐对我们说,你妈妈有心脏病,要是我们不把你接回来照顾你妈妈,她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那么我们就不会连夜到厂里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亲,我们对你姐姐是有承诺的。”
我没有说话,无论对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陈公安,我心中都充满了敌意,我不会因为他们把我接回家中照顾我妈妈就对他们感激涕零。我姐姐是我心目中最美丽最善良最心软的女人,怎么在陈公安眼里就变成了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
陈公安们走后,我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浮肿的手紧紧握着一块被竹花绷绷着的淡粉红的的确良布,一根深棕色的丝线垂挂下来,线头上吊着一根亮晶晶的针。
母亲告诉我,这是我姐姐被带走前正在绣的一对枕套,是她从隔壁自“****”后就造反住进来的毛先生太太阿五那儿讨来的花样。母亲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她说:“晓燕哪里会绣花,她这是找点事情做,宽我的心,也宽她自己的心。可现在,枕套还没有绣完,人却不晓得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这一夜母亲都没有合眼,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虽然关闭了灯,但漆黑中,那一星红红的烟火却彻夜闪烁。我的心随着这一星闪烁的烟火一上一下地不安跳动着,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但我明白,父亲、姐姐、哥哥,一家三个亲人被抓走,这对重病在身的母亲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我清楚地听到黑暗中母亲在一遍遍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在床上翻来滚去,不时用自己的脑袋撞击着靠床的墙壁。母亲在人前的坚强和在人后的脆弱,让我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尚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一瞬间感到了自己肩头的担当。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恐慌:假如有一天,父亲、姐姐、哥哥从遥远的天边回到家中,而守候在母亲身边的我却无法还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母亲,那么,即便我们家血洗沉冤,一个失去母亲的家也只能是一个破碎的家,而一个破碎的家,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将自己的枕头、被子搬到母亲床上,我将自己火热的胸口贴紧母亲颤抖的后背,我抱着母亲,就像抱着一个无助的婴儿,直到她在我的怀中渐渐安静下来,最终掐灭烟头。我相信母亲已经明白:父亲走了,哥哥、姐姐走了,但她还有我,我会陪着她,一直陪着。
第二天早晨,两个陈公安又来了,他们来拿粮票、衣服、洗漱用品。母亲第一次开口问他们,人被关在哪里,能不能去探望?两位陈公安互相看了一眼,没有正面回答母亲的问话,而是顾左右而言他:“他们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知道,要想从陈公安们嘴里套出半点信息,那都是痴心妄想。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哥哥、父亲和姐姐当时被抓和被抓以后的具体情况。
我哥哥其实是在上海被抓的。虽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门,但他的被抓其实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那次他离开家以后去了很多地方,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最后到了北京。其实,我哥哥这次远行是专门去进行社会调查的。他希望了解到,在即将展开的********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有人说,干部阶层是“**********”中的既得利益受损者,我们作为干部子弟反“******”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我哥重点跑了上海和东北,深入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促膝对话,他甚至还到了长春的解放军红九连,和当时全军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于小平彻夜长谈。最后,我哥得出结论:即使在“******”控制的上海和东北,群众也是反对他们的。他把调查结论都详细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哥哥身上还带着一份父亲的在京老战友的名单,他们大多在京城的重要部门曾经或仍然拥有较高的位置和级别。哥哥按着父亲提供的联络图上的名单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门拜访,父亲的老战友们也都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他们看来和自己当年一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这些老干部普遍对“******”恨之入骨,又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国家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大多老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赋闲在家,但和哥哥这样的年轻人聊起国家大事还是滔滔不绝。哥哥把这些老干部对“******”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他将此也看作社会调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这些社会调查后来会牵连一大批老干部和他走访过的人,哥哥为此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记日记。
离开北京后,哥哥到了上海,他落脚在姨妈家。姨父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哥哥5月7号到上海,在姨妈家住下后他又开始拜访父母在上海的老战友,早出晚归,甚是忙碌。5月9号那天,哥哥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我爸的一位老战友丁伯伯家。那天姨父突然提前下班回家,进家门时脸色很阴沉。姨妈问他出了什么事,姨父说,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他下放劳动的工厂里去了,问他是不是有个外甥住在家里,并告诉他,这个外甥出事了,今晚要在他家里进行抓捕行动。还很严肃地对他说:此事已经向马天水同志(当时的上海********)汇报了,天水同志说,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点要求:第一,要积极配合组织行动,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担保不透露半点风声;第二,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成材料,上报组织;第三,不能让上海的其他老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况。姨妈听完姨父的话脸色刷地白了,她很喜欢这个外甥,她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但她显然不愿意外甥从自己家里被抓走。她和姨父商量,等外甥回来是否给他点暗示,或者含蓄地提个醒。正在这时,我表哥回来了。姨父让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的柜台找丁伯伯做营业员的儿子米秋报信,要他告诉所有老同志,小弟(我哥的小名)出事了。表哥二话没说就出门报信去了。
哥哥那天回到姨妈家时天已完全黑了。平时从不开灯的楼道那天晚上灯火通明,每层楼转弯的拐角处都有两三个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在抽烟。我哥上楼时明显感觉到他们直射过来的目光。我哥诧异地想,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小流氓啊?
进门时,我哥发现从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头睡觉,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哥有点纳闷,这才八点多呀!看到我哥进来,姨妈手忙脚乱地又是给他倒水,又是给他盛饭,我哥兴致勃勃地向姨妈讲着一天在外的见闻,根本没有注意到姨妈心神不宁的异样表情。姨妈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镇定,不要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哥显然没有听懂姨妈的意思,他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姨妈话中的另一层含义。已经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拗起身来,对我哥说:“小弟,外面在查‘总理遗言’。”我哥看了表哥一眼,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此时根本没有想到表哥的话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晚上十点左右,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姨妈脸色变了,她压低声音对我哥说:他们是来找你的,你看看怎么办?你到底干什么了?还没等我哥回答,门外就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从天安门一路过来,心中的警觉和自然而然的戒备让他条件反射似地站起来就往厕所里冲。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楼道上那些抽烟的“小流氓”很可能就是冲自己来的。他想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封刚刚收到的来信,那上面讲的都是杭州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情况,还有对王、张、江、姚的看法。他冲进卫生间,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掉,但此时外面的人声已进客厅,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便拉开梳妆柜的门,敏捷地将那封信塞进了一只雪花膏瓶底下。时间太紧迫了,他来不及处理自己放在客厅的黑色旅行袋里的日记本。而姨妈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当然懂得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她也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当公安人员指着黑色旅行袋问姨妈:“这是他的包吗?”姨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楼下停着一辆黑车一辆白车,我哥被押上了黑车,上车前,公安人员将我哥哥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哥哥以为自己会被押送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没想到车绕来绕去开了五六个小时,这时天已经亮了。当车上的人在议论车是否已开到绍兴时,我哥才意识到自己正被押往杭州。哥哥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签字。我哥问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说:“你知道‘总理遗言’吗?”我哥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说:“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之后,他们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对我哥进行了长达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只有一个:你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审讯进行到第三天,来了一位看似和蔼可亲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来督阵的领导。他说:“据我们所知,你对反击****翻案风不满。”我哥说:“我就是拥护******,这有错吗?他上台以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日子开始好过了。”这位领导说:“你想做******的殉葬品吗?”我哥说:“你们不实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儿我也会这么说。”然而,那位公安部领导接下来的一句话几乎从根本上摧毁了我哥哥的心理防线:“你以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