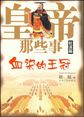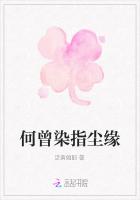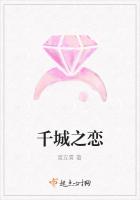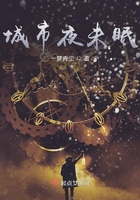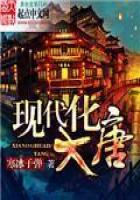其二,燕京的老师上课即来,下课即走,钱穆每到学校上课,国文系办公室往往空无一人。学校也更多地把老师当成雇员,就连办公室要喝水都要自带水壶。这让钱穆很反感,因为他不愿意仅仅把教书当成一个职业。后来钱穆在北大上课时,各系都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就在休息室办公,有一助教常驻这里。老师们上课前后就在室中休息,一进门,就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让你擦脸,又为你泡热茶一杯。上课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下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这种尊师重道的方式让钱穆有了家的感觉,觉得这才是一个中国的老师应得的礼遇。
钱穆后来贵为大师级人物,但是在尊师重道方面也堪为世人楷模。
1941年,钱穆回乡省亲,此行他去常州拜访了自己在常州府中学堂时的历史老师吕思勉,并受其邀请回母校讲演。吕思勉当时在上海光华大学执教,钱穆的学生、史家严耕望曾将吕氏和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钱穆此时的声望已不在吕氏之下,但他在讲演中处处以学生自居,谆谆告诫在场的年轻校友们:
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长寿的秘诀
钱穆和梁漱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只有中学学历,却靠自学成为一代大师,再比如两人从小都体弱多病,却几乎都长命百岁。不过梁漱溟的长寿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清心寡欲,他一生茹素,按他自己的话除了思考没有别的爱好。而钱穆的生活却是多姿多彩,他的生活和梁漱溟比起来就像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的区别。
钱穆最大的爱好除了读书,应该就是旅游了,他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钱穆几乎每到一地都要遍游当地和周遭的风景名胜,时而要做劳形劳力的远足,但他乐此不疲。在他八十之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大量篇幅都用在描写自己当年的游玩之乐以及对山水佳音的感悟上,那个时候他已经目盲,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自然风光的无限眷恋。
令人佩服的是,即使在国难当头、流亡西南的岁月中,钱穆依然游兴不减,那些在苦难人眼中的穷山恶水到他眼里仍然迷人可爱。1943年,钱穆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时,他的学生回忆道:
先生很喜欢散步。每晨早餐后,由我陪从,沿着湘江西岸顺流南行;大约走一小时,再沿着去时的岸边小道回老城。这样的散步,除天雨外,没有一天间断过。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
钱穆在游玩途中曾多次遇险,但他从不挂怀。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劫匪,相机和眼镜都被劫去,差点成了睁眼瞎。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阵豪雨,被浇得狼狈不堪,但他却说“在屡游中,获此稀有之遇,亦甚感兴奋”,俨然已经有了一种东坡“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钱穆还把旅游与教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经常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出游,在途中钱穆的“指点江山”成了学生们难忘的受课。在带北大历史系学生游曲阜孔林的时候,面对孔林金元以后碑碣尤多的情形,钱穆对学生解释:“当时中国人受异族统治,乃不得不更尊孔,使外族人知中国有如此人物,不敢轻视中国。你们老是说孔子是皇帝专制所尊,难道当时中国人尊孔也是担心外族人不易专制吗?”学生默然,钱穆乘机教育学生:“游历如同读一部活历史,司马迁早年就遍游名山大川,你们回去再读《史记》,感觉就不一样了。”
钱锺书的夫人杨绛在北京上大学时,曾和钱穆结伴出游,火车在经过蚌埠一段“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时,杨绛面对这一荒凉而又乏味的路段发出感慨:“这段路最乏味了。”钱穆在一旁听后,对她说:“此古战场也。”又给她介绍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等等。杨绛听他这么一讲,感觉眼前的景物顿时鲜活起来,“油然起了吊古之情”。
钱穆晚年目盲,虽然比起陈寅恪的中年目盲已经算幸运了,但是仍然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夫人的帮助下,这个九旬老头完成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部着作《晚学盲言》。临终前三个月,由钱穆口授,夫人整理,完成了其最后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钱穆再一次向儒家“天人合一”的最高命题致敬,并以此来为自己一生贴上终极标签,他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现在钱穆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中有一“合一亭”,亭的外墙刻有钱穆的《天人合一论》,成为香港着名的风景之一。
除了旅游之外,钱穆还有很多爱好。
比如好音乐,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老师童伯章学过昆曲,擅长箫笛,他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呜呜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的大哥则擅长笙与琵琶,早年两人在乡村小学任教时,兄弟俩常一起合奏《梅花三弄》,颇有点“笑傲江湖”的味道。这个爱好一直延续到他晚年牙齿掉光后。除昆曲外,钱穆也爱好各种地方戏,热衷于研究京剧和评剧,甚至有过写戏剧史的打算。
好美食。有一次钱穆跟友人到包头游玩,人人到这里都要去市区品尝有名的黄河鲤鱼。友人向钱穆建议,干脆咱直接上渔埠吃,这样更新鲜,更有味道。钱穆听完拍手,果然是行家!于是两人一起去了渔埠,没想到那里除了沙滩与渔船之外什么也没有,只好折回。到了火车上听到那些去市区吃鲤鱼回来的人不停夸鱼味之佳,两人心有不甘,竟然冒着赶不上火车的危险又跑回市区吃了一趟黄河鲤鱼,差点因此误点,闹出笑话。
钱穆还精通太极拳,在这上面下了几十年的工夫,堪称行家。据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初期,一天他正在教室上课,突然间来了两个捣蛋的混混,钱穆一怒之下展示了自己的中国功夫,袖子一挽,摆出了一招揽雀尾的姿势,两个混混认定眼前这个小个子老头一定身怀绝技,吓得赶紧拔腿开溜。
钱穆的这些嗜好中,最神秘、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静坐(息功)。
在回忆录中,钱穆详细地记载了一次自己练习静坐的过程:
余时正习静坐,已两三年矣。忆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殓。尸体停堂上,诸僧围坐诵经,至深夜,送殓者皆环侍,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复知觉。又知堂外铳声即当入殓,始披衣起,出至堂上。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念此后学坐,倘时得此境,岂不大佳……
看起来很像武侠小说中的高手在修炼内功,钱穆的功力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一定颇具境界,有事实为证:
有一天,钱穆正站在桥上等候渡船,呼唤渡船靠岸。上船之后,他坐在一个老者的旁边,老者充满惊奇地盯着钱穆看了看,然后对他说:“你一定是静坐的行家。”钱穆问:“何出此言?”老者答:“我是看你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有神,所以才知道的。”
后来,钱穆的高徒余英时回忆老师给他的第一印象也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不知道是不是修炼静坐的缘故,钱穆比常人更保有一颗宁静的心,能够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这正是做学问者最渴求的品质。
1938年秋,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钱穆为了写作他的《国史大纲》来到了距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岩泉寺里,在这里他整整隐居了一年多,完成了这一部五十三万余言的巨着。写作的同时,他还在西南联大兼课,每周四下山,乘坐小火车赶往昆明,周日返回,但他不以为苦。
这种经年累月的苦行僧生活没有几个人可以忍受,就连陈寅恪来到这里看望钱穆后,都感叹说:“使我一个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但钱穆后来在回忆这段山居日子时却说:“回思当年生活真如在仙境。”
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钱穆说:“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好旧的,所以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钱穆在北京教书时,中式的长袍已经成了一种落伍的标志。但是钱穆看到好友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坚决扞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时候,燕大作为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水电费催缴单都是用英文写的,对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但是钱穆不干了,他每个月接到水电缴费单都把它扔到一边。后来学校派人来质问这个“老赖”了,钱穆告诉来人:“我是学校所聘的一个国文教师,不必要认识英文。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办学校要用英文发通知?”
钱穆在中学执教时有一段时间还兼过英文课,他的英文看懂水电单肯定是绰绰有余,他的理由无非是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就得用中文,这种行为就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本能。为此,他不惜当刺头。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教师的宴会上,钱穆大胆直言,批评燕大各楼的起名问题,入校门即见M楼、S楼,不伦不类,既然在中国,就应该起个中国名字才是。司徒雷登最终接受了钱穆的建议,事后,他按照各楼美国捐赠者名字的汉译,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办公楼命名为贝公楼。有人跟钱穆开玩笑说:“正是因为你的提议,学校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座楼,与胡适各分各占一楼,你真是荣幸啊!”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北大搬到了燕大的校园,现在北大校园内有个未名湖,就是当年钱穆起的名字。
在钱穆的心目中,一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髓首推其历史,他认为一个国民只有充分了解本国的国史才能建立起对国家民族的“信仰”,他说:“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欣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销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1950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其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已经功成名就的钱穆完全不用去自讨苦吃,但他看到许多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人彷徨无着,失去精神支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责任,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之机,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1986年6月9日,92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恐怕是他的人生中被人非议最多的,李敖就看不惯钱穆向蒋介石靠拢,讽刺说:“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阶级的怀里的!”
其实,何须苛责钱穆,只要我们完整地看一看蒋介石与钱穆之间的交往,便会觉得钱穆亲近蒋介石顺理成章。
抗战时,钱穆曾受蒋介石委托编写《清儒学案》,并在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两人数度会面,多有交情。但钱穆对于蒋介石并非盲目崇拜,1949年国民党军败退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下野的人士之一。不过蒋介石却从未因此忌恨钱穆,为了表达对钱穆的敬重,在面见钱穆时,蒋介石甚至特地穿上了长袍。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经费十分困难,几乎难以维持,这时蒋介石雪中送炭,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其港币三千元,救新亚于水火之中,前后长达四年,直到1954年新亚得到美国基金会的赞助为止。事实上,当时台湾的很多学校情况并不比新亚好。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由港赴台。蒋介石为了表达对钱穆的敬重,特别在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为其筑别墅一幢,名为“素书楼”,还让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他为研究员,使他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可以潜心治学。
不管怎么样,老蒋对文化的尊重还是有目共睹的,换成另外一个人,在溃败之际未必会把“抢救学人”当成如此重要的大事来抓。也就是因为这样,李敖还能活着骂蒋介石,我想,光这一点,他应该知足了。而对于钱穆来说,他和蒋介石仅在同样对王阳明和曾国藩的服膺上就足以擦出火花来。
1975年,钱穆得知蒋介石去世的消息时,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他的感受并不是特例,这在林语堂等很多人身上都有过。
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岁的钱穆在台湾无疾而终。钱穆生前曾立下誓言,如果活着时不能回去,死后也要归葬故里。1992年,夫人胡美琦遵照其遗愿,将钱穆的骨灰带到江苏无锡老家,撒入了美丽的太湖。钱穆,终于以这种方式回家了。
钱穆去世后,他的高徒余英时在挽联中用一句话概括了老师的人生:“一生为故国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