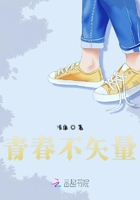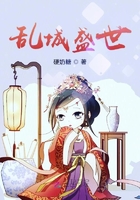他们说,八角井镇需要像王周龙那样的镇长,中国也需要像王周龙那样的基层干部。百姓心中有杆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选镇长不到一月的王周龙,又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对于个人来讲,不仅是无上的荣耀,更是崇高的责任。
对于八角井人来讲,王周龙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喜讯。在那时,王周龙的头上,已经有了许多耀眼的光环:“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等,但在八角井人心中,王周龙是他们按自己心愿选出的镇长,是要为他们服务的公仆,最为重要的是不管他头顶多少光环,他依然是八角井镇土生土长的农民。
八角井人知道,这位心怀苍生的农民企业家,他们自己选出的镇长,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周龙,生于斯,长于斯,从呱呱坠地,儿童、少年、青年,直至中年,不管自己的事业有多辉煌,他都从未离开过八角井,离开过生他养他的故土,对于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他太了解了。
八角井人深信,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周龙,一定会带上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心声,如实地反映到国家最高决策层。
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周龙说:“我要说的就是如何解决农民所面临的问题,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提高农业的生产技能和效率,更新产业结构,创造更富裕的农村生活。”一九九三年三月五日,阳春三月,万里碧空。
八角境中,德阳市内,街道旁,大路侧,人头攒动,一幅万人空巷的图景。
而在那天,这些夹道而立的人们,他们不是欢迎,而是欢送。
旭日东升,霞光万丈。八角井的农民,德阳市的市民,他们打开了所有的临街的门和窗,走出户外,带着欢欣与鼓舞,带着祝愿与期盼,伫立于春风中,静候于晨晖下。欢送的车队,缓缓地驶出“德钢”,驶出八角井,渐渐地离开德阳市区,沿街沿路而立的,有熟悉的面孔,也有不熟悉的面孔,但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都是王周龙的父老乡亲,他们的手中执着“欢送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周龙进京”的横幅,所过之处,有喧天的锣鼓,有诚挚的掌声,有热烈的欢呼……
只要你是人,就不可能不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而这种感动,也不是我这支笔能表达的。王周龙说:“面对这些群众,我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地为他们努力工作。”
王周龙下定了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他一定要对得起脚下的这片土地!对得起支持他的群众!对得起信任他的父老乡亲!
带着父老乡亲对他的信任与期盼,带着来自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迫切的心声,王周龙走出了德阳,走出了四川,跨进了人民心中的圣殿--人民大会堂。
从农民到企业家,由镇长到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这条路走得漫长而艰辛,但王周龙说:“我感到荣幸,也很光荣。”
王周龙说:“在那之前,我只考虑‘德钢’的发展、壮大,‘德钢’职工的权力和利益。当上镇长后,我就必须从全镇的角度去考虑,不但要考虑全镇人民的穿衣吃饭,还要考虑在我的任期内,要怎么让他们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怎样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增加他们的收入。”
王周龙的父亲很平凡,因为他的平凡,他这一辈子从没做过轰轰烈烈引人视听的大事,他最出色的本事就是在每年除旧迎新之际,到八角井的街上,摆上一个写字的摊子替人写春联。他有颗非常善良的心,但他还是一家之主的时候,连救助别人的好事都很少做,因为在那时他们自家都还过着“天点灯,风扫地”的日子。
每逢有人讲自己如何英雄,如何舍己为人的时候,王父也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一个要饭的来到自己的门口,锅里没有一口饭,屋里没有一把米,没有东西打发人家,他常为此感到惭愧。
不管你是否认同,但在父母的眼中,儿女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王父希望王周龙能把人之恻隐之心永葆下去。他对当上了镇长的王周龙说:“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官,上不能给父母增骂名,下不能为子孙添罪孽。”
好的父母是一所好的学校,不管他们是身居高位还是平民百姓。高层显位未必伟大,身为庶民未必平凡,父母的品行如何,很自然地荫及他们的下辈。
身居双位(“德钢”的厂长和八角井镇的镇长)的王周龙,父亲的话时刻伴着他,督促着他。在他后来的工作中,也确实证明了他是个好领导,也是个好厂长(董事长)。八角井镇的群众这么说,“德钢”的干部和职工(股东)也这么说。同时,党和政府也对他工作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给了他很多很多荣誉和称号。
每当王周龙听到来自四方八面的颂扬之词时,每当一次一次站在各种各样的领奖台上时,王周龙总会这么想:“我真的有这么好吗?”
于是,他就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以后做事,更不能让别人在背地里骂我的父母,也不能因自己不小心做错了事殃及后辈儿孙,使他们以后难以做人。
王周龙也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时时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
做“德钢”厂长(董事长),他时时都在考虑职工的权益,股东的利益,企业的发展。做镇长,他要求自己在任期内,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多为群众做点好事做点实事。
许多人只知道王周龙的好,不知道他背后给予他谆谆教诲的父亲,因而没有人颂扬过他,就连近邻好多后辈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王周龙(王厂长、董事长、王镇长)的父亲。
但有了“王周龙的父亲”这样的名号,也是相当值得骄傲的。所以,他老人家在上世纪末撒手人寰时,也极具哀荣。
王周龙又说,他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穷苦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他一个成功的机会,给了他一个施展才智的舞台,使他具备了可以帮助别人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因父老乡亲的信任和支持,赋予了他带动一方、改造一方的权力。
他说,共产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现在经常说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纵横商场二十余年的王周龙,他不懂官场哲学,他只知道,作为八角井镇的镇长,就是八角井镇人民的公仆。
在当时,许多乡(镇)政府,为完成所谓的“目标任务”,创政绩,搞形象工程,便巧立名目,不断的加重农民负担,聚敛钱财,弄得怨声载道。许多不合理的收费遭到农民抵制时,乡(镇)政府便组织起所谓的“征粮队”、“打狗队”、“联防队”之类的行政执法队伍。
王周龙上任伊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八角井镇组织的“打狗队”,因为这支队伍名义上是用来“打狗”的,而实质的任务就是用来收拾“人”的。
王周龙说:“要完成目标任务,树形象,并不是不可以搞,但作为政府,在收取农民的合理税费后,就不能再去‘刮’农民,而是要靠‘挣’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挣的方法就是给乡镇企业以最宽松的环境和最大限度的政策支持,使之发展壮大,然后再用乡镇缴纳利税所积累的资金,做好政府应该做的事。”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王周龙上任后所做的第二件事。
八角井镇发展企业,积累了丰厚资金,许多在当时看来应该由农民负担的也不让农民出了。仅一九九三年,政府便拿出六十万元资金,取消了十九项农民负担,全镇农民大多数只负担农业税、水利费,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村社,多少收取一点公益金,有的村只负担农业税一项开支了,全镇农民个人负担只占原来总负担的百分之三点五。
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声由来已久,国家也曾为此三令五申,但好多地方政府具体实施时,却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为此,国家新一届领导集体采取强硬措施,力争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而早在十多年前,在八角井镇,作为八角井镇的农民是多么神气呀!这样轻的负担的确令中国多少贫穷农村躬背深耕的农民们羡慕啊!
回头来再看那些只靠农民,想尽一切办法来刮取农民才能养机关、养学校、养干部、养教师、养公路、养“五保”、养民兵的乡镇,比一比吧,是不是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还有何脸面做所谓的“父母官”,还大言不惭地吹嘘要“造福一方”?为什么不学学八角井的淘金人,为什么不可以像王周龙那样,不是靠“刮”,而是靠“挣”来解决那些需要“养”的呢?“要想富,先修路”,在改革之初就喊出了这个响亮的口号,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可许多具有开发潜力的地区就是修不起路。
“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行路难的现状也是八角井人迫切需要改变的。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所产生的利税让八角井镇有雄厚的资金积累,由镇政府统一规划、指引带动,钢厂牵头,重新规划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
一条条村镇相连、村村相连的乡村公路的施工建设全线拉开,由“德钢”建筑工程安装公司经理李本辉带队,他们像建设自己的厂房一样,以“深圳速度”,从一九九三年初开始动工,到该年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宽十二米、长三十四公里连接九个自然村和过境干线、入城大道的水泥公路,使八角井镇成为西南第一个村村社社通公路的乡镇。随后,他们又在这些公路的两旁,种下近二十万株意大利白杨。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杨树,全都长到了十余米高,宽大的树冠,浓密厚实的叶片,紧密连成一片,宛如一排排遮天蔽日的绿伞,几百米几千米笔直一线,气度豪迈非凡。
这一排排凝重的碧绿,穿插于八角井镇的万亩良田,稻花香里,蛙声一片。好一派田园风光。
万亩良田万亩园,
碧树梢头挂紫岚。
春夏吐尽鹅黄绿,
秋冬林里涌波澜。
旭日染得田园翠,
清风戏叶绿浪欢。
却似无风又有风,林阴道下尽欢颜。
八角井镇的好多村民都说:“现在出门,再也不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了,只要在本镇内,都可以清清爽爽地去,干干净净地来。”
公路的畅通,不仅改变了整个八角井镇群众的生活品质,也为他们的发家致富,提供了良好的通行条件。
有了路,真的能致富,养鸡的肖碧琼、邹兴富,养鸭的廖再江、张兴友,养猪的陈文国,养鱼兼种植的李明贵,他们都有很深感触。他们都说,如果路不通,他们就不可能如此规模化的种养,也就不可能有他们富有的今天,路通了,减少了他们的运输成本和劳力投资,产品的交易可以直接在各自的家中进行。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的。但这精神从中央传达到地方后,跟着说的不少,落到实处的不多,特别是那些贫困落后的地区,仅为“普九”,就使许多乡镇负债累累。
在八角井镇,当企业有钱以后,兴办教育便不再是难事。于是,八角井镇政府便开始把兴办教育落到实处。
一九九三年初,新的一届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上任后,镇长、书记就带领全镇的企业厂长、经理们参观本镇学校。
当时八角井镇有九个自然村、一个街道办。九个自然村每村都有一所小学,在八角井镇街上还有所中心校。
在这里土生土长,也曾在那些小学、中心校就读过的镇干部和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自从跨出了学校后,都为各自的事业和工作而奔忙,很少回到自己的母校去看看,有时都只是从校外匆匆而过。
当年还是蹦蹦跳跳的学童,如今有的已过而立,有的年近不惑,还有的竟已两鬓斑白,而这些人均事业有成,是八角井镇的精英与骄傲。但他们的母校呢,几十年过去了,风摧雨蚀,比起他们当年就读时更加残破。
这些意气风发,功成名就的八角井精英,又重新回到久违的母校,当他们走进自己当年的教室时,不管是镇长王周龙,还是企业厂长、经理们,都被教室内的景象惊呆了。几十年过去了,学校还是当年的学校,教室还是当年的教室,课桌也同样还是当年的那些课桌。因为破旧的课桌上,竟然还刻着今天这些企业家、干部们“王胖娃”、“张狗子”的奶名。
镇长王周龙一见此状,不由阵阵心酸。这就是如今这些在八角井镇叱咤风云,威风凛凛,在商场上纵横驰骋的企业家们的启蒙母校啊,怎么能再让她如此满目疮痍、如此颜容破败?
他对同来的一干人说,请大家找找自己从前坐的位置吧,去体味体味。
几十位企业家、经理们看到此景,也不禁触景生情,他们和镇长王周龙一样的牵怀动容,一样的心潮难抑。
王周龙突然问:“弟兄们,这学校该不该修?”
“修!”
几十个厂长、经理异口同声,没有一丝杂音。
王周龙听后,又大声地说:“好!那么就拿出你们的行动来。”
随后,王周龙带头从自己领导的“德钢”拿出四百多万元,而他自己也率先捐资一万元。在他的带动下,钢厂四千名职工捐资近二十万元,筹资建校,全镇企业随后紧跟,一共筹资一千多万元,又由“德钢”本厂的建安公司承担基建任务,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建起了一所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多功能镇中心小学,让全镇所有的学生,近两千名八角井人的后代在这全国一流的学校里接受良好的教育。
为了保证教学的质量,八角井镇还建立了“教育基金会”。用高薪招聘小学教师,按质付酬加奖金,不断增强师资力量。八角井镇中学副校长张在华说:“因有良好的教学环境和较高的待遇,许多优秀的教师都把八角井镇学校当成了他们首选的去处。”
这种极有远见,立足于为后人造福的建校行动,如果没有镇政府大力倡导、“德钢”的牵头、其他乡镇企业的支持,连想都不敢想。
看吧,校园内那一张张天真、活泼的笑脸,朗朗的书声,涌动着八角井镇末来的希望。
原东河镇党委书记江忠贵说:“八角井、东河镇原本一家,一九六一年以前,均属东河镇的辖区。”
但因有绵远河的阻隔,给行政管理带来诸多的不便,不得已,才划一为二,也就成了河东河西两种不同称谓,不同的地域经济模式和发展方向。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东河镇地广人稀,产粮甚多,加上经济林业(水果)收入,东河人衣食甚丰,让当时还处于捧着石头望馍馍的八角井人羡慕不已。
一条河阻隔不了人们对幸福的向往。在那时,许多八角井的姑娘以能嫁到东河为幸事,以嫁往东河为自己终身幸福的依托。
一条河自然也不能阻隔亲情间的往来,众多的联姻,使东河人与八角井人走动频繁。再者,东河那边没有集镇,也就没有产品交易的场所,所以东河人要买东卖西,就不得不渡河到八角井。
亲情的往来,产品的交易,促使许多人因此以身涉水,也使许多人因此而丧命于绵远河中。江忠贵说:“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几人淹死在河里。”
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八角井顺应时代的潮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了在经济上的腾飞,以农耕生产为主业的东河镇在发展上开始不断落后,于是,仅一河之隔的东河镇人便纷纷拥进八角井。
面对这样的潮流,绵远河水又在那些到八角井工作的人身上大显淫威。一九八四年七月中旬,曾在东河任党委书记,后到八角井自来水公司工作的赵家泰回东河休息星期日,星期一早晨六时许,赶往八角井上班,当他下岸泅水过绵远河时,就再也没有上岸了。同一天,家住东河五村六组的王道和,他是个瓦工,在八角井镇一家砖瓦厂上班。中午十二点,他下班回东河,体力和水性俱佳的他,也同样命殒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