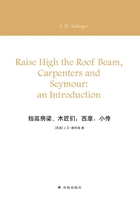就是在那天晚上六六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他终于咬住了那个梦中的花蕾。他是顺着一条蓝色的小径走上那座雪白的菠萝状山丘的,那山丘薄得透明雪白如玉在阳光下微微颤动着,上面布满了这种蓝色的小径。他顺着小径爬上了那菠萝便看到了那顶端中央挺立的浑圆褐色的花苞。到处飘荡着花香。一只蜜蜂嗡嗡地围着那花苞跳舞最后轻轻落在那花蕾上。他知道那蜜蜂是在吸吮那花蕾里的水,他知道那花蕾深处有很香很香的水,他就是到这里来喝这种水的。他的嘴很渴,好像有无数只烈火的小手正从那喉咙里伸出来,伸向那个花蕾。他挣扎着爬过去。他用了很长时间赶走那个蜜蜂,最后,扑向那个花蕾。
他的嘴唇触到了那柔韧而温软的花瓣。那湿润的花瓣颤动了一下微微挺起来迎接他。他呻吟了一声便咬住了它。就在这时,就在这时,一股温暖白色的水流从那花蕾的中心汩汩流出,越流越多,越流越多,直到整个天地都涨满了这白茫茫的一片,把他漂浮了起来……
这天夜里六六醒来时发现身子下面湿了一片。不是他小时候尿床的那种湿。那湿是黏稠的,他从未有过。
6
现在你可以对马小燕所说的那次谈话作一番大致的推测了。
当然不完全像马小燕所说。六六虽然曾经有过用唾沫弹女孩的劣迹,但长大以后却是一个相当腼腆容易脸红的少年,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软磨硬缠不像是他所为。那么他有没有张惶失措呢?有没有目不转睛呢?有没有词不达意结结巴巴引人怀疑甚至反感呢?有没有笨拙地企图表达某种亲近之意呢?
我在设想。
我设想在六六懒洋洋地打开门时,首先闭了一下眼睛。这个动作可能因为刺目的阳光,也可能因为门口站着的那个模糊背光的身影使他有一种令人心痛的联想。震颤是微妙的,难以言说,又确确实实存在,这种感觉一旦抓住六六这种孤寂又茫然的心灵,将使他无法摆脱。
“你们家有没有锯子?”
没有回答。
“你们家有没有锯子?”
他注视着她。沉默。
“你们家没有锯子吗?”
仍然是那种如梦初醒的茫然,只是现在有了声音:
“是,我们没有。”
于是她疑惑不解又满腹怨气的走了。
走出几步,她回过头,看见他恍惚的目光像影子一样跟着她。
7
马小燕在那个十一月的夜晚突然惊醒。她听到一种来自屋内的响动,确切地说那声音来自天花板的上部。开始她以为是老鼠,但后来她发现这声音要大得多。有一次她恍惚间听到了一个喘息,那只能是人的喘息之声。如此几个夜晚之后她感到恐惧,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恐惧,在她十六岁的生涯中这种恐惧是不多见的。她告诉了父亲。父亲看着她的眼睛说:
“你能肯定不是在做梦?”
“我能肯定。”她说,脸色苍白。
父亲从她的眼睛中看出某种不同于以往那个喜欢恶作剧的女孩的东西。他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以一种老军人特有的简洁,他说:
“我让小王住你隔壁。他有枪。”
小王是他的警卫员。
六六在天快亮的时候才溜回被窝,他的牙齿格格打架,但这不是出于寒冷,而是出于兴奋。他为脑中出现的一幅情景激动不已:马小燕裸露的肩膀和大腿在台灯下闪烁着雪一样流动的光芒。
当她向尿盆弯下腰时他看见了浑圆的臀部和小花背心深处奇异的颤动。遗憾的是她穿着衬衣,而且从他这个角度他无法看到那一对乳房,那乳房他曾经仔细估计测算过,和二姐的应该不差大小。不过他相信他会等到看清楚的那一天的。
他用了两天的时间在母亲房间的天花板上打了一个洞。从那里他爬上了连接这一排平房屋顶的长长的通道。
严格说来这个洞是他母亲打的。九月的一天他听见母亲房中传来一阵轰响,走过去时他发现他那疯子母亲站在一张支在桌子上的椅子上的小凳上,手拿一把锯子,正在锯开天花板。
“猫,猫要上去。”她说。
父亲脸色发青地冲了进来;这时那些宝塔一样的凳子椅子突然塌了,母亲像一袋沉重的面粉在桌角上蹭了一下又滚到地上。
“猫,猫要上去。”她又说。
父亲阴沉地望了天花板一眼,那里,一块被撕裂的胶合板碎布般耷拉下来,露出黑洞洞一个豁口。
这是母亲被送往精神病院前两天的事情。
有一天六六漫不经心地走进母亲的房间,看见那些乱放的桌椅已蒙上灰尘。突然他听到了一种声音,嗡嗡嘤嘤在头顶旋转,抬起头他发现声音是从豁口传来的。好奇心使他仿效母亲爬上桌子将耳朵凑近豁口,他的心顿时通通跳起来,原来那竟是和他隔着一间房子的马小燕的声音!
他在桌子上支好椅子,从工具箱里找到那把锯子,开始重新锯那个豁口。和母亲相比他无论从力气和技巧都更胜一筹,而且更加深思熟虑。最可贵的是再没有人进来打搅他,因为母亲被送进医院了,二姐去油田了,父亲出差了,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一声不响地干着,只是在头晕眼花力气不支时才停下来,即使这时,周身汹涌奔突的血液又呼啸着冲上他的脑门,于是他又拿起锯子。
他在夜深时分住手,睁着眼睛躺在桌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微明,爬起来再接着干。
马小燕父亲的警卫在第二天晚上九点多听到她在敲墙,于是来到了她的房间。
“有什么情况吗?”他问。
“现在还没有,”她说,勉强一笑,“不过你从现在起就来陪着我。我觉得他一会儿就要到了,真的。”
他想了想,坐下来。
“好吧,这样也好,省得你到时候叫不醒我,我有时候睡得很死,”他认真地说。
“你带枪了吗?”
他有些炫耀地掀开大衣的前襟,一只放手枪的小皮套露出来。
“我装了整整十发子弹,一颗不少。”
六六在夜里十一点多站到了豁口前。窗外寒风轻轻地摇曳着树枝,晃动的影子和清冷的月光一起倾泻在地上。
他仰头望着豁口。那黑洞洞的洞口神秘而无言地向他敞开着。
他伸出双臂,用双手抓住豁口的边缘。
他深深运了一口气,身子一提,就腾空而起。
现在他是在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通道里。一股腐朽的尘土味扑面而来。他突然感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像电流一样通过他的全身,他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马小燕刚刚听到那个声音时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当时,她和警卫都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看到台灯蒙蒙的亮着,自己正在灯下叠着一床被子,不知为什么那被子总也叠不好。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来自顶棚的那个声音。“它来了,得把警卫叫来,”她想,赶紧去敲隔壁的墙,在敲的时候她又模糊想起警卫似乎已经来到了屋里,可这时候他竟然不知到哪儿去了,这使她感到焦虑。“我是在梦里,”她对自己说,“这要是在梦里就好了,”这样想着她就真的醒了过来,她看见警卫闭着眼睛张着嘴正歪在一张椅子上,而顶棚上,真的传来一种隐隐的小心翼翼的响动。
她从床上光着脚跳下来,使劲儿摇着警卫的肩膀:
“它来了,它来了!”
大衣从椅子上滑落,他张开眼睛从椅子上一蹦而起,抓住腰上的枪套:
“谁?谁来了?”
马小燕紧张得说不出话,只是用手指着顶棚。
警卫顺着她的手朝顶棚望去,眼睛布满红丝,直到这时他才完全醒过来。
顶棚上一片寂静。
“什么也没有哇,”他疑惑地嘟囔一句。
马小燕将手指放在唇上,示意他小声。她的眼睛闪着绿光,像猫一样。
他立即明白了,他拉灭了电灯。
黑暗中他们等待着,望着头顶上方。
一片寂静。
寂静中警卫掏出枪,打开了保险。
终于,小心翼翼地,那个声音又响起来,黑暗中他很快就辨认出了它移动的方向。
“谁在那儿?”他喝道。
那个东西突然不动了。
“还真是个人,”他低声说,骂了一句,“我操他奶奶!”
接着,他抬起胳膊,向着顶棚上那个方向,连发数枪。
屋顶有只猫
1
很久以来我听到过这样一种理论:某处一只蝴蝶翅膀的颤动引起了千里之外的一次强烈的地震。或者说某一次大规模地壳运动的最终原因是某一只小粉蝶在阳光下一次本能的肢体抽动。我相信这种理论。而且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从小粉蝶的翅膀到那次地壳运动之间漫长的因果之链。过程可以省略。只要你一下就理解了,理解了上帝在给我们制造命运这种游戏时,有多少深思熟虑和漫不经心。
那么对于六六,那只小小的蝴蝶翅膀在哪里?
六六,被一发飞来的子弹打死了。我在黄羊堡初中的同学六六,在他十四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爬上了一个名叫马小燕的女孩子的屋顶,结果被一发子弹打中。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去看一个女孩儿的尾巴。或者,为了看她的乳房。为什么要去看尾巴或乳房?为了向一个名叫王建军的小子证明自己能行。为了自己对女孩子胸前那两个器官说不清道不明的痴迷。如果他是去看尾巴,那他就是为了别人,如果他是去看乳房,就是为了自己。这两种说法都说得通。然而,为什么他要爬屋顶?为什么他非要爬上那高高的屋顶呢?
我被六六爬屋顶这个细节深深吸引。我知道,如果他想向王建军证明自己的能力与忠诚,如果他确实想窥探马小燕——无论是窥探她的乳房还是她的尾巴,他都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他可以看门缝或者看窗户。他可以跟踪她尤其在夜晚她独自出门或上厕所的时候。以他和马小燕住在同一排平房这一有利条件,他不是不能找到机会。为什么他偏偏选中了爬上屋顶,这种又费时又费力,而且还有一定危险的方式呢?是什么使他对一个高悬于自己三米之上的、攀登起来非常困难的、常人一般不去问津的冷僻角落如此钟情呢?
六六对屋顶的偏爱使我眼前闪过了一个女人的形象。这女人奇特的经历就和她后来那诡异的举止一样令人不可理喻。她早年的美貌早已变得模糊,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一个疯女人的形象。但她常说的一句话却一直让我难以忘记,这句话随着六六的这次意外事件在我眼前变得格外清晰。这女人是六六的母亲。她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是一只猫。”
2
在那个闷热的中午,当六六的母亲背着一个奶黄色的小书包走出军区大院的大门时,没人发现她有什么异样。她的穿戴素雅得体,白皙秀丽的脸庞神色平静。碰到一两个熟人向她打招呼时她也微笑着点点头,一切都符合一位小学女教师特有的矜持和温文。她经过士兵守卫的岗楼走下那道宽阔的斜坡,就来到了一条僻静的街道上。街道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白杨树,树后面是高大的有铁丝网的围墙,围墙里面都是这个大军区的地盘。街道很安静。已经过了上下班时间,这条不通汽车也没有商店的小街几乎没有行人。她顺着街道走了一段拐过一个弯,经过她就职的那所八一小学的校门,来到了校门对面的一个小银行。
在银行里她填写了一张取款单,取款单的数字恰好等于他们夫妇结婚十年来的全部积蓄。钱被取出来了,那是厚厚的一捆,她看都不看就把它装进小包,然后走出银行进了隔壁的小卖部买了一盒火柴。她背着钱和火柴又沿着街道向回走,一直走回了军区大院。但是她没有回家,而是在半路上一拐弯进了公共厕所。厕所光线很暗散发着它特有的在夏季尤为浓烈的气味,一排排木头隔板隔出了一间间使人感到安全的小间。她为自己选择了最里面的一间。她插好门,蹲下来,从书包里取出捆得整整齐齐小砖一样沉甸甸的钱,拆开,然后微笑地,从容地,慢慢地,划着了一根一根的火柴,用这火柴点燃了一张一张的纸币。她看着它们像有生命一样地抽搐,翻卷,发出疼痛似的呻吟;她的表情专注痴迷甚至有些沉醉。当多达数千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令人瞠目的数字)的纸币在她手中全部变成一堆冒着黑烟的灰烬时,剩下的事情,对这个白皙而文静的女人来说,就只有爬树和疯狂了。
在这个冬天人们不止一次的看到六六的母亲。她一头乱发火焰状腾起,双目如炬脸颊赤红,一身军大衣衣襟敞开油迹斑斑,脚下的翻毛大头皮靴如同两只大船。她用仇恨的目光打量着路边某一棵蒙着尘土的白杨树,后退几步拉开距离一段助跑加速之后是猛地一窜,手脚并用在树干上走路,在不可避免的地心引力之下是沉重的有声有色的跌落,土雾腾空而起,她在土雾中爬起来,脸上多了点色彩身上多了点沧桑然而并不气馁,绕树一周,口中喃喃,信心十足地筹划着下一次冲刺。于是又是起跑和加速,加速和冲刺,冲刺和跌落。再起跑,再加速。再冲刺,再跌落。
如此周而复始。
她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猫。对一只猫来说眼前这段树干只是她脚下道路的一段。为什么她竟然走不通了呢?她不能容忍。她认为是这棵树背叛了她。
这一年,六六刚刚三岁。这一年夏天六六的父亲在外地出差因而六六的母亲有机会拆开了一封寄给丈夫的信。没人知道那信是谁写的又写了什么,人们只知道,在读了那封信后,便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从此六六母亲供职的那所学校里少了一位温文的女教师,军区大院里多了三个无人照料的孩子。
据说六六的母亲是天津一个资本家的小姐。解放后她毅然和自己的家庭决裂只身一人来到大西北报考了当时最火爆的农学院。抗美援朝爆发了,学校组织女学生给前方“最可爱的人”写信,六六母亲也写了,她的信,正好交到了前方一位尖刀连连长的手里。通信进行了一年多,这位尖刀连长(这时已是尖刀营长了)带着自己的光荣集体回国那一天六六母亲和学校许多女同学一起去车站迎接,于是尖刀连长就成了六六的父亲,六六母亲也就真的成了六六母亲。之后六六母亲又毅然和自己的学业决了裂作为一名光荣的随军家属跟着六六父亲去了许多地方,陕西,青海,最后是这个西北大戈壁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歪打正着地符合她当初报考农学院的初衷,因为她那和工农相结合的愿望算真的实现了。
但是那封信改变了一切。那封信把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学生投身革命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一下子葬送了。当然事情的真正原因只有他们夫妇知道,或者正如她丈夫所说只有她自己知道(“我可以向毛主席发誓我并没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他说)。而她,自从这个夏天的中午开始,就已经不用我们惯常的方式说话,因而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在那些学校没课父亲又碰巧不在家的下午,她的三个蓬头垢面的孩子会牵着手蹒跚着来到树边,观看母亲这项别开生面的运动。三个孩子最大的八岁最小的只有三岁,阶梯般由高至矮站成一排,目光战战兢兢又痴迷固执。他们的母亲一遍一遍地爬上跌下,就像一个过于身体力行的教练。她根本不看他们一眼,即使偶尔一瞥也漠然而冷淡,她也许是把他们和那些树,甚至是猫,混在一起了。他们是猫。为什么不是猫呢?而猫,是不需要照顾的。
只有一次,她突然停下来,用迷惑不解的目光望着他们,问:“你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