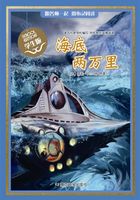话分两头。再说张廷秀在南京做戏,将近一年,不得归家。一日,有礼部一位官长唤去承应。那官长姓邵,名承恩,进士出身,官为礼部主事,本贯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氏。夫人朱氏,生育数胎,止留得一个女儿,年方一十五岁,工容贤德俱全。那日却是邵爷六十诞辰,同僚称贺,帀筵款待。廷秀当场扮演,却如真的一般,满座称赞。那邵爷深通相法,见廷秀相貌堂堂,后来必有好处。又恐看错了,到半本时,唤廷秀近前仔细一观,果是个未发积的公卿,只可惜落于下贱。问了姓名,暗自留意。到酒阑人散,分付众戏子都去,止留正生在此,承应夫人,明日差人送来。潘忠恐廷秀脱身去了,满开不欲,怎奈官府分付,可敢不依!连声答应,引着一班徒弟自去。廷秀随着邵爷直到后堂,只见堂中灯烛辉煌,摆着桌榼,夫人同小姐向前相迎。众家人各自远远站立。廷秀也立在半边。堂中伏侍俱是丫鬟之辈。先是小姐拜寿,然后夫人把盏称庆。邵爷回敬过了,方才就坐。唤廷秀叩见夫人,在旁唱曲。廷秀唱了一会,邵爷问道:“张廷秀,我看你相貌魁梧,决非下流之人。你且实说:是何处人氏?今年几岁了?为甚习此下贱之事?细细说来,我自有处。”廷秀见问,向前细诉前后始末根由。又道:“小的年纪十八,如今扮戏,实出无奈,非是甘心为此。”邵爷闻言,嗟叹良久。乃道:“原来你抱此大冤。今若流为戏子,那有出头之日!既会读书,必能诗词,随意作一首来,看是何如?”即令左右取过文房四宝,放在旁边一只桌上。廷秀拈起笔来,不解思索,顷刻而成,呈上。邵爷举目观看,乃是一首寿词,词名《千秋岁》,词云:
琼台琪草,玄鹤翔云表。华筵上,笙歌绕。玉京瑶岛,客笑傲乾坤小。齐拍手唱道:长春人不老。北阙龙章耀,南极祥光照,海屋内筹添了。青鸟衔笺至,传报群仙到,同嵩祝万年称寿考。
邵爷看了这词,不胜之喜,连声称好。乃道:“夫人,此子才貌兼美,定有公卿之分。意欲螟蛉为子,夫人以为何如?”夫人道:“此乃美事,有何不可!”邵爷对廷秀道:“我今年已六十,尚无子嗣,你若肯时,便请个先生教你,也强如当场献丑。”廷秀道:“若得老爷提拔,便是再生之恩。但小人出身微贱,恐为父子,玷辱老爷。”邵爷道:“何出此言!”当下四双八拜,认了父母。又与小姐拜为姐妹。就把椅子坐在旁边,改名邵翼明。分付家人都称大相公,如有违慢,定行重责,不在话下。
且说潘忠那晚眼也不合,清早便来伺候。等到午上,不见出来,只得央门上人禀知。邵爷唤进去说道:“张廷秀本是良家之子,被人谋害,亏你们救了,暂为戏子。如今我已收留了,你们另自合人罢!”教家人取五两银子赏他。潘忠听见邵爷留了廷秀,帀了口半晌还合不下。无可奈何,只得叩头作谢而去。邵爷即日就请个先生,收拾书房读书。廷秀虽然荒废多时,恰喜得昼夜勤学,埋头两个多月,做来文字,浑如锦绣一般,邵爷好不快活。那年正值乡试之期,即便援例入监。到秋间应试,中了第五名正魁,喜得邵爷眼花没缝。廷秀谢过主司,来禀邵爷,要到苏州救父。邵爷道:“你且慢着!不如先去会试。若得连科,谋选彼处地方,查访仇人正法,岂不痛快!倘或不中,也先差人访出仇家,然后我同你去,与地方官说知,拿来问罪。如今若去,便是打草惊蛇,必被躲过,可不劳而无功,却又错了会试?”廷秀见说得有理,只得依允。那时邵爷满意欲将小姐配他,因先继为子,恐人谈论,自不好启齿,倩媒略露其意。廷秀一则为父冤未泄,二则未知玉姐志向何如,不肯先作负心之人。与邵爷说明,止住此事,收拾上京会试。
话分两头。且说张文秀自到河南,已改名褚嗣茂。褚长者夫妻珍重如宝,延师读书。文秀因日夜思念父母兄长,身子虽居河南,那肝肠还挂在苏州,那有心情看到书上。眼巴巴望着褚长者往下路去贩布,跟他回家。谁知褚长者年纪老迈,家道已富,褚妈妈劝他弃了这行生意,只在家中营运。文秀闻得这个消息,一发忧郁成病。褚长者请医调治,再三解劝。约莫住了一年光景,正值宗师考取童生。文秀带病去赴试,便得入泮。常言道:“福至心灵。”文秀入泮之后,到将归家念头撇过一边,想道:“我如今进身有路了,且赶一名遗才入场。倘得侥幸连科及第,那时救父报仇,岂不易如翻掌!”有了这般志气,少不得天随人愿,果然有了科举,三场已毕,名标榜上。赴过鹿鸣宴,回到家中拜见父母,喜得褚长者老夫妻天花乱坠。那时亲邻庆贺,宾客填门,把文秀好不奉承。多少富室豪门,情愿送千金礼物聘他为婿。文秀一心在父亲身上,那里肯要。忙忙的约了两个同年,收拾行李,带领仆从起身会试。褚长者老夫妻直送到十里外,方才分别。
在路晓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京都,觅个寓所安下。也是天使其然,廷秀、文秀兄弟恰好作寓在一处,左右间壁,时常会面。此时居移气,养移体,已非旧日枯槁之容了。然骨韵犹存,不免睹景思形。只是一个是浙江邵翼明贵介公子,一个是河南褚嗣茂富室之儿,做梦也不想到亲弟兄头上。不一日,三场已毕,同寓举人候榜,拉去行院中游串,作东戏耍。只有邵、褚二人,坚执不行。褚嗣茂遂于寓中治榼,邀请邵翼明闲讲,以遣寂寞。两下坐谈,愈觉情热。嗣茂遂问:“邵兄何以不往院中行走?莫非尊大人家训严切?”翼明潸然下泪,答道:“小弟有伤心之事,就是今日会试,亦非得已,况于闲串,那有心情!只是尊兄为何也不去行走?如此少年老成,实是难得。”嗣茂凄然长叹道:“若说起小弟心事,比仁兄加倍不堪。还仗仁兄高发,替小弟做个报仇泄恨之人。”翼明见话头有些相近,便道:“你我虽则隔省同年,今日天涯相聚,便如骨肉一般,兄之仇,即吾仇也。何不明言,与小弟知之?”嗣茂沉吟未答。连连被逼,只得叙出真情。才说得几句,不待词毕,翼明便道:“原来你就是文秀兄弟,则我就是你哥哥张廷秀!”两下抱头大哭,各叙冒姓来历。且喜都中乡科,京都相会。一则以悲,一则以喜。
春榜既发,邵翼明、褚嗣茂俱中在百名之内。到得殿试,弟兄俱在二甲。观政已过,翼明选南直隶常州府推官,嗣茂考选了庶吉士,入在翰林。救父心急,遂告个给假,与翼明同回苏州。一面写书打发家人归河南,迎褚长者夫妻至苏州相会,然后入京,不题。
弟兄二人离了京师,由陆路而回。到了南京,廷秀先来拜见邵爷,老夫妻不胜欢喜。廷秀禀道:“兄弟文秀得河南褚长者救捞,改名褚嗣茂,亦中同榜进士,考选庶吉士,与儿同回,要见爹爹。”邵爷大惊道:“天下有此奇事,快请相见!”家人连忙请进。文秀到了厅上,扯把椅儿正中放下,请邵爷上坐,行拜见之礼。邵爷那里肯要,说道:“岂有此理!足下乃是尊客,老夫安敢僭妄?”文秀道:“家兄蒙老伯收录为子,某即犹子也,理合拜见!”两下谦让一回,邵爷只得受了半礼。文秀又请老夫人出来拜见。邵爷备起庆喜筵席,直饮至更馀方止。
次日,本衙门同僚知得,尽来拜访。弟兄二人以次答拜。是日午间小饮,邵爷问文秀道:“尊夫人还是向日聘在苏州?还是在河南娶的?”文秀道:“小侄因遭家难,尚未曾聘得。”邵爷道:“原来贤侄还没有姻事。老夫不揣,止有一女,年十六岁了。虽无容德,颇晓女红。贤侄倘不弃嫌,情愿奉侍箕帚。”文秀道:“多感老伯俯就,岂敢有违!但未得父母之命,不敢擅专。”廷秀道:“爹爹既有这段美情,俟至苏州,禀过父母,然后行聘便了。”邵爷道:“这也有理。”正话间,只听得外边喧嚷。教人问时,却是报邵爷升任福建提学佥事。邵爷不觉喜溢于面,即分付家人犒劳报事的去了。廷秀弟兄起身把盏称贺。邵爷道:“如今总是一路,再过几日同行何如?”廷秀道:“待儿辈先行,在苏州相候罢!”邵爷依允。
次日,即雇了船只,作别邵爷,带领仆从,离了南京。顺流而至,只一日已抵镇江。分付船家,路上不许泄漏是常州理刑,舟人那敢怠惰。过了镇江、丹阳,风水顺溜,两日已到苏州,把船泊在胥门马头上。弟兄二人只做平人打扮,带了些银两,也不教仆从跟随,悄悄的来到司狱司前。望见自家门首,便觉凄然泪下。走入门来,见母亲正坐在矮凳上,一头绩麻,一边流泪。上前叫道:“母亲,孩儿回来了!”哭拜于地。陈氏打磨泪眼,观看道:“我的亲儿,你们一向在那里不回?险些想杀了我!”相抱大哭。二子各将被害得救之故,细说一遍。又低低说道:“孩儿如今俱得中进士,选常州府推官,兄弟考选庶吉士。只因记挂爹妈,未去赴任,先来观看母亲。但不知爹爹身子安否?”陈氏听见儿子都已做官,喜从天降,把一天愁绪撇帀,便道:“你爹全亏了种义,一向到也安乐。如今恤刑坐于常熟,解审去了,只在明后日回来。你既做了官,怎的救得出狱?”廷秀道:“出狱是个易事,但没处查那害我父子的仇人,出这口恶气。”文秀道:“且救出了爹爹,再作区处。”廷秀又问道:“向来王员外可曾有人来询问?媳妇还是守节在家,还是另嫁人了?”陈氏道:“自你去后,从无个小厮来走遭。我又且日逐啼哭,也没心肠去问得。到是王三叔在门首经过说起,方晓得王员外要将媳妇改配,不从,上了吊救醒的。如今又隔年馀,不知可能依旧守节?我几遍要去,一则养娘又死,无人同去;二则想他既已断绝我家,去也甘受怠慢,故此却又中止。你今只记他好处,休记他歹处。总使媳妇已改嫁,明日也该去报谢。”廷秀听了这话,又增一番凄惨,齐答道:“母亲之言有理!”廷秀向文秀道:“爹爹又不在此,且去寻一乘轿子来,请母亲到船上去罢!”文秀即去雇下。陈氏收拾了几件衣服,其馀粗重家火,尽皆弃下。上了轿子,直到河口下船。可怜母子数年隔别,死里逃生,今日衣锦还乡,方得相会。这才是:兄弟同榜,锦上添花;母子相逢,雪中送炭。
次早,二人穿起公服,各乘四人轿,来到府中。太爷还未升堂,先来拜理刑朱推官。那朱四府乃山东人氏,父亲朱布政与邵爷却是同年。相见之间,十分款洽。朱四府道:“二位老先生至此,缘何馆驿中通不来报?”廷秀道:“学生乃小舟来的,不曾干涉驿道,故尔不知。”朱四府道:“尊舟泊在那一门?”廷秀道:“舟已打发去了,在专诸巷王玉器家作寓。”朱四府又道:“还在何日上任?”廷秀道:“尚有冤事在苏,还要求老先生昭雪,因此未曾定期。”朱四府道:“老先生有何冤事?”廷秀教朱爷屏退左右,将昔年父亲被陷前后情节,细细说出。朱四府惊骇道:“原来二位老先生乃是同胞,却又罹此奇冤!待太老先生常熟解审回时,即当差人送到寓所,查究仇家治罪!”弟兄一齐称谢。别了朱四府,又来拜谒太守,也将情事细说。俗语道:“官官相为。”见放着弟兄两个进士,莫说果然冤枉,就是真正强盗,少不得也要周旋。当下太守说话,也与朱四府相同。廷秀弟兄作谢相别,回到船里。对兄弟道:“我如今扮作贫人模样,先到专诸巷打探,看王员外如何光景。你便慢慢随后衣冠而来。”商议停当。廷秀穿起一件破青衣,戴个帽子,一径奔到王员外家来。
且说赵昂二年前解粮进京,选了山西平阳府洪同县县丞。这个县丞,乃是数一数二的美缺,顶针捱住。赵昂用了若干银子,方才谋得。在家守得年馀,前官方满,择吉起身。这日在家作别亲友,设戏筵款待。恰好廷秀来打探,听得里边锣鼓声喧,想道:“不知为甚恁般热闹?莫不是我妻子新招了女婿么?”心下疑惑。又想道:“且闯进去看是何如。”望着里边直撞,劈面遇见王进。廷秀叫声:“王进那里去?”王进认得是廷秀,吃了一惊,乃道:“呀,三官一向如何不见?”廷秀道:“在远处顽耍,昨日方回。我且问你,今日为何如此热闹?可是玉姐新招了丈夫么?”王进在急忙间,不觉真心露吐,乃道:“阿弥陀佛!玉姐为了你,险些送了性命,怎说这话!”廷秀先已得了安家帖,便道:“你有事自去。”王进去后,竟望里面而来。到了厅前,只见宾客满座,童仆纷纭。分帀众人,上前先看一看,那赵昂在席上扬扬得意,戏子扮演的却是王十朋《荆钗记》。心中想道:“当日丈人赶逐我时,赵昂在旁冷言挑拨,他今日正在兴头上,我且羞他一羞。”便捱入厅中,举着手团团一转,道:“列位高亲请了!”廷秀昔年去时,还未曾冠。今且身材长大,又戴着帽子,众亲眷便不认得是谁。廷秀覆身向王员外道:“爹爹拜揖!”终须是旦夕相见的眼熟,王员外举目观看,便认得是廷秀,也吃一惊。想道:“闻得他已死了,如何还在?”又见满身褴褛,不成模样,便道:“你向来在何处?今日到此怎么?”廷秀道:“孩儿向在四方做戏,今日知赵姨夫荣任,特来扮一出奉贺。”王员外因女儿作梗,不肯改节,初时员外到有个相留之念,故此好言问他。今听说在外做戏,恼得登时气紫了面皮,气倒在椅上,喝道:“畜生!谁是你的父亲?还不快走!”廷秀道:“既不要我父子称呼,叫声岳丈何如?”王员外又怒道:“谁是你的岳丈?”廷秀道:“父亲虽则假的,岳父却是真的,如何也叫不得?”赵昂一见廷秀,已是吓勾,面如土色,暗道:“这小杀才已绑在江里死了,怎生的全然无恙?莫非杨洪得了银子放走了,却来哄我?”又听得称他是姨夫,也喝道:“张廷秀!那个是你的姨丈?到此胡言乱语!若不走,教人打你这花子的孤拐!”廷秀道:“赵昂!富贵不压于乡里,你便做得这蚂蚁官儿,就是这等轻薄。我好意要做出戏儿贺你,反恁般无礼!”赵昂见叫了他的名字,一发大怒,连叫家人快锁这花子起来。那时王三叔也在座间,说道:“你们不要乱嚷,是亲不是亲,另日再说。既是他会做戏,好情来贺你,只当做戏子一般,演一出儿顽顽,有何不可?却这般着恼!”推着廷秀背道:“你自去扮起来,不要听他们。”众亲戚齐拍手道:“还是三叔说得有理!”将廷秀推入戏房中,把纱帽员领穿起,就顶王十朋《祭江》这一折。廷秀想起玉姐曾被逼嫁上吊,恰与玉莲相仿,把胸中真境敷演在这折戏上,浑如王十朋当日亲临。众亲鼻涕眼泪都看出来,连声喝采不迭。只有王员外、赵昂又羞又气。正做之间,忽见外面来报,本府太爷来拜常州府理刑邵爷、翰林院褚爷。慌得众宾客并戏子,就存坐不住,戏也歇了。王员外、赵昂急奔出外边,对赍帖的道:“并没甚邵爷、褚爷在我家作寓。”赍帖的道:“邵爷今早亲口说寓在你家,如何没有?”将帖子撇下道:“你们自去回覆!”竟自去了。王员外和赵昂慌得手足无措,便道:“怎得个会说话的回覆?”廷秀走过来道:“爹爹,待我与你回罢!”王员外这时,巴不得有个人儿回话,便是好了,见廷秀肯去,到将先前这股怒气撇帀,乃道:“你若回得甚好。”看他还穿着纱帽、员领,又道:“既如此,快去换了衣服。”廷秀道:“就是恁般罢了,谁耐烦去换!”赵昂道:“官府事情,不是取笑的。”廷秀笑道:“不打紧,凡事有我在此,料道不累你。”王员外道:“你莫不风了?”廷秀又笑道:“就是风了,也让我自去,不干你们事。”只听得铺兵锣响,太守已到。王员外、赵昂着了急,撇下廷秀,躲进去了。廷秀走出门前,恰好太守下轿,两下一路打恭,直到茶厅上坐下攀谈。吃过两杯茶,谈论多时,作别而去。
却说玉姐日夕母子为伴,足迹不下楼来。那赵昂妻子因老公选了官,在他面前卖弄,他也全然不理。这一日,外边帀筵做戏,瑞姐来请看戏,玉姐不肯。连徐氏因女儿不愿,也不走出来瞧。少顷,瑞姐见廷秀在厅前这番闹炒,心下也是骇异。又看见当场扮戏,故意跑进来报道:“妹子,好了!你日逐思想妹夫,如今已是回了,见在外边扮戏!”玉姐只道是生这话来笑他,脸上飞红,也不答应。徐氏也认是假话,不去采他。瑞姐见他们冷淡,又笑道:“再去看妹夫做戏。”即便下楼。不一时丫鬟们都进来报,徐氏还不肯信,亲至遮堂后一望,果是此人。心下又惊又喜,暗叹道:“如何流落到这个地位?”瑞姐道:“母亲,可是我说谎么?”徐氏不去应他,竟归楼上说与女儿。玉姐一言不发,腮边珠泪乱落。徐氏劝道:“儿!不必苦了,还你个夫妻快活过日。”劝了一回,恐王员外又把廷秀逐去,放心不下,复走出观看。只见赵昂和瑞姐望里边乱跑,随后王员外也跑进来。你道为何?原来王员外、赵昂,太守到时,与众宾客俱躲入里边。忽见家人报道:“三官陪着太守坐了说话。”众人通不肯信,齐到遮堂后张看,果然两下一递一答说话。王员外暗道:“原来这冤家已做官了,却乔妆来哄我。懊悔昔时错听了谗言,将他逐出。幸喜得女儿有志气,不曾改嫁,还好解释。不然,却怎生处?只是适来又伤了他几句言语,无颜相见,且叫妈妈来做个引头。”故此乱跑。自古道:“贼人心虚。”那赵昂因有旧事在心,比王员外更是不同,吓的魂魄俱无。报知妻子,跑回房里,打点收拾,明日起身,躲避这个冤家,连酒席也不想终了。
且说王员外跑来撞见徐氏,便喊道:“妈妈,小女婿回了!”徐氏道:“回了便罢,何消恁般大惊小怪?”王员外道:“不要说起,适来如此如此。我因无颜见他,特请你去做个解冤释结。”徐氏得了这几句话,喜从天降,乃道:“有这等事!”教丫鬟上楼报知玉姐,与王员外同出厅前。廷秀正送了太守进来,众亲眷都来相迎。徐氏道:“三官,想杀我也!你往何处去了?再无处寻访!”廷秀方上前请老夫妇坐下,纳头便拜。王员外以手扶住道:“贤婿,老夫得罪多矣,岂敢又要劳拜!”廷秀道:“某实不才,不能副岳丈之望,何云有罪!”拜罢起来,与众亲眷一一相见已毕。廷秀道:“赵姨夫如何不见?快请来相会!”童仆连忙进去。赵昂本不欲见他,又恐不出去,反使他疑心,勉强出来相见,说道:“适来言语冲撞,望勿记开!”廷秀道:“是我不达,自取其辱,怎取怪姨夫?”赵昂羞惭无地。王员外见廷秀冷言冷语,乃道:“贤婿,当初一时误听谗言,错怪你了,如今莫计较罢!”徐氏道:“你这几年却在那里?怎地就得了官?”廷秀乃将被人谋害,直到做官前后事细说,却又不说出兄弟做官的缘由。众亲眷听了,无不嗟叹。乃道:“只是甚冤家下此毒手,如今可晓得么?”廷秀道:“若是晓得,却便好了!”那时廷秀便说,旁边赵昂脸上一回红,一回白,好不着急。直听到“不晓得”这句,方才放下心肠。王三叔道:“不要闲讲了,且请坐着,待我借花献佛,奉敬一杯贺喜。”众亲眷多要逊廷秀坐第一位。廷秀不肯,再三谦让不过,只得依了他。竟穿着行头中冠带,向外而坐。戏子重新登场定戏。这时众亲眷把他好不奉承。徐氏自归楼上,不在话下。
却说张权解审恤刑,却原是杨洪这班人押解。元来捕人拿了强盗,每至审录,俱要原捕押解。其中恐有冤枉,便要对审,故此脱他不得。那杨洪临起解时,先来与赵昂要银若干盘缠,与兄弟杨江一齐同去。及至转来,将张权送入狱中,弟兄二人假意来回复赵昂,又要索诈他东西。到了专诸巷内,一路听得人说太守方才到王家拜望。杨洪弟兄疑惑道:“赵昂是个监生官,如何太爷去拜他?且又不是属下。”到了王家门首,只听得里边便闹热做戏,门首悄悄的不见一人,却又不敢进去,坐在门前石上,等个人出来问个信。刚刚坐得,忽见一乘四人轿抬到门前歇下,走出一位少年官员,他二人连忙立起。那官员是谁?便是庶吉士张文秀。他跨入门来,抬头看见二人,到吃一惊。认得一个是杨洪,一个是谋他性命的公差。想道:“元来是他一路,不知为何坐在此间?”且不说破,竟望里面而去。杨洪已不认得,向兄弟说:“赵昂多大官儿,却有大官府来拜?”你道杨洪如何便认不得了?文秀当初谋他命时,还是一个小童,如今顶冠束带,换了一番景象,如何便认得出?文秀乃切骨之仇,日夜在心,故此一经眼,即便认得。
且说文秀走入里面,早有人看见,飞报进去道:“又有一位官府来拜了!”说犹未了,文秀已至厅前。众亲眷并戏子们看见,各自四散奔帀,又单撇下廷秀一人。王员外原在遮堂后张看,这官员却又比先前太守不同,廷秀也不与他作揖,站起身说道:“你来了。”那官府道:“如何见我来,都走散了?”廷秀忍不住笑。文秀道:“且莫笑,有句紧话在此。”附耳低声道:“便是谋你我的公差与杨洪,都坐在外面。”廷秀惊道:“有这等事!如何坐在这里?其中可疑。快些拿住,莫被他走了!”一面讨过冠带,换了身上行头。文秀即差众家人出去擒拿。廷秀一面换起冠带,脱下身上行头。
且说众人赶出去,掀翻杨洪兄弟,拖入里边来。杨洪只道是赵昂的缘故,口中骂道:“忘恩负义的贼!我与你干了许多大事,今日反打我么?”正在乱时,报道:“理刑朱爷到了!”众家人将杨洪推在半边。廷秀兄弟出来相迎,接在茶厅上坐下。廷秀耐不住,乃道:“老先生,天下有这般快事!谋害愚兄弟的强盗,今日自来送死,已被拿住!”朱四府道:“如今在那里?”廷秀教众人推到面前跪下。廷秀道:“你二人可认得我了?”杨洪道:“小人却认不得二位老爷。”文秀道:“难道昔年趁船到镇江告状,绑入水中的人就不认得了?”二人闻言,已知是张廷秀弟兄,吓的缩作一堆。朱四府道:“且问你有甚冤仇,谋害他一家?”二人道:“没甚冤仇。”朱四府道:“既无仇隙,如何生此歹心?”二人料然性命难存,想起赵昂平日送的银子又不爽利,怎生放得他过!便道:“不干小人之事,都是赵昂与他有仇,要谋害二位老爷父子,央小人行的。”廷秀弟兄闻言,失惊道:“元来正是这贼!我与他有甚冤仇,害我父子?”朱四府道:“赵昂是何人?住在那里?”廷秀道:“是个粟监,就住在此间。”朱四府喝声:“快拿!”手下人一声答应,蜂拥进去,将赵昂拿出。那时惊得一家儿啼女喊,正不知为甚。众亲都从后门走了,戏子见这等沸乱,也自各散去了。那赵昂见了杨洪二人,已知事露,并无半言。朱四府即起身回到府中,先差人至狱内将张权释放,讨乘轿子送到王家。然后细鞫赵昂。初时抵赖,用起刑具,方才一一吐实。杨洪又招出两个摇船帮手,顷刻也拿到来。赵昂、杨洪、杨江各打六十,依律问斩。两个帮手各打四十,拟成绞罪。俱发司狱司监禁。朱四府将廷秀父子被陷始末根由,备文申报抚按,会同题请,不在话下。
且说廷秀弟兄送朱四府去后,回到里边,易了公服。那时王员外已知先来那官便是张文秀,老夫妇齐出来相见。问朱四府因甚拿了赵昂,廷秀说出其情。王员外咬牙切齿,恨道:“原来都是这贼的奸计!”正说间,丫鬟来报,瑞姐吊死了!原来瑞姐知得事露,丈夫拿去,必无活理。自觉无颜见人,故此走了这条径路。王员外与徐氏因恨他夫妻生心害人,全无苦楚。一面买棺盛殓,自不必说。王员外分付重整筵席款待,一面差人到舟迎取陈氏。一时间家人报道:“朱爷差人送太老爷来了!”廷秀弟兄、王员外一齐出去相迎。恰好陈氏轿子也至,夫妻母子一见,相抱而哭。张权道:“我只道此生永无见期了,不料今日复能父子相逢!”一路哭入堂中。先向王员外、徐氏称谢,王员外再三请罪。然后二子叩拜,将赵昂前后设谋陷害情由,细细诉说。说到伤心之处,父子又哭。不想哭兴了,竟忘记打发了朱爷差人。那差人央家人们来禀知,廷秀发个谢帖,赏差人三钱银子而去。当下徐氏邀陈氏自归后房,玉姐下楼拜见,姑媳又是一番凄楚。少顷,筵宴已完,内外两席,直饮到半夜方止。
次日,廷秀弟兄到府中谢过朱四府,打发了船只,一家都住于王员外家中。等邵爷到后,完姻赴任。廷秀又将邵爷愿招文秀为婿的事,禀知父母。备下聘礼,一到便行。半月之后,邵爷方至,河南褚长者夫妻也到,常州府迎接的吏书也都到了。那时王员外门庭好不热闹。廷秀主意,原作成王三叔为媒,先行礼聘了邵小姐,然后选了吉日,弟兄一齐成亲。到了是日,王员外要夸炫亲戚,大帀筵宴,广请宾朋;笙箫括地,鼓乐喧天。花烛之下,乌纱绛袍,凤冠霞帔,好不气象。恰好两对新人,配着四双父母。
那府县官闻知,都去称贺。三朝之后,各自分别起身。张权夫妇随廷秀常州上任,褚长者与文秀自往京中,邵爷自往福建。王员外因家业广大,脱身不得,夫妻在家受用。
不则一日,圣旨颁下,依拟将赵昂、杨洪、杨江处斩。按院就委廷秀监斩。行刑之日,看的人如山如海。都道赵昂自作之孽,亲戚中无有怜之者,连丈人王员外也不到法场来看。
廷秀念种义之恩,托朱爷与他帀招释罪。又因父亲被人陷害,每事务必细询,鞫出实情,方才定罪。为此声名甚著。行取至京,升为给事。文秀以散馆点了山西巡按。那张权念祖茔俱在江西,原归故土,恢复旧业,建第居住。后来邵爷与褚长者身故,廷秀兄弟各自给假,为之治丧营葬。待三年之后,方上表,复了本姓。廷秀生得三子,将次子继了王员外之后,三子继邵爷之后,以表不负昔年父子之恩。文秀亦生二子,也将次子绍了褚长者香火。张权夫妇寿至九旬之外,无疾而终。王员外夫妻亦享遐龄。廷秀弟兄俱官至八座之位,至今子孙科甲不断。诗曰:
由来白屋出公卿,到底穷通未可凭。
凡事但存天理念,安心自有福来迎。
(《醒世恒言》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