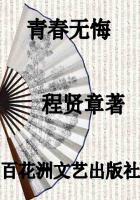“呼——呼——哧——”
张曼新和妻子朱宝莲偕同三个儿子乘坐的国际列车冲刺般抵达匈牙利共和国首府布达佩斯,几声长吁,疲惫不堪地卧在车站的铁轨上,如同一头刚刚驾车翻过高高山坡的牛。
经过七天七夜颠簸的张曼新,虽然胡子拉碴的,眼窝明显下陷,腮帮子有些往里抠,但他的目光却放射着斗士进入临战前的渴望与激昂。他一看手表,除去北京与布达佩斯之间七个小时的时差,正是凌晨五点二十八分。
布达佩斯,是个什么样子呢?张曼新此刻的心情,就像成年的小伙子第一次相亲,又激动,又慌乱。激动的是,毕竟马上要一睹女方的芳颜了;慌乱的是,对于对方的真面目是美是丑毕竟还不知道呀!况且,一家人下了火车,往哪儿去,他心里还没有底。但他又知道,现在自己就是一家人的统帅,统帅要是慌乱了,队伍会不战自乱。于是,他振作起精神,向家人一挥手:“布达佩斯到了,下车!”
“噢,下车喽!”年龄最小的儿子乐乐,像第一次到动物园似的高兴得又喊又叫。
蹦蹦和彤彤呢,他们虽然也有对出国的向往和对童话般欧洲风情的神思梦绕,但他们自从上了国际列车以后,看到车上大都是体态慓悍和神态高傲矜持的大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和由于语言不通形成的障碍,就大致感觉出到国外并不是原来想象的玫瑰花一样令人陶醉的乐园。
此刻,如果说心里真正忐忑不安和缺少欢乐的则是朱宝莲。
女人想问题往往底色是灰调子。
虽然他们在七天七夜的火车旅途中并不乏欢乐,每到一个车站都做生意,将带来的商品高价出售,随身携带的二锅头酒和服装到了莫斯科已经销售告罄,并着实赚了一笔钱。
看来,贫穷的东欧对中国的生意人来说可谓遍地是黄金。
要不到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人怎么会趋之若鹜?
不要说别的,当时一件羽绒服在俄罗斯能卖到比在中国高数倍的价钱。
难怪到俄罗斯的“倒爷”们都发了横财。
可是,这时的朱宝莲并没有因一路上赚了些钱而陶醉。一来她心里总是惦记着菲菲由北京回银川的路上病了没有?当菲菲知道自己被骗了,肯定会哭,会闹。这孩子气性大,哭起来没完。要是万一哭病了可怎么办呀?虽然张曼新的母亲周雪影会带孩子,但菲菲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自己呀!在孩子的眼里,妈妈的爱是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再有,就是朱宝莲脑子里有“在家千般好,出门事事难”的观念,一看到满街的大鼻子洋人,又是到了人家的国家,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忧虑。
布达佩斯火车站虽然没有北京火车站那样高大气派,却显得比北京火车站空旷,其原因是上下车的人很少。
人太少办不成大事。人太多大事也会变成小事。
张曼新走出车站,目光为之一亮。
只见车站前的大街,两厢都是清一色的七八层高的楼房,这些楼房由于大都是长方形石块砌成,威严地军阵般排列,显得格外雄壮。这些楼房从建筑风格看,德国式、罗马式和哥特式居多,几乎每幢楼房的顶端及门窗都饰有浮雕、圆雕和透雕,雕塑的人物几乎都是圣经故事和罗马神话中的爱神、战神等,加之街道是青砖铺地,路面由于多年汽车轮胎摩擦变得黑中透亮,泛着一种冷色调子,整条大街于古老中抖擞着中世纪奥匈帝国的凛然与强悍。
秋季的布达佩斯清晨,天高气爽,天宇碧蓝,清风阵阵,颇有几分凉意。
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起初都有几分惊奇,也有几分疑惧。
因为,在这起初的短暂瞬间,你会觉得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诞的梦魇。
蹦蹦经过短暂的喜悦之后,发现他的视野中没有他着意寻找的黑头发、黄皮肤长相的人,心里不由泛出几分惶惑,浑身不由微微一抖,悄声问张曼新:“爸,咱们去哪儿?”
“是呀,到哪里去呢?”透过张曼新四处张望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也在思考这个事关一家人有个安身之地的大问题。对匈牙利的国情,他不了解;对布达佩斯的市场状况以及城市的街道分布等,他不清楚;对于布达佩斯有没有中国人经商,他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是,张曼新决不是个莽撞汉子,而是一个具备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机变力很强的人物。
深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张曼新,临离开北京前,请人用英文写了一个路条:“Execuse me,Sir/Madam,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the address of Chinese Embassy in your country?Thank you!”(尊敬的女士和先生,请告诉我中国驻贵国大使馆的地址。谢谢!)如同珍宝一样带在身上。
此外,张曼新身上还有一本中英文的常用语对照词典。
于是,他果断地说:“先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在什么地方呢?”朱宝莲问张曼新,目光中燃烧起希望。
“这不,我带着路条哪!”张曼新得意地一笑,立刻取出来事先请人用英文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共和国大使馆”的字条交给蹦蹦,“你去找人问问,中国大使馆在什么地方。”
“嗯。”蹦蹦应一声,但从语气看有几分发怵。因为,他既不会英语,也不懂俄语和德语。
“哈罗!”蹦蹦只会用英语打句招呼,马上将字条交给一个迎面走过来的老者。
那老者端详了一下字条,表示不知道地双肩一耸,脸上有几分歉意地一笑,离开了。
“他怎么说?”张曼新急切地问道。
蹦蹦苦涩地一咧嘴:“他什么也没说,看样子他不懂英文。”
“那就再找个年轻一点的人问问。”张曼新告诉蹦蹦。
不大工夫,过来一个年轻女士,结果看过字条以后,礼貌地一笑,依然来了个“无可奉告”。
后来张曼新他们才清楚,匈牙利虽然属于欧洲,但本国使用的语言既不同于印欧语系中的印度语系、日耳曼语系、罗马语系和斯拉夫语系等,也与同属于乌拉尔语系的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有极大的区别,而是极特别的马扎尔民族语言。所以,由于整个匈牙利国家的一千多万人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马扎尔人,所以马扎尔的民族语言便成了匈牙利的“国语”。诚然,在匈牙利也使用英语和德语,那只不过在为数甚少的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人才能够交流,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只是懂匈文。
难怪蹦蹦一连吃了两个“闭门羹”!
不过,好事多磨。当蹦蹦问到一个中年男子,他不仅立刻“OK”了一句,而且还极热情地表示要将他们带到中国大使馆。
“谢谢。”张曼新一激动,说了句中国话,并连连点头表示感谢。他同时感到,匈牙利人对中国人热情友好,和善亲切。
那匈牙利中年男子将张曼新一家领上了公共汽车,前后又转了两次车,来到离大使馆不远处,做了一个“到了”的手势。
“谢谢!”张曼新以感激的笑靥作答。
可是,当他们细微一打量,只见房子上空飘扬的是越南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看来那个匈牙利男子把他们当成越南人了。
“不对,这是越南大使馆!”蹦蹦说。
“找到越南大使馆,就说明我们到了使馆区,再找中国大使馆就容易了。”张曼新安抚地说完,一扭头,突然像当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喜地喊道,“瞧,那不是中国大使馆吗?”
朱宝莲和蹦蹦顺着张曼新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马路对面,果然是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位于布达佩斯市六区班宗街十七号。
这座哥特式楼房,在临街的拐角处。门前是宽阔的街道,街道两边生长着葱茏的花木,加之街道路面洁净如洗,空气显得格外清新。
晨光熹微中的中国大使馆,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晨风中高高飘扬,像火炬般在熊熊燃烧。在门扉的右侧,一块镌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共和国大使馆”的铜匾在彩霞的辉映中鎏金闪烁,美轮美奂,门楣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宛如母亲亲切的笑脸,浮现着温存的慈爱。
作为海外游子的张曼新,作为举目无亲的张曼新,作为尚未有栖身之地的张曼新,此刻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看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字样,那激动,那喜悦,那亲情,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字眼儿来形容都不会过分。
“到家了!”张曼新两眼扑闪着激动的泪花,心里由衷地说。
是呀,中国大使馆在所在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权代表,把祖国视为母亲的海外游子们,怎么能不把大使馆看成是家呢?
既然到了家,自然就会产生进家的渴望和急切。
乐乐跑到大使馆门口,刚要挥起拳头敲门,却被朱宝莲制止住了:“不要敲,那红的小钮钮是门铃,你够不着,让你爸按。”
张曼新抢步上前,抑制住沸腾的心潮,用力按下了门铃。
“叮铃铃……”清脆的铃声,在门口响起,响亮悦耳,宛如伏天“咕咚咚”喝下几口冰镇汽水,透心的酣畅。
大约过了几分钟,大使馆的门方喑哑地开了。
但是,门只开了一个缝。
一个仿佛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将头探了出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中年女人问道。
张曼新急忙自报家门,脸上洋溢着喜不自禁的企盼:“我叫张曼新,我们一家人从中国来,刚下火车。”
“你们找大使馆干什么?”
“我们想通过大使馆了解一下匈牙利政府对中国人的投资政策。”
张曼新的话一说完,那中年女人一咂嘴:“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大使馆不掌握,你还得找匈牙利政府的有关部门去了解。”
张曼新苦涩地说:“可我们刚到匈牙利,语言又不会说,叫我们找谁呀!”
“你们要是真想了解什么,那就等上班后再来吧!”中年女人说完,将头缩回到门里,大门也随之一声不吭地关上了。
张曼新是怀着一颗冰凉和失落的心,两条腿似灌了铅一样沉重地离开大使馆的。
“老张头,咱们现在到哪里去呀?”朱宝莲见张曼新神色不爽,忧虑地问道。
“哦!”张曼新应一声,立刻意识到自己方才的情绪不对头。此时,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需要自己挺直腰杆,带领家人迎接困难,并战胜困难。只要你勇敢地面对生活,生活是会真诚地给你以回报的。
想到此,张曼新镇定情绪地引用了一句不知出自何种典籍的名句:“上帝关了所有的门,也会给人留一扇窗。”然后取出一封信,信封上用英文写着一个在匈牙利罗兰大学读书的中国女留学生的名字和地址。这个女留学生是张曼新的一个朋友的亲戚,他这个朋友告诉他,到匈牙利以后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找找她,并附了一封信。张曼新对蹦蹦说:“拦辆出租车,把这个信封上的地址叫出租车司机看看,去罗兰大学!”
这样,张曼新一家五口来了个“按图索骥”,顺利地来到罗兰大学,又顺利地找到了这个中国女留学生。
这位女留学生是姐弟二人,同在布达佩斯读书。她见张曼新是国内的朋友介绍来的,又是中国老乡,分外热情。她询问了很多国内的情况,并给张曼新一家做了一顿便饭,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信息,即匈牙利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后,鞋帽服装和日用品非常匮乏,一些从俄罗斯、印度、越南来的商人,还有极个别的中国人,在多瑙河畔摆摊,不过都是小本经营。
张曼新听了这个信息,心里像吃了颗定心丸,微皱的眉头熨平了。
饭后,张曼新带领家人来到一家青年旅馆,安顿了下来。
善于捕捉和利用机遇的张曼新,决心在多瑙河畔奋力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