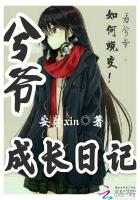诗中讲述了北方军队中一个阵亡的农民士兵家中的动人故事。士兵彼德负了重伤,住在医院里,即将牺牲。为了通知他的家庭,也为了安慰他的父母,由旁人用彼德的名义代写了一封信寄回家里。此时正是秋天收获的季节,父亲在田里劳动,母亲在家里。信差到了,门前游戏的年幼的妹妹从田里叫来了父亲,从家里叫来了母亲。丰收时节,果实累累,雨后晴空,美丽无比。年老的母亲带着不祥的预感来到门前。撕开信封一看,虽然签的是儿子的名,又是儿子的口气,但却是旁人的笔迹。信中告诉家里的人,他受伤住了医院,又安慰他们,“不久就会好转”。显然,安慰是没有用的。老母亲站立不稳,斜倚门柱,面色惨白,四肢无力。女儿们围在四周,大女儿在一旁安慰。但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早在母亲送她的儿子(“那个勇敢而单纯的灵魂!”)远征的时候,她已经准备着他的牺牲了。这首诗通过这个普通、朴素的故事,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些勇敢淳朴的农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最大,而战争之取得胜利,也正是由于这些勇敢淳朴的农民母亲和儿子。
诗人为我们塑造出一个非常感人的母亲的形象,同时,农民战士虽未出场,却也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眼前。这首诗的艺术技巧也很成熟,它既是一首叙事诗,诉说一段感人的故事,同时又是一首有动作、有对话的诗剧和抒发诗人主观感受的抒情诗。它还利用了对比的手法,用富饶、宁静的俄亥俄秋郊田野景色来衬托这幕悲剧,使之更加感人。
欲望三部曲
《欲望三部曲》是20世纪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的一部长篇小说,由《金融家》(1912)、《巨人》(1914)、《斯多噶》(1947)三部作品组成。最后一部由他的妻子续完最后一节,在他身后发表。
三部曲描写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攫取财富和权力的过程,揭示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德莱塞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好色而又贪婪的金融资本家柯帕乌的典型形象。小说以柯帕乌从发迹到死亡的一生为主线,以费城、芝加哥、纽约、伦敦等大城市为主要舞台,用大量生动的事实和逼真的画面,广泛地揭露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各个领域里的黑暗内幕。这是一幅以泼辣的笔和重彩浓墨所描绘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画卷,是较早描写垄断资本家的豺狼本性和丑恶灵魂的作品之一。
《欲望三部曲》的第1部写柯帕乌的发迹,写他因盗窃公库而入狱,被判4年徒刑。第2部写他出狱后野心不死,精力未减,重整旗鼓而一度成功,生活上也更加腐化,后来在竞争中遭到挫败,被迫离开芝加哥。第3部写他在芝加哥失败后,与英国金融资本家发生联系,把自己的资本投入伦敦地下铁道的建设工程,直写到他死亡。柯帕乌从一个掮客发迹而成为小商人、资本家、百万富翁以至金融巨头,一生道路上充满了血污和邪恶。他像一头野兽,一切行为全受贪婪残暴的本能所支配;也像野兽一样,虽困犹斗。他不知道有什么法律、伦理、道德。作者的生物社会学观点在这一形象上得到充分体现。他把资本家之追逐利润看作是资本家主观的、本能的、心理的特性,而不是导源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机制。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他对于柯帕乌的欲望冲动、精力、才干,有时也不免流露出欣赏的心情。
三部曲还通过资本家之间的一场场恶斗,生动地描绘了在资本兼并过程的残酷和不择手段。竞争双方不仅使用了经济手段,而且常常求助于政治手段以至刑事犯罪手段。小说接触到了资本与政治的关系,雄辩地揭露了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美国两党政治的虚伪性。金钱可以左右美国的政治,金钱可以买动一切,从流氓打手到两党要员,甚至资本家的老婆和女儿。
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的又一部作品。海明威一方面继承了马克·吐温等人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进行革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对现当代美国和世界文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丧钟为谁而鸣》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通过后方一支游击队的一次军事行动,展现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广阔画面。罗伯特·乔登是一个美国人,他自愿参加到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行列中。按照俄国将军戈尔兹的指示,他的任务是配合当地游击队在共和国部队发动进攻之前炸毁一座有战略意义的桥梁,以便阻止法西斯军队过河拦截。乔登与游击队员们一起呆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他发现游击队员士气低落,特别是他们的首领帕勃罗是一个狡猾的人,缺乏勇气,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念。乔登争取到帕勃罗的妻子皮拉尔的支持,游击队的其他成员也站到了乔登一边。但是内部尖锐的对立情绪以及一场严重的暴风雪增加了乔登的困难。附近山上另一支游击队的领袖艾尔·索多答应派人支持他,然而他们的行踪被敌人巡逻兵发现,他们虽然打死了敌人,却招来了法西斯飞机的猛烈轰炸。这时消息传来,戈尔兹将军的进攻计划可能已经泄露,法西斯军队已经作好了反击准备。
在这种形势下,乔登派人去向戈尔兹将军建议撤销原来的进攻方案,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当共和国军队进攻的信号打响时,乔登和帕勃罗的游击队炸掉了桥梁,乔登不幸受重伤,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对反法西斯正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心:“我们已经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奋战了一年,如果我们在这里取得胜利,我们就将在每一个地方取得胜利……”怀着这样崇高而坚定的想法,他掩护了自己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乔登也像《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一样厌恶和诅咒战争,在暴力和死亡的笼罩下为恐惧、噩梦所困扰。尽管如此,他却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他们两人身上那种迷惘与悲观的情绪,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而战,因而保持了较高的斗志。这样,海明威终于分清了战争正义与非正义性,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支持人民的立场。
小说中与乔登的军事行动这条线索交织进行的还有另一条线索,那就是乔登与玛丽娅的恋爱情节。玛丽娅的父亲是共和政府的一个市长,后来与玛丽娅的母亲一起遭到了法西斯匪徒的杀害。她自己也遭到长枪党党员的奸污。在游击队的山洞里皮拉尔精心调护她,使她身心迅速康复,并极力促成她与乔登的恋爱。尽管这种爱情显得有些过分浪漫,过分理想化,但正如亨利与凯瑟琳一样,男女主人公那种真诚相爱的精神毕竟是美好的,感人的。
第二十二条军规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瑟夫·海勒(1923~)的代表作,也是“黑色幽默”小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的作品虽不多,却在欧美各国有广泛的影响,对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品写的是二战期间,奉命驻扎于地中海“皮亚诺扎岛”(此岛为作家所虚构)上的一个美军空军大队的生活。小说没有统一完整的情节,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光怪陆离的场景构成了全书的内容。它分为42章,每章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讲述一个主要故事,再由贯穿全书的人物尤索林的经历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串联起来,从而形成一部结构貌似松散,实则各章之间有内在联系的长篇小说。
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是些荒谬绝伦的形象,性情古怪、情感冷漠、行为疯狂、不可理喻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全都无法按正常人的标准去衡量。
指挥这支飞行大队的司令官卡思卡特上校,是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冷酷无情的家伙。他为人圆滑,八面玲珑,36岁就当了上校、指挥官,为此他洋洋得意,自命不凡。一想到许多年纪比他大的人连个少校都还没混上,他便心花怒放,觉得自己已是个实权在握的大人物。与此同时他又常常痛苦不堪,因为有些比他还年轻的人已当上了将军。每念及此,他便嫉妒得发疯,恨得咬牙切齿。因此他时而踌躇满志,时而忧伤自怜,时而气概非凡,时而沮丧懊恼,时而胆识过人,时而怯懦畏缩。狂妄与自卑奇妙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为了向上级邀功,早日实现爬得更高的野心,他打着为国尽忠的旗号,不断增加部下的飞行次数,用飞行员的鲜血去为自己铺路架桥,弄得人人怨声载道。
专管部队队列操练的谢司科普夫少尉同样是个不择手段博取功名的野心家。他表现欲极强,“大战爆发他颇为高兴,因为战争使他有机会可以每天穿上军官制服,用清脆、威严的嗓音冲着一群群小伙子喊一声:‘弟兄们!’”为能够让自己训练的中队在阅兵式中得到第一,他绞尽脑汁,甚至想过把每列12人“钉在一根长长的2英寸厚、4英寸宽的栎木桁上,好使他们在行进时步调一致。”为此还需“在每个人后腰上插入镍合金做的旋转轴承,否则他们就不能作90°的转弯。”只是因为他拿不准军需主任是否供应那么多的轴承、外科医生是否肯与他合作,才万分惋惜而罢了手。最后谢司科普夫终于设计出不挥动双手行进的队列姿势,在阅兵式上一举成名,被誉为“军事天才”,从此青云直上,官至将军。
下级军官迈洛的所做所为更让人瞠目结舌。这个年仅27岁的伙食管理员大发战争横财,手段之“高明”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起先,他用美军的作战飞机作国际贸易,利用不同国家,前方和后方的商品差价赚钱。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他竟成立了庞大的跨国公司,各国军政要员纷纷入股,甚至连敌对国德国的政府也是股东之一。于是不同国家的运输机、轰炸机、歼击机都成了迈洛任意指挥的工具,每天“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挪威、丹麦、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芬兰、波兰以及欧洲各地之间”,机身上拖着五颜六色的广告牌,飘摇翻飞,构成空中一大景观。迈洛最后竟神通广大到承包“战斗工程”,和美军签订合同去轰炸德国桥梁;同时又与德军订立契约,让高射炮去打美国的飞机,两头捞取好处。干这一切时迈洛理直气壮,认为这纯属商业活动,他恪守的是商业道德。这表明迈洛之流的心中根本就没什么祖国的概念,凌驾一切之上的只是利益原则。对这场战争而言,这不啻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飞行大队中有位随军牧师,负责士兵的信仰。却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其表现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身份极不相符。他不断被一些“苦恼的、重大而复杂的本体论问题”折磨着:“有没有一种真正的信仰,或者死后有没有灵魂?有多少天使能够在一根针尖上跳舞?在创世纪前的那无数年代里,上帝自己究竟在忙着干些什么?”牧师无时无刻不想回家,老是在幻觉中看到妻子、孩子、岳母惨遭不幸,看到自己家的房子着了火。其实他本人也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他的信仰是“祖先们”传下来的。他不得不相信主的存在,因为正是对这个“永久的、全能的、无所不知的、相信人道的、全人类的、拟人的、能操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亲美的”上帝的信赖,才支撑他度日如年地活下去。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尤索林。他最初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入伍,到头来却发现这场战争不过是场骗局。上司们只顾升官发财,米洛这种无耻之徒在大战中如鱼得水,越是卑鄙的家伙就越能名利双收。士兵们的牺牲毫无价值,更没有丝毫崇高感。于是他成了不可救药的厌战者和怕死鬼,千方百计地想脱离战争。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凡是精神病患者就可以被遣送回国,尤索林认为有机可乘。但该军规又规定,凡想回国者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说明自己不能再飞行;而既能提出申请,就说明申请者不是精神病人,因此还得飞行。尤索林又寄希望于飞满规定的次数后停止飞行,第二十二条军规明确规定,飞满32次的飞行员即可不再执行飞行任务。可尤索林完成规定次数后却仍不能停飞,因为军规还有一个附加条件:飞行员终止飞行前必须执行长官的命令,而卡思卡特上校的命令使他必须继续飞行。尤索林一直飞到50次仍不能如愿,最后他终于彻悟到第二十二条军规不过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圈套,自己根本就无法摆脱它的控制。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表层意义十分明显,暴露美国军事官僚机器的黑暗和不人道,揭穿了美国政治与军事政策的伪善本质,但这并非小说的根本主题。它真正要告诉人们的,是现代西方社会的荒谬性。事实上,战争只是一个喻体,“第二十二条军规”是对一个毫无理性可言的世界的高度象征。它无处不在,俨然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神秘力量,操纵着芸芸众生。它肆意嘲弄人类建筑在理性基础上的宗教、道德和社会结构,使人生的意义变得荒诞不经。它看似无形,实则是一张天罗地网,人类的任何挣扎都无济于事,只能是越陷越深。因此,小说是对二战之后西方人生存状况的深刻揭示。
《第二十二条军规》具有典型的“黑色幽默”风格。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以反讽为基础的艺术构思上。作家认为,世界不可理喻是不可更改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荒诞的。既然这是一个倒错的社会,那么正常的人类生活准则就成了不正常的,不正常的东西反而成了正常的。在这种构思上的反讽中,幽默的效果就产生了。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为部队帐篷的门朝哪个方向开而大打官司的佩克姆将军和德里德尔将军,看到了因设计出让士兵双臂不动的行进模式而一鸣惊人的谢司科普夫少尉,看到了同时承包炸桥和保桥的迈洛,看到了坚持一丝不挂、游来荡去的尤索林……作家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把这一切当作正常的东西呈献给读者,而读者在领悟了其潜台词完全对立的含义后,禁不住便露出一个苦涩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