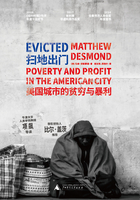天寒地冻,电话里的声音也如冰凌一般晶莹剔透,心底有蓓蕾初绽,然而,只含苞默念。有些话语,只适合开在心里,有些情怀,只能默默凋零。
冬至那天,风烟俱净,我站在三层楼上的长长的阳台上,看清晰的远山,看疏朗的枝条,享受着透明的阳光,觉得整个冬天都是明净的了。
假日一天,慵慵晨起,洗漱用餐锅碗洗净,恍知要参加儿子的年终英语汇报,遂急急披衣冒雪驰行,入室,抖不落沾衣的白雪,坐定,看孩子们轮番上演,时时望望窗外飘飞的白雪,竟有恍如时空穿越的迷离之感。
午饭后,稍事休息,开始张罗着找衣服洗澡,洗完澡,把换下的衣服一一收进水盆里,趁洗衣机忙活的当儿,我们做熟了晚饭,吃罢,再等洗完衣物,洗了拖把拖了地,又该催促着儿子上床休息了。
当一切停顿下来,我坐在电脑前,开始没有目的地闲逛。没有喜欢的文章,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看一场电影,如此浑浑噩噩,时光如沙漏般悄然而下,当关掉全部网页的那一刻,蓦然想到,哦,冬天在哪呢?在室外吧。一天,转眼就要过去了,可我还没出门到那透亮的寒气里走走呢。
可是,看看时钟,已经22点多了,走到阳台上,一股寒气袭来,看看天幕,只看到一颗模糊的小星星,对面的房子上,地上,依然残存着雪。拉开一点窗缝儿,一股清凉的冷气扑来,令我顿时对身后的暖气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排斥感。一天的忙碌,我在这暖气屋子里待得竟忘记了空气的流动,忘记了内心的渴望,是适应了,还是麻木了呢?动则生静,静极思动,莫非是天地之道?
记得十年前的一个暑假,我有十多天自己待在漂白了的四壁间,除了下楼买了两三次食物之外,竟能做到足不出户,不管风花雪月,那时,我是那么安于孤单。那年的冬天,家里没有暖气,我每天晚上都和五六岁的儿子在泡沫垫上拉着手跳,直跳到筋疲力尽,气喘吁吁。那时,我很渴望在冬天能拥有花房一样的暖。然而,现在,当回首之际,猛然看到渐多的白发,不再青春的脸,心底陡然一惊,又即刻释然,而心,才开始回归,想弄懂自己活着的意义。
我的确渴望逃离身后的暖了。
身后的暖,是静止的暖,几盆花草也难以调节的沉闷的暖。回头望着饮水机上的吊兰,上面的叶子披下来,下面新生出的小叶子却倔强地要往上长,我不知道那新生的叶子为什么如此这般,就像我说不清为什么此时,在冷与暖的分界处,我欲乘风而去。我想,如果我在外面奔波太久,一定也会怀念这屋子的暖,然而,我在暖里,却不可遏制地向往着冷了。
我需要暖意,就像心里不能没有春光,我也爱着姹紫嫣红,然而我无法不深爱着冬的皎洁,冬的深邃,冬的悠远。
乱花迷人眼,固然可爱,然而,容易让人沉醉不知归路,我爱冬天,就像爱着那个不会醉酒的男人。
天寒地冻,电话里的声音也如冰凌一般晶莹剔透,心底有蓓蕾初绽,然而,只含苞默念。有些话语,只适合开在心里,有些情怀,只能默默凋零。只是,我自己知道,有些美丽,不是为了观赏,单单是用来感觉的。
花落花开,我自欣喜。
静静地思念,无奈地惦记,看看你,就走开。
女人是花,总要有一个季节,忘我地开。只是,我选择了冬季。
没办法,冬天,我第一次睁开眼,就遇到了清澈的冬天,清澈的你。
思绪兀自缭绕不绝,然而我终究没有出去。听着闹钟的滴答声,我辗转反侧,久久未眠,内心的动乱让我更加渴望冬天的静谧与辽阔。
懵懂着又过了一天,本想步行回家的,好在路上好好感受冬意婆娑,然而,一个同事驱车停在路边,非要拉我上车,盛情难却,只好连声感谢着。推开家门,冬天也仿佛关在了门外。等吃罢晚饭收拾妥当,走出来,在薄雪里走着,在冷冷的灯火阑珊里走着,思想也格外清晰透亮,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内心,也如此冷澈,如此清醒。我不能完全懂得整个世界,但我可以努力懂我自己,于茫茫之中,我微乎其微可有可无,然而,我只要知道我是如此清醒地爱着,如此深挚地爱着,我就没有理由不感激生命的美好与可爱。
不问念从何起,也不问情归何处。我喜欢所有的季节,只要季节里有你,我爱所有的冬天,只要冬天里有你的气息。
这个冬天,清澈如你。
哲学家是忠于智慧和健全理智的,因而是坏蛋贼骗子。社会应该使仇恨教会的人受火刑。这些恶棍竟提醒人们当心:在尘世,不要两眼朝天被掏走钱袋。
——霍尔巴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