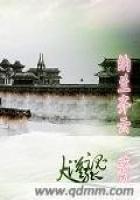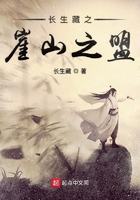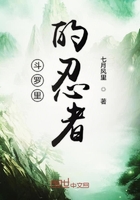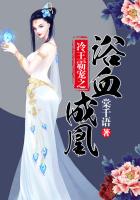一 半个字的电报
这篇关于沈从文的短文,写在1988年5月9日。本来是准备给沈从文看了逗他取乐的。想不到沈从文在第二天就去世,没有能看到。现在沈从文去世已经四个年头了。我把这篇短文找出来,略作修改,予以发表。这样,一篇取乐的短文,竟变成了悼念的祭文。
1988年4月6日上午10点多钟,我陪同台湾的青年作家张大春,到北京崇文门东大街22号,访问我的三妹夫沈从文。虽然大门上贴着“免进牌”,我们还是破门而入。
我向沈从文和三妹兆和介绍了张大春。三妹沏上一壶湖南绿茶。咱们坐下聊天,聊上一大堆旧事和笑话。前三朝,后五代,谈文章,扯家常。不知为什么,一扯就扯到了我那“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笑了,指着我轻轻地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我提出抗议:“你说什么?”他用浓重的湖南腔重说一遍:“媒婆!”我说:“我做了你们的大媒,不感谢我,反而说我是媒婆?”话未落音,三妹抢着说:“你不仅做过媒婆,还做过收生婆呢!”
三妹说得没错。我自幼好管闲事。抗战时期,逃难到四川乡下,到处缺医少药。我凭一点卫生常识,常常施医给药、替孩子种牛痘、开刀挤疖子、给人打针,什么都干,像一个免费的“赤脚医生”。我又在江安,给戏剧家蔡松龄的夫人接生,难产变成顺产,生下一个大胖儿子,我给起名“安安”,做了我的干儿子。直到一个做护士的表妹骂我:“瞧你不要命!你又不是医生或护士,一针把人戳死了怎么办?”这才洗手不干这些三姑六婆的营生。
为什么说到“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就要说我是“媒婆”呢?这件事,四妹充和在她写的《三姐夫沈二哥》文章里首先提到。后来凌宇先生在他的《都市中的乡下人》一书里也谈到,可是都谈得太简单,看来我不得不再给他们二人做个注解。下面我把可笑的历史往事从头说起。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十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家看门的吉老头儿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个客人一听,不但不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面发愣。吉老头儿抱歉地说:“您莫走,我去找二小姐。”
我家有个大小姐,常常不在家。我这二小姐成了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出三个字:“我走吧!”他这话好像对我说,又好像对他自己说。我很快把话儿转个弯:“太阳下面怪热的,请到这边阴凉地方来。”可是他巍然不动。我无可奈何,只好说:“那么,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他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三妹回来吃午饭。我怪她:“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三妹不服气:“谁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我说:“别说了,吃完饭,马上去。他是老师么!”我告诉她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三妹吃了一惊:“旅馆?我不去!”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三妹是他的学生。
“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我说。
三妹只是摇头。
我为她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好办法。就说:“还是要去,大大方方地去。来而不往,非礼也。究竟是远道来的老师呀!”
三妹不得不同意。她问我:“怎样开口呢?”我说:“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说:“好,听你的。”她终于去了。
去了不到一小时,三妹同沈从文来到我家。三妹让五个弟弟轮流陪伴沈先生。沈从文善于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听得最起劲的是最小的小五弟。故事一直讲到小主人们被叫去睡觉为止。我呢,不做臭萝卜干,早托词走开了。
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在我家作客。几天后,回到他当时教书的青岛大学。次年,由于沈从文的介绍,三妹也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了。
那年在苏州的旅馆,他们俩见面时候是怎样开腔谈话的呢?几十年后,我才知道。
1969年9月,沈从文和三妹已经结婚36年,住在北京。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三妹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俩先后下放湖北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三妹先走,沈从文晚了好几个月才去。沈从文下放前一天,我去送行。闲谈中,他告诉我36年前的情景:
“那年我从苏州九如巷闷闷地回到旅馆,一下躺倒在床上,也无心吃中饭。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身背后。我请她进来,她却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把我教她讲的话,一字不差,背了出来!
1933年初春,我和三妹一同住在苏州。一天,三妹给我看沈从文给她的信。信中婉转地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我准备了一番话给报务员做解释。想不到报务员匆匆一看,就收下了电报稿,没有问什么。我得意洋洋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一人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报务员看了电报稿,觉得很奇怪!密码?不收!报务员要三妹改写文言,三妹不肯。三妹涨红了脸,说这是喜事电报,说了半天,报务员才勉强收下。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天长地久有时尽。这“半个字”的电报,以及这个白话文的“蜜”电,在三妹和沈从文的心中将是天长地久永无尽的甜蜜记忆。
(原载1992年7月《群言》杂志)
二 一封快信和一页日记
一封快信
大春:
5月9日晚上,我把《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的初稿写好。松了口气,晚上睡得很沉。
10日晚7时多,得三妹电话,说沈二哥不好,我就揪心了。九时多得我的堂妹夫王正仪医生电话,说沈二哥在8点35分去世。这一夜我和有光都觉得心绞痛。虽然是意料中的事,可是怎样也拨不开沈二哥的身影。这时候距离我的《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脱稿只有24小时。我准备等我的文章发表后要宣读给沈二哥听,让他再笑我、骂我。这下再不能听到沈二哥骂我的声音了。他骂我“媒婆”的笑语声还在我耳边回荡。
你可能是最后一位由台湾来见到沈从文的人。你见到他34天后,他就离开了他爱的人、他爱的世界。
附日记一页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一文,没有心情修润改错,望你为我修理修理。
一页日记
1988年5月11日,下午2时35分,我们到沈从文家。进门,家里比平时更安静。客堂里,沈二哥的一张照片被披上了黑纱,照片前的茶几上有一篮绚丽多彩的鲜花,这是小龙朱的花场的花,是二哥的大儿子小龙朱亲手栽培的花。我们只默默地注视着沈二哥的照片,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1982年,沈从文、张兆和在北京家中(李又宁摄)
孩子们说,三妹在休息。我轻轻推开沈二哥和三妹卧室的门,三妹站在床前,并没有睡。我轻轻抚摸着三妹的手,我们在书桌边坐下。三妹很平静安详。我默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倒是三妹先开了口,像叙述一件别人的事。她说:“二哥昨天下午四点多钟时,还扶着四妹充和送他的助行器笑着走路。五点多钟二哥感觉气闷和心绞痛,我扶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他不让我离开他,但又说要送他上医院。”当时家里只有三妹一个人和一位刚请来不久的男保姆。三妹安慰了他,匆忙打了几个电话。三妹又说:“过去在他五年的病中,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
“先是20号楼(三妹家住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我们的堂妹夫王正仪医生来了,摸摸脉、听听心脏,不言语。随后救护车和医生来了,历史所里的王序、王亚蓉来了,家里人也陆续回来了。进行抢救,打了三针强心针,几位医生护士轮流进行人工呼吸和按摩心脏,一直到晚上8点35分……”
三妹回头问她的小儿媳张之佩说:“给二姨倒茶没有?”我说:“已经有了。你这五年也太累了。除了照应沈二哥,你什么也做不了。”
三妹还是那样镇定、安详。这安详内含着一颗哀沉的心。
三妹低沉的声音:“是的,我很佩服冰心,她的身体比我坏得多,可是她还在写。我要学她,这以后,我空了,我要写二哥,写他最后的五年,写……”
写吧,这是最大的安慰,对过去的人、对现在的人、对未来的人!
1988年5月12日
三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上海有一条最早修筑的小铁路,叫淞沪铁路,从上海向北到炮台湾。
英国怡和洋行在同治年间(1862—1874)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自行开始修筑这条铁路。到光绪二年(1876)完工。从上海到吴淞镇,路长只有14公里。第二年(1877),清政府认为外国人居然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这条铁路就破坏了风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跟怡和洋行进行了无数次的交涉,出钱把铁路买到中国手中后,在愤怒之下,下令拆毁。把机件等物储存在炮台湾。经过了漫长的20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新拨官款在原地修复通行。因为机件在炮台湾,淞沪铁路由吴淞镇延长两公里,全长为16公里。
中国公学就在吴淞镇和炮台湾之间,它们三个所在地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国公学的同学都以学校在中国第一条铁路所在地为荣。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预科的。这时候三妹17岁、我18岁,第一条铁路整整30岁(如果不算前20年的账)。
我和三妹不但同时进中国公学,还在她三岁我四岁同时(1913)在上海同一天开蒙认方块字,念“人之初”。四年后(1917)搬家去苏州,同在家塾里,同在一个桌子上念《孟子》、《史记》、《文选》和杂七八拉的“五四运动”的白话文。我们三个女学生(大姐元和、我、三妹兆和)很阔气。有三位老师:一位道貌岸然的于先生专教古文,另一位王孟鸾老师教白话文,这是两位男老师。有一位吴天然女教师,是教我们英文、数学、跳舞、唱歌的。在《三叶集》(叶圣陶的子女写的集子)好像提到过她,吴天然老师是教过我们A、B、C、D的。又四年(1921)我和三妹又同时进入苏州女子职业学校,读了一年,我们又同时留级,因为除中文课程外,其他课程都不及格。我们两姐妹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患难姐妹。
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在中国公学读完了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我却先后读了三个大学。在中国公学两年,一年预科,一年“新鲜生”。就转学光华大学,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学。“一·二八”战争,苏州到上海火车不通,我坐轮船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了一学期。最后,又回到光华大学戴方帽子的。
大学里收女生是新鲜事,男生对我们女生既爱护又促狭。他们对女生的特点很清楚,挨个儿为我们起绰号。世传三妹的绰号“黑凤”,并不是男生起的,这名字我疑心是沈从文起的。原来男生替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我有两个绰号,一个叫“鹦哥”,因为我爱穿绿;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可这个绰号见过报的。你如不信,可在1928年上海《新闻报》上找到这么一篇新闻,《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平时有‘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五个姓张的是:张兆和、张允和、张萍、张依娜、张××。队长是三妹。我对运动外行,身体瘦弱,人一推就倒。可我喜欢滥竽充数,当一个候补队员也好。
我家三妹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参加的五十米短跑是最后一名。
中国公学的老校长何鲁,忽然下了台,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接任校长是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他早年曾在中国公学念过书,他聘请了几位新潮流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就是沈从文。三妹选了他的课,三妹下了第一堂沈从文先生的课,回到女生宿舍,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
别瞧三妹年纪小,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这些“纸短情长”的信,一律保存,还编上号。这些编号的信,保存在三妹好友潘家延处,家延死后,下落何处,不得而知。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这封信可没有编号,如果编号也许是13号。当然,三妹没有复信。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据三妹说,原封不动退回。第四封以后的信,没听见三妹说什么,我们也不便过问,但是知道三妹没有复信,可能保存得相当周密。
我转学到上海大西路光华大学(1929),这以后,沈从文究竟给三妹多少封信,我当姐姐的不好过问。是不是三妹专为沈从文编过特殊的号,这也是秘密。
大概信写得太多、太长、太那个。三妹认为老师不该写这样失礼的信。发疯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对我说:“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我问她:“去做什么?”她说:“我跟校长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校长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三妹急红了脸:“不要讲!”校长很郑重对这位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三妹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以上是三妹亲口跟我讲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可是我们两姐妹都有了孙女时,偶尔谈到“顽固地”“爱他”和“不爱他”时,三妹矢口否认跟我说过这些话。
光阴如箭,这箭是火箭,人过了25岁后,觉得日子过得比过去快上一倍。一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这半个世纪中,我和三妹同年(1933)结婚,我嫁周耀平(现名周有光),她嫁沈从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儿子,我的儿子叫小平,她的儿子叫龙朱。“卢沟桥事变”,我们两家分开。她老沈家住云南呈贡,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从成都到重庆,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后搬家30次以上。
日本投降后1946年,张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会,照了十家欢。这以后又各奔前程。从此天南地北、生离死别,再也聚不到一起了。一直到1956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三弟定和跟我三家。算是欢欢喜喜、常来常往过日子。十年后(1966),猛不丁地来了个“文化大革命”,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离子散。两年后,北京三家人家只剩下四口人:沈家的沈二哥、张家的张以连、我家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连连12岁独立生活,我的孙女小庆庆九岁。三妹下放湖北咸宁挑粪种田,听说还和冰心结成“一对红”。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儿子晓平(小平)、媳妇何诗秀先后下放湖北潜江插秧、种菜。我家爷爷(周有光)下放宁夏贺兰山阙的平罗。捡种子、编筛子、捡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会、认罪会。大会多在广场上开。有时遇到黑黑的空中大雁编队飞行,雁儿集体大便,弄得开会的人满头满身都是粘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难洗干净。我家有光幸亏戴顶大帽子,总算头上没有“鸟便”。有光跟我谈起这件事,认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看来大雁比人的纪律性还强,所谓“人不如禽兽”。
本来也要我带庆庆跟着爷爷下放平罗的。我思想搞不通,不去,就不去,动员我也不去,也无可奈何我。我是娇小姐,受不了那塞外风沙,也吃不下为三个人打井水、洗衣服、生炉子烧饭的苦。我一把锁锁上了城里沙滩后街55号大杂院里我住的房子的大门(原有五间半房子,上缴了四间),住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里儿子家,看孙女烧饭。靠丈夫、媳妇三人给我的微薄津贴打发日子。真正不够用时,我有好亲戚好朋友处可借。虽然他们生活也不好,可他们总会竭力为我张罗。我一辈子怕开口问人借钱,这下子完了,只好厚着脸皮乞讨,这也是人生应有的履历。
过年过节,我把12岁的小连连接到中关村住几天,庆庆就不肯叫他“叔叔”,瞧不起他。庆庆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叔叔,他只比我大三岁,他没羞没臊,还抢我糖吃。我不但不叫他‘叔叔’,也不叫他‘连连’,我叫他‘小连’。”我骂庆庆,太没有礼貌。实在那时候,孙子骂爷爷,儿子逼死妈妈的事多着呢,还讲什么礼貌。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70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1988年5月9日晚初稿成
于沈从文二哥逝世前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