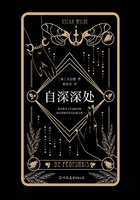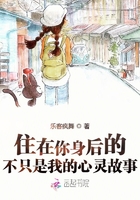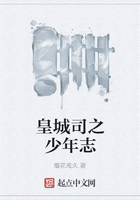这间教室就是右边那幢外墙砖泥混筑、内里木构楼房的底层。后来它很快不再做教室了,而是成为宣传队的排练室。带宣传队的是两个女老师,一个白胖一个黑瘦,白胖的那个就住在楼上,她是主要负责的,可能为了方便,她把排练安排在楼下。一年多以后,才转到左边那座内里被拆空的大房子里。
跳新疆舞时,需要学会扭脖子,就是那种身子不动,脖子左一下右一下移来移去的动作,看似容易,其实很难。八个女孩被一胖一瘦的老师一个个拉到门后,一个身体被门板夹住了,其余的人嘻嘻哈哈地挤在门后用力推着,然后老师双手托住你下巴,向左扳向右扳。我怕痒,老师巴掌一伸向下巴两侧,还未触及皮肤,我就先缩起脖子咯咯咯笑。老师脸一下子黑了,推肩膀、扳脑袋,下手很重。这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演出已经迫在眉睫,而演出是政治任务。
那扇夹身子的门就在木构楼房的底层,我曾经削破大拇指的地方。
3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再也不需要进入课堂了呢?完全想不起来了。“文艺汇演”这个词现在已经消失,当时却极其亢奋地盛行着。我相信,整个公社的盛行首先是因为父亲。“汇演”的全称应该是“汇报演出”--说是向贫下中农汇报,最终却演变成了各个中小学间的竞赛,与学校的面子密切相关。一台晚会下来,节目彼此串在一起,谁优谁劣谁强谁弱一目了然。
就较上劲了,不敢轻视。全公社各小学中能与我们抗衡的是十几公里外靠乌龙江边的一所,那里有位知青以前在城里是宣传队的,因为舞跳得好,被招去当民办老师,专门带宣传队。那所小学在排什么节目、跳什么舞,是我们老师需要搜集的情报热点。到了汇演时,其他小学的节目我们可以懒得看,那所小学从服装到在台上的一举一动却必须纳入我们视野,老师挤在幕布旁盯着看,看完再拿人家做榜样,告诉我们时不我待。
为了排练,已经不用上课了,每天空着手去学校,进的不是教室,而是那间木构楼房的底层。每次排的都不止一个节目,三五个总得有,以防这个节目栽了,还有另外的补救。
我渐渐觉得这件事有趣起来,不用上课是其一,其二是每次演出后公社食堂都备有夜宵,咸菜粥为主,不限量尽管吃。挤挤挨挨的一群人,脸上都还留着泛起油光的彩妆,再熟悉的彼此都陌生了几分。那时有几人肚子里油水过剩?三餐之外多出来的这一餐,就像中了大奖,哧溜哧溜的喝粥声在浓郁的脂粉味中响成一片。
当然,最重要还是因为服装。平时只能穿简衣陋衫,裤子短了,接上一截,衣裳破了,补上一块,而一旦演出,却可以花枝招展,红衣绿裙次第而来。
《红太阳照边疆》《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是朝鲜舞,《向着北京致敬》
《北京的金山上》是藏族舞,《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是蒙古族舞,《阿佤人民唱新歌》是佤族舞,《万岁毛主席》是新疆舞……我后来对北方的向往或许正始于此,朝鲜族、蒙古族、维吾尔族都在北方,而藏族、阿佤以及彝、苗等族虽在西南,当时我却辨不清方位,所有的遥远都归于可望不可即的北方。
服装常常是老师带我们一起制作的。先在自己头上量出尺寸,用铁线箍出一个圆圈,然后再以蓝、红、绿等碎布条绕着铁线编出五彩辫,一圈编满了,留一撮近尺长的布条垂在左侧,这是跳藏族舞时必须的;新疆舞的帽子,用料节俭,把硬纸皮剪出瓜瓣似的弧形,以订书钉固定住顶部,用广告颜料画上花纹,两侧再各钻个孔系上一根橡皮筋就成了。演出时把橡皮筋勒到下巴,怎么蹦跳旋转,帽子都不会甩下来。
新疆舞的黑绒布背心跳藏族舞时也可以混用。背心是请服装店的师傅做的,绒布在当时算是奢侈品了,灯光下能泛起光泽,但还不够抢眼,必须把金银纸剪成一块块小圆圈,在胸前竖着贴出几排,方才有了舞台感。
最有舞台感觉的是藏族女孩的围裙,要先把红、绿、金、蓝诸多颜色的油光纸剪出大小略有参差的长条子,色泽越多越亮越好,然后再把它们交错贴到一块舌头般的长布条上,这便是围裙了,系在腰间,可一直延伸到膝盖以下,整个人顿时夺目,它是点睛之物。
裙子最费衣料,一开始曾把医用纱布染成深褐或浅黑,或者把彩旗改造一下围起来。彩旗是丝绸的,品质当然不错,只是太贵,总是用不起,也太轻飘了,旋转时撑不起来,反而常常贴到腿上,缺乏美感。后来日本尿素袋子出现了,尼龙纤维的,垂悬感好,染一染,也很吃色,质地马上就高档了起来。
蒙古舞就不需要我们操心,老师买了廉价的棉布找师傅制作,领口、襟边、下摆加两道滚边,怎么看都与旗袍类似--无非下摆宽大一些,腰间再扎一条彩绸做装饰。
蒙古舞不好跳,需要用力前后甩肩膀,每个动作有棱有角,腰、背、肩都很费劲,这不是问题所在,而在于这套服装让我一下子就想起奶奶的旗袍。
算起来奶奶那时不过六十出头,眼下这个年纪的许多女人还有意无意残留女儿态,一不小心还敢穿着热裤、吊带裙冲上街头,拿那时的奶奶和她们比,似乎奶奶都可以当她们的奶奶。当然在年幼者的眼里,即使二三十岁的人也是苍老的,可拿出当年的照片来看,没错,皱纹如果仅是表象,那么浓厚的黯然倦怠神情总不至于骗人,它们都似残烛,比残烛更枯萎。奶奶一直这样,一直这么老,我想不起她还有另外的样子。但据说年轻时她是那一带数得着的美人,所以才有镇上的小康之家托人到村里说媒,二十四岁刚一守寡又有镇上另一殷实之家的子弟登门想强娶,她坚决不从,抱着出生才九个月零八天的我父亲逃回娘家,靠给人不分昼夜辛苦做女红养大儿子,并把儿子送进福州的学堂。而在我父亲之前,她生过一个女儿夭折了,再生一个儿子又夭折了,终于我父亲来了,还来不及高兴够,丈夫却突然死于伤寒。所谓的命运,她真的有资格举手质问苍天。以寡母之柔弱无依,独自养大顽皮的儿子,这个过程每个缝隙确实都被泪水和汗水浸透了。年轻的辛苦,到晚年再回忆,那股酸楚已经发酵出诸多滋味,她觉得仅自己一人独享太亏了,于是一遍遍地铺陈。只要我们哪天作怪,违她的意造她的反,她就会把右掌像一面旗子往前一举,如同古玩收藏家炫宝般凌空亮出食指、中指、拇指上骇人的粗大厚实的杏黄色茧子,自己显然抢先被感染了,体内某个开关被霍地拧开,往事一下子都醒过来,潮水般倾泻而出,语调或高或低地飘忽,表情或明或暗地起落,其用意是告诫我们,如果没有她当初的坚贞绝不低头,就断无我父亲的长大成人,当然也就没有我们来这个世界的可能,所以我们的不孝不敬就是可耻的卑鄙的忘恩负义。
关于我们来到世上的途径,从伦理学上讲她的逻辑似乎也没错,但从生物学上看,父亲就是长成歪瓜裂枣、地痞流氓、缺胳膊短腿,也照样恋爱娶妻生儿育女,而我们即使不是父亲带来的,也可能由别的谁弄来,总之该来的终究都会来。不过当时我们还是被奶奶饮水思源的强大暗示震慑住了,一想到自己差点不能来到这个世界,心里就打几个战。她抑扬顿挫纵情陈述时,我常常会联想起在敌人铡刀前昂首挺胸的刘胡兰。前几年某英模报告团光临,被单位组织前往,进场前同事腹诽的有,抱怨的也有,结果却统统被感动得泪水涟涟。那天我突然想起奶奶,她最合适的职业原来是当一名光荣的宣讲团成员啊。
“文革”开始后,服装遭了殃,男女老少都款式一致色彩统一,除了黑就是军绿色,奶奶却不在此列,她终生穿自制的旗袍,或深蓝或月白或湖蓝,春夏秋冬无异。倒没有收腰裹臀,而是直筒的,从上直直延伸到脚面上,也没高开衩,开衩没意义,她不出门,也不打算诱人。要说这样当然非常费布料,不是因为她胖,而是因为她高。我的表叔,也就是她的侄子有一次对我说:你奶奶至少一米七三!我想不起来了,小时候我的眼睛还没学会丈量人,看站着的她,觉得像平地竖起一根竹竿,她躺下来也没其他可像的,还是像一根倒在那里的竹竿。同一时代的女人中,我没有见过比她更高的,高而且瘦,终年躺着不动,却长不出多余的肉,到死腹部都是平平的。
她不出门不是她不想,而是她的脚不让。非常小啊,蜷成一块馒头大小的肉团子,五个脚趾叠成尖尖的笋状,上面永远浮着一层斑斑点点的白,我后来知道,那是死皮。在乡下那几年,晚上挤一张床睡,她和弟弟睡一头,我和姐姐睡一头,棉被明显偏短,她长腿一伸,就就是因为小脚,奶奶每天都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那时隔壁住的是姐姐当年的奶妈一家,奶妈是一个质朴善良的结实农妇,每天早上她为自家挑水时,就顺便多挑两担给我们,碰到需要买米买柴之类的重活,奶妈三个体壮如牛的儿子就踊跃代劳。三个儿子叫他们母亲不是“妈”,也不是“娘”,而是“依奶”,叫父亲则是“依哥”。很奇怪,这种叫法在福州并不普遍,不知起因究竟是什么,反正我们姐弟三人也从了他们,一起“依奶”、“依哥”地叫。没有他们,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很难挨过那段岁月。
躺在床上奶奶起初也做点事,比如缝补衣服,这是她拿手的,却也是她最厌恶的,火气在每一个针眼上跳动。眼睛不好了,我们帮她穿线,要是手脚慢一点,她立即就找到出气的借口。“狗母货!”这是她的口头禅,一边骂一边欠起身子试图揍过来。等到给自己备好几身衣服和几双鞋子后,她就再不肯碰一碰针线了。有一件阴丹士林旗袍做得最精致,襻扣从领口绕到腋下,再整齐排列到接近脚踝处,做好后她折叠起来,存到箱子里。与之藏在一起的,是双尖头小鞋子,红绸面,绣着黄绿相间的菊花。每过一阵她都要把它们拿出来看一看,晒一晒太阳。她说:“我死了之后穿的。”
我至今没穿过绣花鞋,也永远不打算穿任何绣花鞋。不再做女红,奶奶打发时间就剩下吃零食和吸水烟了。冰糖、冬瓜糖之类的是常备的,烟丝也一刻不能少。身体懒得动,嘴却不能不动。现在回想,会不会正是由于她总是不动弹,才致使两条腿愈发没有了力气?都这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终日横陈床上,她却每天不厌其烦地早起洗漱打扮,梳子沾上油一下一下把已经非常稀疏的头发拢到脑后,盘个小小的髻,然后整齐地穿好旗袍,每一颗襻扣都纹丝不乱系上,到了晚上再脱下,工工整整折叠好,换上短衣,日日循环往复,一丝不苟。偶尔下床行走,她必须小心扶住墙,一步一摇晃,风吹杨柳状,随时会倒下去似的。
做这些叙述时,远去的往事和亲人都隐约摇曳在时光深处,清香缕缕不姐出生后她已经强压怒火,结果我又是女孩,令她差点对林家传宗接代绝望。母亲说生我坐月子时,根本看不到奶奶露过面。幸亏几年后弟弟出生了,但二孙女是多余的这个纠结她一直没打算消除掉,其中的原因,有一大半来自我母亲。当一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女人半途杀出来,成为寡母捧在手心辛苦养大的那个儿子最心爱的女人,麻烦肯定就紧随而至了。寡母认为这是抢,我母亲却认为理所应当,两人都没打算妥协,针尖厉害,麦芒也不逊色。我被殃及是因为母亲的严重偏心,这当然不好,在多个子女中如何等量付出疼爱,是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前,既考验做父母的智商,也考验他们情商的头等大事。母亲聪明伶俐,一双巧手似乎无所不能,裁缝、打毛衣,甚至做家具、砌砖墙都技惊四邻,但在平衡子女这件事上,她得分不高。晚年她也不时反省,相当懊悔,却已时过境迁,一切难以更改。我猜想,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奶奶的发力上阵,非要咄咄逼人地替姐姐争个长短,或许情况不会那么糟。而当奶奶奈何不了心高气傲的儿媳妇之后,她也只能掉转枪口,对付一向不知乖巧为何物的二孙女。“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有意无意之间,每个人都可能忽然如此幼稚无理性。
记忆里总是听奶奶喊头痛,能令她平静下来的是万金油。太阳穴、额头反反复复涂抹,以至于那股辛辣的药味成为她的标记性气息,在屋里每一件家具和她的衣服鞋袜间挥之不去。一九七二年秋天她在医院去世,正在县城出差的父亲赶回来时,一边踉踉跄跄地俯着身子奔跑,一边尖厉失态地呼喊号叫,脸上湿漉漉地布满眼泪鼻涕。我当时正站在门旁,看着父亲这么古怪地迎面而来,吓得猛地缩紧身子。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他一直爱说爱笑,一旦沉下脸又是威风八面令人生畏。孤儿失去寡母,他的悲切应该甚于一般的丧母之痛。
丧礼开始时,不知是谁捧着一个老式相机来给我们合影。相机那时还是稀罕物,所以就有点非同寻常。就在狭小低矮的太平间里,已经略有僵硬的奶奶被抱到椅子上坐定,而我们全家穿白衣罩白布围着她站立。我在左边,隔得有已经近了,其实并没有。恼怒的父亲从后面伸过手,狠狠一揪,我趔趄着,一下撞到奶奶身上。
我很难描述当时的恐惧之感,恐惧到无以复加的绝望。那个拍照者后来又殷勤洗来一大沓照片,父亲一开始把它们放在桌上,慢慢改放抽屉里、箱子中。无论它们在什么位置,都成为我避之唯恐不及之处,我远远避开桌子,我绝不拉开抽屉,我打死也不会碰箱子一下。
死的时候,奶奶果然穿的是她自己早早做好的长及脚面的阴丹士林旗袍和那双精巧的红缎面绣花鞋。谢春妹,这个名字是后来为她扫墓时,才从墓碑上看到,非常普通,乡土味浓郁,这与她沉寂落寞的一生是协调的。
各种舞蹈里,我跳得最不好的就是蒙古舞,一穿上那身服装,万金油、烟草以及老年人特有的酸腐味就混合着扑面而来。除了阿拉善,至今我没去过内蒙古的其他地方,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贡格尔草原都仍在远处。总有一天我会抵达那里,至少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要双手叉腰,用力地前后甩动肩膀,努力把这个动作做得优美而有劲道。
奶奶说,女孩子抛头露面干什么?我任何一次演出她都没看过。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