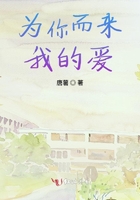一
村子里静静的。
下地的似乎又照常下地了,偶尔有拿簸箕的女人在村里走过,也是匆匆忙忙,只有鸡们、猪们在悠闲地撒欢。间或,从田野上传来灰驴的一两声叫,淡远而悠长,仿佛扯着日影儿慢慢移……
然而,这平静又有些让人不安。要细细听,在庄稼人的院落里,这儿、那儿会有窃窃私语;而在那一堵土墙的后边,高大瓦屋的窗棂处,或是双扇老式大门的缝缝里,也正有一双双眼睛在窥探。这私语和目光,又分明是冲着村中那三间新式平房去的。
这三间新式平房是山根年初才盖的,在村里虽数不上头一份,倒也称得上气派:大窗明玻璃,比一般房子整整高了三尺。只是院墙还没打起,灶屋是旧的,院里还不曾看到女人呆过的迹像。明白人一下子就会看出,主人的好时光刚刚开始。
可此刻,这三间新式平房的主人——山根,却呆呆地蹲在院子里,那神情象是一只被打蔫了的狼。五尺高的汉子哟,就那么缩成鳖样的一团,两只大手用力地揪着头发,脸色乌青,眼神木滞,透着吓人的死光。谁看到这样的目光,谁心里就会不由得打寒颤:他才二十六岁呀!
邻家那只芦花大公鸡已经是第三次在他面前挑衅了。它探探头,往前挪一步,再探探头,又挪一步,眼看已接近邻家端来的那碗饭了,他还是一动不动。鸡犹豫了,要不要再跨一步呢?这人平日是很历害的,他踢过它。那天,当它勇敢地登上了灶屋的锅沿,瞧他那傲气劲:“等着吧,会有人收拾你!”——他指的是女人。当然,治家的女人比他还狠,可他还没有女人。那么……鸡展展翅,终于又勇敢地跨前一步,虽有几分惊乍,嘴,已经伸到碗里去了……
山根完了。
当村里人都开始做发家梦的时候,山根已在脑海里给自己美美地画了一幅“蓝图”。当然那不是吃穿不愁、囤满囤流的“小康”,而是在不久的将来,当当那“山根公司”的经理。山根是硬性人,他不咋咋乎乎地吹,只暗暗在心里攒劲。这个当过三年汽车兵、有着高中文化程度的乡下娃子的计划,应该说是很周密的。当他经过复员后的三年苦干,终于摆脱了一切拖累(体面地埋葬了在床上瘫了七年的老娘,又翻盖了三间平房),待无牵无挂之后,才开始展劲的,他看准了跑运输的利,于是便倾家、举债买了台七吨的大“江淮”车,并且立即与五家砖瓦窑订了送煤的合同。他算过了,只要跑上一年,债就能全部还上。那末,再跑一年呢?
这娃子太狠了,挣钱不要命。为了还债,车买回来的第三天,在村里人还没有求他捎脚的时候,他便在家门口的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凡本村人乘车,不论远近亲疏,十五里地一角;外村人乘车,十五里地两角。这一下就把乡亲们得罪完了。本乡本土的,一个庄里住着,捎个脚还要拿钱?咋不截路去呢!嘴厉的女人竟然在背后咒他:“好得车开沟里,栽死他!”这还不算,村里有些好事的女人要张罗着给他说媒。让他开车送,他竟说:“这油钱谁掏?”女人们的嘴也是够一份的:“那你打光棍吧,山根。”他傲哟:“女人,总有一天叫她们找上门来!”还有一回,车开到村口的时候,在东头场里干活的人都嚷着叫他停停,好坐上“抖抖”。谁知,他高高地坐在“司机楼楼”里,不喊倒还慢慢开,一听吆喝,便加大油门,把车开得飞风一般,扬了人们一脸灰。
他一心奔“钱”,一心奔“钱”,三顿饭常常只吃一顿,渴了喝口凉水,饥了啃块干馍。上方山拉煤,人家一天跑一趟,他一天跑三趟,昼夜不息。那眼熬得像血葫芦一般!人们见了,都以为他挣钱挣疯了。
终于,在七天之后的夜里,车眼看要进村了他却头一晕,在下岗拐弯的时候跌进了南北潭——七丈深的南北潭。幸亏他没关车窗,人被甩出来了……
一声喧天的巨浪埋葬了他那宏伟的“蓝图”。一个乡下娃子人生的第一次冒险彻底失败了。真惨哪!
车完了,可那借了近两万元的债将怎么还呢?两万元,一个吓人的数目,又有谁能够解救他呢?
山根就那么在院里蹲着,不管谁来劝,不管谁说什么,他都一声不吭。阳光下,那咬破的厚嘴唇一滴一滴地往下淌血,使他显得分外狰狞。
不会再有人借给他钱了。他面前似乎只有三条路:上吊;逃走;扛长工。要说扛长工,如果按村里窑上“吉老板”给的工钱算(这工钱不算低,可他连这一条路也堵死了),他需要二十年才能把帐还清。二十年,一生最好的时光,都要用在还债上。
后院那信主的“老姑奶奶”又在祈祷了。一生都没嫁出去的“老姑奶奶”打从信了主,不但逢五做“礼拜”,还天天哑着喉咙唱,声音低沉缓重,像纺线的花絮一样时断时续,唱得人心灰:“嗨嗨米呀……嗨嗨兔……”山根,山根,有的时候,人是不是也得信信这命?
二
兆成老汉有一点点信。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他就觉得不顺当。正耙地哩,套绳断了一股,刚接好套,那借来的灰驴却又脱缰跑了,累得他呼呼哧哧一直撵到村西窑上才“吁”住。待他抓住缰,狠狠地抽了灰驴一鞭,忽听见有人叫他“兆成,兆成……”
一听是吉昌林——“吉成板”的声音,他忙抬起头问:“啥?啥事?”
当上窑老板的吉昌林远远站在窑上,正威风凛凛地招呼他的工人背砖出窑,手一挥一挥的,嗓门也格外响:“山根那娃子,嗨!”
一听这音儿,兆成老汉更慌。他拴了灰驴,急急地凑过去问:“山根出啥事了?”
“去吧,去吧。爷儿们,去劝劝他,我这会儿不得空。”吉昌林皱着眉头说。
“咋啦?到底咋啦?”兆成老汉像是一下子被甩到云彩眼儿里去了,愣愣地瞪着眼问。
“唉,车翻到南北潭里了……”吉昌林沉重地叹了口气。那神情,就像他的轮窑塌了一样。
这一句犹如五雷轰顶!兆成老汉顿时懵了头。他二话不说,扭头就走。走了半截,又忽地折回来,急头怪脑地朝地上跺了两脚,又忽地折回去走。心里一个劲叫:天爷!天爷!
三个月前,老实厚道的兆成老汉把一生积蓄的三千块钱借给了山根。这钱原是盖房用的。山根借钱的时候曾答应过他,待年底赚过本来,给兆成老汉拉三车煤,不要运费。他的心劲不高,盖三间坐地小瓦屋,用煤换砖当然便宜些。过日子,不都是提着心劲往上走吗!
兆成老汉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走。来到山根房前的时候,他抬头看看那半截子土墙,咂咂嘴,怔怔神儿,又往前走,勾着头一步步走回家去。进屋蹲下来,一连吸了三袋烟。
吸过烟之后,他想:这娃子心性太高,会不会一下子想到绝路上去?这念头吓了他一跳!于是,又慌慌地从家里走出来,朝山根家奔去。远远,当他又看见山根家那半截土院墙的时候,站住了,又是蹲下来吸了三袋烟,才缓缓地站起,弓着老腰往山根家走,走得很慢。
在这个世界上,做人不是很难吗?他活过六十四个年头了,他知道做人难。可他那三千块挣哩老不容易呀!那里一滴血一滴汗地换,一口一口地省……可还得做人,还得做人,既然是个人……
进了院子,山根翻开眼看看他,没有吭声。他也没有吭声。就又蹲下来,默默地吸旱烟,吸了两口,又把手伸进怀里,摸摸索索地掏,久久,摸出平日见乡干部才掏的纸烟来,哆嗦着手递给山根。山根接过来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这会儿,兆成老汉开腔了:“娃子,你可不能往绝路上想啊!你放心,我不问你要钱。这种时候,我不能问你要钱。你……想想办法吧。”
山根的嘴角痉挛地抽搐了一下,笑了。那惨然冰冷的笑使兆成老汉一阵脸红,又一阵心悸。他低头看看那被鸡们啄得“麻坑”点点的饭碗,又望望远处那一缕一缕的还未散尽的炊烟,嗫嚅了半晌才说:“找找吉老板吧。娃,低低头,咱低低头。如今只有他了……”
山根还是不说话。那惨冷的笑依旧挂在脸上,像止不住似地机械地抽动着面部神经,显得恶狠狠的。
兆成老汉不忍再看山根那张“灰”了的脸,忙说:“娃,我去,我去。”说着,他长长地叹口气,脚步迟疑疑地迈着,待出了院了,才腾腾地加快了脚步。又走,又折,心乱得像一窝麻。最后把孙子毛头叫了过来,低声吩咐说:“毛头,你看住山根,只要他进屋一关门,就赶紧叫我。听见了?”
五岁的毛头顺从地点点头,规规矩矩地站在了那堵矮墙的后边。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一会儿探头看看,一会儿又看看,待瞅过几回,便怯怯地溜到墙边喊:“山叔,我去玩哩,你可别关门!”
“噗嗒”,一颗泪珠从山根眼里滚了出来。
三
乡农贷员兆保立是吉兆村第一个过“城市生活”的人。
他原是很瘦很瘦,尖尖的一个脸儿,眉眼上也看不出福相来。那时候,他有什么办法呢?家里,一个病怏怏的懒女人拖着三个娃,日子总是过得很艰难,又总是欠着队里什么,每到年底,也总要请客才能免去那拖欠了很久的公债。一个月四十二元的工资实在是不抵用的,好在“大锅”里搅混,厚道的庄稼人也就不说什么。
可是,终于有一日,人们见他从乡里回来的时候哼着梆子戏,那破烂的自行车竟也换成了新“飞鸽”,后来,常有人请他喝酒,两只眼总是醉眯眯的。再后,就跟城里人一般模样了,每天早上照例是一磅鲜牛奶外加两个荷包蛋。那奶是外村人送的,并不像城里人那样排在街口傻等。饭后呢,也学城里人去“散步”,去呼吸那“新鲜空气”。这“锻炼”也是太阳老高老高才开始,背着手围村走一圈间或也认真地甩甩胳膊,呼呼,吸吸,兜里还一准装着“小戏匣子”随他唱。就这么天天锻炼,猴瘦的兆保立竟然一日日胖起来了,不但脸色红润,尖下巴也成了双的,打一个肉乎乎的褶儿。
每当他“散步”到窑场的时候,要是吉昌林在,他定要喊上一句“早啊,支书大老板!”
吉昌林也准定要回他一句:“财神,到底是吃官饭的哇!”
于是,你笑,我笑,拿烟来吸。他承认他没有吉昌林本事大,可他很快就要挤进这个行列了。
然而,这天早上,吉昌林那阔脸大嘴巴上并没有带笑,而是很沉重地说:“财神,我先给你说,一个庄里住着,和尚不亲帽儿亲。你可不能逼着要债,你得帮他。山根出事了……”
兆保立听到山根倒楣的消息,微微怔了一下,既然笑着,也就笑下去,并不曾变色。只伸手掏烟来吸,恰恰又没带烟,遗憾地把手放下,那手抖抖地。
吉昌林递过烟来,正神正色地说:“保立,你说啥也得缓缓,人到难处了,咱不能再落井下石。”
兆保立看看吉昌林:“咱能干那事儿?可这,这这……是公款哪!”
“嗨!”吉昌林摇摇头,“是呀,公款。”
“唉,这娃……”兆保立咂咂嘴,又咂咂嘴。
分手之后,兆保立又继续“散步”了。他硬撑着往前走,竭力做出平静的样了,身上却已经出汗了。
太阳斜上了东岗,虽不十分暴烈,倒也透出几分焦躁。远处的杨树上有知了在叫,长久不歇地聒噪着,很刺耳……
也是年初,他挪用了信用社的无息贷款一万元,借给了买车的山根。当然,这钱不是白借的,一万元贷款,他只给了山根九千做为月息一分开,他先扣了一年的利钱。山根那会儿急用钱,也就认了,这事只有天知,地知。
说来,他原也不曾想到,一个过去被人看不起的农贷员竟也会有权,而且这权也是可以当钱使的。自从允许个体户贷款,他的运气也就跟着来了。是呀,政策好了,他也沾了这好政策的“光”。急用钱的户很多,“烧香磕头”的也就来了。“敬”的人多,自然也就成了“神”。神是“香火”熏出来的。连他自己也不晓得究竟是哪一日开始被人敬重的。他虽是一个小小的、月工资仅有四十二元的农贷员,可日子过得并不比那些有名气的万元户差。他总是很忙,常常在这家喝了酒,又赶到那家去。人们也敬重这“忙”,身价也就一日日抬起来了。“财神”哟,他是“财神”,人们都这样叫。他就越发地胆大,越发地敢干。酒醒一醒的时候,他也想想久远的将来,做事自然就谨慎些。不过,他还从未出过漏子。有那么多人要干事,要发家,要展本事,也就捎带着把他“养”起来了。
可是,山根出事了,狗急还跳墙呢,人要是逼急了,那可啥事都干得出来。万一山根还不起债,闹到法院去,这事儿不就露馅了吗?要是,要是在这娃子身上栽了,他这一辈子可就完了!不能完哪,他这好“日月”虽然来得容易,可也不能白白失去。他胖了,肚皮上有油了,有了敬了。他那女人,他那娃子,也都打扮得鲜鲜亮亮地人前走人前站了。
天很蓝,白云在悠悠地飘,田野里展现着无边的绿,村子上空的炊烟还未散尽,袅袅地在庄稼院的四周荡着。一时间,叫人觉得那有吃、有穿、有钱花、有人敬的日月是那样地可恋。
当兆保立来到山根家那堵土墙边的时候,脸上的汗已经擦干,制服上的扣子已经系好,主意也想出来了。
一进院,他就哭丧着脸说:“兄弟,恁哥不是埋怨你,这几万块钱的物件能儿戏吗?借款的时候,我就对你说,这是公款,恁哥一个农贷员,头皮老薄呀!”
山根翻开眼皮看看他,又闭上了。
兆保立蹲下来,往前凑凑,声音低了些:“唉,既然到了这一步,咱好点子、孬点子都得想。反正这一万是公款,你得想法叫我捂住。”
山根没有睁眼,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疙瘩,蹙得叫人心里发紧。
“山根,别愁。恁哥能难为你?这事是不小,可事大事小……”兆保立又往前凑了凑,分外关切地望着山根,话到半截,却咽了。喉咙里还长着一个“跑”,他多想喊出来呀!可他不说,叫人想。他不怕跑,人只要一跑,无论是死是活,就没有他的事了。这边有“保人”顶着呢,叫那不知内情的保人去顶黑锅吧!
山根微微地动了动眼皮,似乎听出了点什么。
兆保立还是不放心,继续“点化”说:“就这吧,兄弟,你是明白人,用不着恁哥多说。咱三天为期,三天以里你想个了结的办法。恁哥不难为你。这年头……”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在手里捏了捏,放在了山根的手里,拍拍他,又拍拍他。
这两“拍”似有千斤的份量,山根的身子哆嗦了一下,两张崭新的十元票滑落在地上。兆保立赶忙拾起来,又硬塞在山根手里,用十二万分恳切的口气说:“兄弟,老少。我这几天手紧,实在不够意思。你,再想想……”
凭心,他实在不愿看山根那张乌青乌青的脸。这娃子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头,他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呢。这也叫一辈子呀!唉,他虽可怜山根,可他更可怜自己。好不容易“等”来的日月,难道让人家去享?难道叫他去装傻蹲监狱吗?那可万万不能!他得精心保护好这能当钱使的“权”。他费了多少心机呀!
跑吧。跑吧。远走高飞吧!
四
现在的人,谁是傻子呢?
山根的远房嫂子李喜花听到这倒楣的消息之后,赶忙打发儿子把男人从地里叫回来,关上门召开了家庭“紧急会议”。
这是个精明的女人。人长得不算秀气,眼皮是双的,走路带一阵溜溜的风,那薄薄的嘴唇常常抿着,笑也会笑,狠也会狠。在嫁人之前,她曾为两个娘家兄弟赢得了两份很厚的见面礼和一处小小的宅院。她是把男家掏空之后才嫁过来的。出“门”前,她又为两个不中用的娘家兄弟尽了最后一份力,撇下了所有的嫁妆,就那么光光地一个人来了。可她决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花瓶”,在嫁到吉兆村不久的时光里,她很快地以做事的干练和持家的能为在家中占了统治地位。男人的懦弱,更衬出了她的能干,就是盘“窝”的蜘蛛也不比她更强些。为了这不中用的男人,为了刚刚上学的孩子,为了这个家,她使出了全部的智慧和心力。这是个为那些不中用的男人打天下的女人哟!
现在,在这个小小的“家庭会议”上,她的绞尽脑汁的思考更是叫人赞叹和吃惊。她想:做为本家一姓的亲戚,首先,这时候不能要帐,一要帐人家会说你太短。其次,得赶紧摸清山根手里还有多少钱,有没有还帐的能力。要是没钱还帐,房子千万不能叫别家弄了去。那三间平房正好在她家屋后,地势好,可以搞个“二进院”。为实现这“二进院”的计划,不能强逼,也不能傻等,得想办法叫山根自己吐口,把房子暂时先抵上。只要他说过话,别家就不能争。她表哥在县公安局干事,不怕动武。
当她细细地对男人说出这一切之后,马上吩咐男人在家候着,一有风吹草动就骑车往县公安局跑。接着又打发七岁的儿子小虎去学校请假一天,回来趴房后窗户那儿监视山根的动静,千万不能叫他跑了。人一跑,怕就争不过公家了。
男人嗫嚅着想说句什么,喜花便狠狠地“剜”了他一眼:“想必你这三千块钱来哩老容易!”
男人不吭了。一个怕老婆的汉子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只好又闷闷蹲下。
待一切吩咐了,李喜花麻利地从锅里盛了碗热汤,又卷了两张夹菜的烙馍,一阵风儿似地朝山根家走去。
一拐进院,她就高声说:“山根,吃饭。就是天塌下来,咱也得吃饭。”
山根抬起头,看看端着饭碗的远房嫂子,嘴角抽动了几下,似乎想喊声“嫂”,却没有喊出来。
喜花把饭放到山根面前,轻声叹口气,说:“听说信儿,恁哥就打发小虎去地里喊我回来做饭。他怕你一时想不开,伤了身子……”说着,眼里湿湿的掉了两滴泪。
“嫂,我……”山根呜咽了,在亲人面前,一股热流直冲喉管。他想哭,他想喊,他想撞墙。他恨自己不争气哟,老不争气。
喜花递过一双筷子,软言细语地劝道:“山根,咱是亲一窝呀,能不管你吗?有恁嫂吃哩,就有你吃哩。咱不就这几家近亲吗?刚才恁哥说见‘财神’来了,你别理他。咱欠哩是公款,拖一天是一天,他还能把谁吃了?”说着说着,她忽然扬起脆亮的嗓音儿,站院里高声骂起来,“兆成老鳖孙也不是好东西,眼皮恁浅!咋?俺兄弟欠不起那几个钱?真短见哪,一听说出事可跑来了。咋不栽断他那腿哩?咋不磕碎他那牙哩?”又回头对山根说,“兄弟,吃!你吃饭。”
山根看看,看看,又把筷子放下了。“嫂,我,我真咽不下去……”
“山根,你哪怕吃一口哩,也是恁嫂一份心意。听话,别往心里搁。”喜花脸一嗔,把馍硬塞在山根手里。
山根在本家嫂子那关注的目光下,勉强把馍举到嘴边,却又放下了。那纵是猴头燕窝他也吃不下去的。
“山根,东山日头不是还有一大垛吗,咱慢慢来。恁嫂这一头总不逼你吧?要是手里有俩钱,咱就先拣那要哩急的户抵上。要是真没钱,咱挺着。”喜花慢慢地开导他,话语里透着女人特有的柔情和自家亲人的关切。
当着这贴己的亲人,山根眼里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硬汉子终于说话了:“嫂,我这一辈子怕是完了……”
“唉,山根,”喜花跟着叹了一口气,“到这一步了,咱就不说恁远,先顾眼前吧。兆成那老鳖孙要是再来,你就对他说,别打房子哩主意,那房子是借俺嫂子的钱盖哩,看他还咋说。”
山根慢慢抬起头,木然地望着远房嫂子那挺受看的脸,久久,久久……
李喜花讪讪地避开了他的目光,伸手拍拍山根身上溅的泥点,低着头说:“兄弟,要是馍咽不下去,你就喝口汤。你出事了,恁嫂心里也不好受哇!”说着,不知怎地,竟“呜呜”地哭起来。
五
山根,你是汉子吗?堂堂的五尺汉,就这么蹲着,像鳖一样,等人家找上门来?
你说什么,你还有什么可说?
你的计划不是很周密吗,你不是要一步一步来吗,你不是说你要干个样儿让他们瞧瞧吗,蛋哪!三天前你还坐在“司机楼”里唱《军港的夜》呢。
那时你多兴啊!你觉得你是吉兆村的第一个强人,没有人能胜过你,连赫赫有名的吉昌林,你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你只想着你那“未来的公司”——“山根公司”,一个庞大的车队,一个叫姑娘们羡慕的“经理”。你甚至还私下看中了一个姑娘,在禹县东关卖茶的姑娘。你每次走到那儿都要鸣一鸣喇叭,于是,她就会抬起头来,笑一笑。那笑多甜哪!可你还没有给她说过一句话,你只是暗暗地在心里记住她。她是你的人了,你这样想,总有一天你会带着整个车队来接她。你有的是力气,有的是汗水,还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到那时候,你将是吉兆村第一个娶城里姑娘的汉子。
你红眼了。你想把这一切尽快挣到手。你还想叫吉兆村的老辈人瞧瞧你的本事。你料定你这一百多斤是不会垮的,你拼上了,一连七天七夜……恨不能一下子把债还上。
是哩,你不怕得罪人,要干事就不能怕得罪人。可你太狠了,当村里爷儿们求你办事的时候,你没说过一句好话,你也没让他们占过你一分钱的便宜,连顺路进城的都被你扣下一角路钱来。至于那些想用汽车送粪的亲戚,你张嘴就要一百元,把他们吓得咧嘴。可你也想过,创业的时候,要狠一点,亲爹也不能客气。等将来干出样子,你要大大方方地给村里爷儿们办件好事。这会儿就让人骂吧。可是,你料定会有这一天吗?
现在,你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就是把你的骨头榨出油来也还不了债。败了,你得承认你败了,没有人扶你,你再也站不起来了。到这会儿你才明白,一个人是干不了大事的。在吉兆村,你一个人注定不行。
人得罪了那么多,谁还会帮你呢?
山根,别再指望了,谁也别指望。既然你是汉子,那就站起来吧,站起来。再看看这天,多蓝的天,这云,多白的云,这院落,还没住进女人的院落,这好日子不是你的了。你个笨蛋,你个****的!咽下一口血,你认了吧。
可你这口热血难咽。你是老不服,老不服哇!你能再有一次机会,仅一次……
六
快到晌午的时候,吉兆村最有权威也最有力量的人物走出来了。他,就是昔日被人称做“铁旗杆”、而今又被人叫做“吉老板”的吉昌林。当他那铁塔一般的身量、那响亮的咳喇声一出现在村街上,善良而又无能为力的村民们不禁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山根有救了。
吉昌林这个名字,在别处也许并不那么显眼,可在小小的吉兆村,却是万万不可小觑的。十八年了,这位“铁旗杆”整整在吉兆村竖了十八年,至今还稳稳地站着,没有谁能够扳倒他。当干部吃香的那些年,人家是大队支书;这会儿干部不那么吃香了,人家又用最低的价包了大队的“轮窑”。人物呀!人家真是人物。过去的时候,那窑总也赔钱,总也赔钱,像是填不满的老鼠窟窿。可一到人家手里,没添一件像样的机器,也没怎么管理,只凭那一声响亮的吆喝,便开始大把大把地捞“票”了。他有买化肥的指标,有分好地的权力,有叫人多生一个娃不罚款的办法,还有划分宅基地的权……话得说回来,一个立了十八年都没倒下的角色,吉昌林的豪爽大度也是出名的。只要求到他的门下,只要有人喊声:“昌叔,我没办法了。”他哈哈一笑,事儿就办了。不管你这人有用还是没用,他都会帮忙。即使是傻子来求他,他也不慢待,常常叫人感激得下泪。吉兆村有多少人欠他的情啊!乡里,县上,甚至地区,都有替他办事的朋友,连这些朋友也都一个个欠着他什么。可也得记住,你不能捣他的蛋,要是想和他作对,那么,除非你离开这块土地。不然,总会有些事情的。总有。现在,他虽然屈尊当了副支书,可他抓住了这能赚钱的轮窑,不动手就成了十万元户。“铁旗杆”依旧是铁旗杆。只要他想管,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天地狭小的吉兆村,出了这么一位“福星”,不也是人们的造化吗?
吉昌林还像往常那样披着涤卡褂子,胸脯挺着,两手背着,摆动的衣袖忽悠忽悠地扇着,踏在地上的脚步是坚定而有力的。那阔方的脸庞,那宽大的额头,那富态的鼻子,还有那透着长者的威严的目光,无不给人以沉着老练的感觉。他的威风不是摆出来的,而是自自然然带出来的。
从地里回来的庄稼人,远远地就吆着牲口站下,和他打招呼,“昌叔,昌叔”地喊;走到门前的,更是谦恭地邀他上家吃饭,虽知道他不会去,也是要让一让的。他一路走来,响亮地应着,打一个“嗯”声。他走,日影儿也跟着他走,仿佛要把一块很大的荫凉带到山根家去。善良的庄稼院的女人也都在关注着这一幕,借了喊娃儿的工夫探头来看。至于跟在他身后的那个年轻娃子,任谁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跟在吉昌林身后的年轻人叫吉学文,他三个月前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人长得很单,脸稍稍白净些,浓眉下一双细眼,点漆一般亮。只脸庞娃气,常常又抹一点雪花膏让人闻见,总也摆不起成人的架势。平日里,他老穿那件印有“人民炮兵”的白背心,下边又是宽荡荡的绿军裤,走起来两只胳膊还一甩一甩迈正步,似叫人想起他在队伍上的英武,也曾叫村里那些早已不再对复员兵感兴趣的姑娘们笑话。可他不觉,仍还是这样穿,这样走。有一阵子,他还大白天端着衣服到南北潭去洗,借机和那些姑娘们说几句话,谈谈部队上的事情。渐渐,就传出他想自己找对象的风声,便很有一些人看不起。可吉昌林偏偏挑上了他,他当支书了,现在是吉兆村的第一号人物。不过,他仅仅是才当上一个月的支书,村里人并不看重。谁都知道,他是配班子的时候,凭年轻才“化”进去的。论权论势,吉兆村还是得吉昌林说了算。即使这娃子有一日成了气候,他也得不到什么了。凡是能分的,在吉昌林当支书的时候就全部分下去了。连水渠上的砖也是一截一截地扒着分的,集体是个空壳子,他当支书只有落骂的份。至于定盘子的事情,谅他那嫩肩膀也挑不起。这不,像尾巴一样跟在吉昌林后边,来是来了,又能济什么事呢?
将近山根家院墙的时候,吉昌林慢下来,掏火点烟来吸,让年轻的新支书走到前边去。这谦让分明是有意的,让人看出前任支书的宽怀和大度。吉学文似也觉出,慌忙让步,被他一掌拍进去了。
院里弥漫着热辣辣的愁。山根蹲着。兆成老汉竟又来蹲着,多皱的印堂上亮亮地红了一块,亮中浸着愧色。面前的地上,烟灰磕了一坨一坨。老汉一望见那晃进来的高大身影儿,忙弓身欠起,嘴角处斜斜地扯起一线喜:“山根,恁昌林叔来了……”
吉昌林接过话头,用气恼和同情的口气说:“山根,你这娃子!嗨……给支书说说,支书来了。”
山根却像聋了似的,厚嘴唇紧紧地闭着,眼死死地望着脚下那一小方地,不肯抬头。
吉昌林耸耸那披着的涤卡褂,来回挪动着,院里随即响起震人的“夯子步”,叫人觉出那扎实的力量。尔后,他站下来,定定地望着山根,以长辈的口气说:“山根,你给支书说说嘛!这不丢人,你娃子也别硬撑了。”
兆成老汉愣了,这是怎么了?吉昌林没有当众拍胸脯,也没有哈哈一笑,不当回事,而是把那嫩娃子往前边推。若在平常,他决不会这样。他会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又会脸一沉,高声地熊你为啥不来找他。可今天,他却反常了。
新支书吉学文是刚从乡政府开完会赶来的。他挠挠头,一时不知说啥才好,很窘。他想说,山根,你得振作起来。可怎样才能使山根“振作”呢?他想说,山根,大家会帮你的。可怎么叫大家帮他呢?集体没有一分钱,连干部的补贴都是群众摊的,而且已经有人不想摊了。村里没钱,他这个才当了一个月的支书也没有号召力,谁听他的呢?可他知道这位本家叔是要把他推到前面去,要试试他的本领,他从话里感觉到了。他也知道他得管,必须管。村里的事已经很久没人管了,这是他上任后要处理的头一件事,这事要是不管,那么……
“山根……”吉学文怔怔地想了好半天,才迟迟地说出这半句话来。
兆成老汉憋不住了,他不看那嫩娃子,只眼巴巴地瞅吉昌林:“昌林,山根这事咱不能不管呐!”
“管!学文,这事咱得管!”吉昌林很干脆地说,可话头却仍是冲着新支书的。这又使人明确地看出,他是为树新支书的威信才来的。他不是不管,有新支书在呢。他是等学文拿主意,别看年轻,他尊重他。
邻家院子传来了扇风箱的声音,“啪嗒,啪嗒”,慢慢有炊烟飘过来,很浓。日影儿斜到了房沿下,辣辣地照着。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吉学文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汗。他感到了无形的压力,感到了一个乡村支部书记的份量。脑海里像有一个陀螺在旋,一个又一个念头涌出来,又一个个地否定掉。最后,他竟紧张得口吃起来:“山根,你,你你你,没有一点办法了吗?你要是有啥点子,就说出来好了,咱……”
蓦地,吉昌林的脸沉下来了:“这是啥话?嗯——”这一声“嗯”拉得很长,鼻音很重,分明带着不得不批评的口气。怎么能这样说呢?年轻娃。
学文的脸“腾”地红了,他尴尬地站着,那脸上的红慢慢浸到脖颈处,显得很蠢。他也知道这是废话,没一点点用处的废话。在这种时候,又当着出事人的面,本该说一些有用的有力量的话。可他,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事情,只好艰难地、求救似地望着吉昌林和兆成老汉,说:“那……咱开会商量商量吧?”
“也中。”吉昌林不满地叹口气说。
吉学文抹了一把汗,走出去了。兆成老汉连连摇头,也终于跟着走出去。只有吉昌林还在院里站着。他响亮地咳嗽了几声,表情严肃地看着山根,似乎希望山根能抬起头来,能说一句什么,可山根却一直没有抬头。于是,他来来回回在院里踱步,又时常停下来望山根,久久之后,才十分遗憾地摇摇头走出去了。当他临走出院子的时候,再次地回头看了山根一眼,默默地……
山根还是虎死不倒架呀!
七
一个乡村的支部会,又是怎样开的呢?
在村头的大槐树下,兆成老汉闷闷地蹲着吸烟。吉昌林像半截塔似地坐在那儿,两眼眯眯地,一只大巴掌轻轻在亮脑门上拍,一下一下,似要拍出什么来。只有吉学文正襟危坐,很认真地捧着从部队上带回的绿皮日记本,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末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
没等他说下去,吉昌林的眼睁开了,巴掌依旧在脑门上拍着,却用请示的口气说:“学文,喊喊五魁吧,嗯?喊喊,都是支部的人。”
“中,叔,中。”吉学文应着赶忙站起,小跑着进村喊人去了。
过了一袋烟的工夫,小伙子回来了,往下一蹲说:“魁叔早起进城帮工了,得仨月。”
吉昌林的眼睁睁,闭闭,像又记起什么似地问:“噢,老八哩,你八叔?”
“隔墙问了五爷,也不在。”吉学文应道。
“喊喊,再喊喊,你说哩?学文,在家不在家,咱喊了,礼多人不怪。”吉昌林又用商量的口气说。
谁去喊呢?自然又是他。吉学文挠挠头,再次站起,颠儿颠儿地跑去了。
炎炎的正午,天很热。村里的庄稼人瞅见这年轻娃子一趟一趟地跑,一趟一趟地喊,更有些看不起他。当支书了,当支书又咋样呢?狗狗子,就这么一趟趟颠儿吗?
来回跑了这么几趟,吉学文出汗了,头上火星子乱蹦,可他还是规规矩矩地汇报说:“五魁、老八、三黑都不在家,说是早起给你说了。”
“噢,”吉昌林用力地拍了两下脑门,“你看我这记性!老了,真老了。”
“昌叔……”
“中,我先说几句。”吉昌林挺挺身子,脸,也跟着严肃起来,“我干哩年数长,事经的也多些,都是些老套套,敲个边边鼓。学文,今儿个这事,你娃子可老嫩……”
“叔,叔,我年轻哩。你多说,多说。”吉学文红着脸子,头忙忙点。
吉昌林脸色更沉了:“这事儿,咱不管能办不能办,都不能在群众跟前玩花花舌。能办,咱办;不能办,咱说些宽心话。咱是‘支部’,不能跟着慌。咱要慌,叫群众咋办?嗯?”
“叔,你说,你说。”吉学文手里的笔一点一点地在本上跳着,舞得很麻利。
往下,吉昌林响亮地咳嗽了一阵。“嗯,就先说这几句吧。”
吉学文颇有些失望地合上了日记本,身子还是像小学生那样地坐着,只有从眼睛里才能看出那一股一股往上窜的心火。
兆成老汉鳖不住了,在树上“梆梆”地敲着烟锅,急火火地说:“昌林,吉兆村千把口人,能眼看叫山根往绝路上走?”
“老兆,你也跑前跑后,这能是不管吗?嗯?”吉昌林说,“都是在党的人,会不管?”
兆成老汉眼角里漫出了一丝愧意,低下头再也不吭了。可不,他头一个跑去看,头一个。他明白吉昌林话里有话,这话烧人的心,他是为他那三千块钱去的,他昏了……
吉昌林却又大度地摆摆手:“老兆,掏心窝子说,我比恁还急。政策呀!咱得讲政策。过去是肉烂在锅里,这会儿你能还叫群众平摊吗?那报上登多少,不叫吃大户。再说,学文现今是支书了,咱得听听学文哩。”
兆成老汉嗫嚅着又趷蹴那儿了,接下去又是闷闷地吸烟。
吉学文扬起脸来,又一次很尊重地望着吉昌林,说:“叔,你是老支书了,你看咋办?”
“学文,把这一摊交给你了,放心大胆干!恁叔不能多揽权。”吉昌林鼓励说。
吉学文手里捧着日记本,依旧很恭敬地望着吉昌林,望着……
吉昌林也定定地望着这年轻的支书,望着这张年轻的脸,那目光仿佛在说:“娃子,你是支书了,恁叔得考验你哩,红脸黑脸你都得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