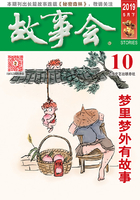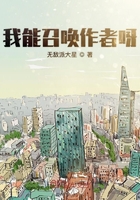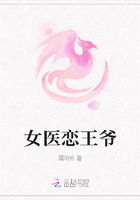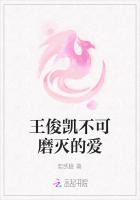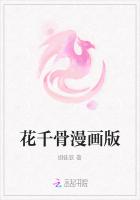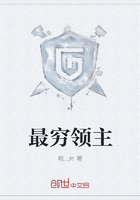我正俯身向前走着,父亲低沉的、气喘吁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到都到了,你慌什么慌?”我站在原地,弓下腰,扭头看着父亲。父亲微恼的、胡须拉杂的脸上挂满了汗水,滴滴答答,不住地往下掉。尽管我穿了新买的“回力鞋”,尽管不过上午八九点钟光景,但太阳已早早地翻过县城东面的落溪山顶,直直地照耀着城厢粮站门口的斜坡,斜坡是干巴巴的水泥铺就的,经过连续几天烈日的暴晒,散发出熊熊的热力,感觉像赤足踩到火盆上。我背过双手,扶住腰间的麻布口袋,直了一下腰,双肩顷刻间如释重负,可手一松,沉重的酸悠悠的感觉便再次裹满了双肩。我其实一点也不慌,只是看着近在眼前的城厢粮站,心里无法抑制地有一点小小的激动;父亲说我慌,想来是嫌我走得太快,父亲好多次说过,路是一步步走的,慢是一程,快也是一程,不必要急的。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走了那么远的路,双肩那么沉,加上即将大功告成的喜悦,我想不加快脚步都不行啊。但是,我没有反驳父亲。父亲的背上也背着帆布口袋,而且装的比我多了一倍还不止,鼓鼓囊囊地压在父亲背上,走平路时还没什么,遇到上坡,父亲微驼的腰身便不得不更深地弯下去。见我停下了脚步,父亲笑了起来,我的小心思,他似乎早已洞穿。一年前,我初中毕业,因为父亲管理的茶园经营遇上了麻烦,我几乎放弃了中考,后来勉强参加了考试,结果却可想而知。新学期一开学,父亲便偷偷跑去学校找老师替我报了名,要我去复读。父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要我去复读的时候,我没答应也没反对,父亲笑着对我说:“去吧,我知道你不甘心,我更不甘心啊……”几天前,我从学校拿回录取通知书,交到父亲手里,像顺利完成了一件父亲交给的作业。父亲把通知书捧在手心,像捧一件珍贵的易碎品,父亲笑了,他的言语更深刻地说明了他内心的兴奋:“我就知道么,我儿,不该像我,一辈子窝在溪头沟里的!”父亲还说了很多的话,其他的,差不多都是喃喃自语,近乎语无伦次了……转眼就到了八月末,录取通知书上的开学时间越来越近,再不把“粮食关系”转到学校,开了学我就将无饭可吃。这就是我和父亲兴奋且急切的原因,父亲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是因为父亲习惯了把自己的情绪藏在在内心里。城厢粮站的院坝是平平展展的水泥地,当空的烈日下,水泥地变成了一张巨大的镜面,隐约地反射出热辣辣的光芒。我和父亲汗涔涔地走过院坝,活像多年后我在汗蒸馆滚烫的木地板上踱步。收粮大厅里空空旷旷的,没有了太阳的暴晒,热力自然减小了不少,放下帆布口袋,浑身刹那间就清清爽爽的了。收粮大厅里摆了一架磅秤和一张竹制座椅,却没有人。我和父亲背着玉米,一大早从溪头沟出发,走了那么远的山路来交粮,却找不到收粮的人。父亲将鼓鼓囊囊的帆布口袋挪到磅秤边,撩起衣服擦了擦眼角的汗水,开始以磅秤为圆心转着不规则的圈儿。一边转圈儿,一边四下里张望。收粮员在院坝角落出现的时候,父亲正转到面朝大门的方向,等父亲发现时,收粮员的身影已经站到了帆布口袋前。“打开。”收粮员说。收粮员指向帆布口袋的手里握着手绢,却一点也不影响他伸出食指,倒是另一只手里端着的白色陶瓷茶杯,因为他身体的晃动,接连发出了几声清脆的响动,有几滴茶水沿着杯沿滴落了下来,收银员赶紧收起握手绢的手,飞快地摁住杯盖。我和父亲七手八脚地解玉米口袋上的绳结。不知道是紧张,还是绳结打得太死,我解开了老半天,父亲还没能解开。在收粮员的注视下,父亲的手微微发起抖来,后来父亲索性低下头,大开的嘴巴不由分说地含住了绳结,双手死死地抓住帆布口袋,下颌接连甩动了几下,很快扬起脸来。父亲满脸通红地牵着帆布口袋的边,露出口袋里黄橙橙的玉米。收粮员拿眼瞅了瞅父亲,端起茶杯,押了一口,然后探着头,朝父亲身前的玉米口袋瞄了一眼:“晒一下。”收粮员说着,又一次伸出握着手绢的手指了指亮光光的水泥地面。父亲的身子一下就挺住了,父亲交过多次粮,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昨晚刚刚从火炕上取下来,又连夜手工瓣下的玉米粒竟然还需要晾晒。父亲想说什么,可收粮员丢下那句话就转身走开了,父亲张开嘴,面对的不过是一张摇摇晃晃的背影。父亲噎在那里。我看着父亲,又看看越走越远的收粮员,也噎在那里。收粮员的身影是接近十二点时出现在磅秤边的。父亲站起身,迎着收粮员,抖抖擞擞地走上前去。父亲笑了笑,想说些什么,就在父亲张开嘴的一刹那,传来了收粮员的话:“搞什么名堂?都快十二点了!”父亲浑身一怔,双腿不觉间开始闪动,险些跪倒在地。收粮员说完,又要转身离开。父亲的脚步那一刻突然变得出乎意料的迅捷。父亲冲到收粮员跟前,挡住收粮员的去路,哆嗦着,变戏法似地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烟。收粮员离开以后,父亲便带着我,将玉米倒了出来,又一点点在院坝里摊开,中途,父亲叫我一个人守着,他要出去上个厕所,如果没猜错,那香烟应该就是在那时候买的。父亲一手捂着香烟,另一只手抓住收粮员洁白的衬衣口袋,准确无误地塞了进去。父亲的动作之果断之迅捷,让收粮员一时没回过神来。“你——”收粮员的眼睛鼓得浑圆,盯着父亲,只吐出一个字便紧闭了双唇。面无表情地回到磅秤边,收粮员指了指父亲,又指了指玉米口袋,心领神会的父亲一下明白了收粮员的意思,飞快地将重新装好的玉米口袋搬上磅秤,又飞快地跟着收粮员走进院坝边的粮食仓库。父亲从仓库出来的时候,双手拿着空帆布口袋,昂首挺胸,活像战场上凯旋而归的士兵。跟着父亲往回走,走到城厢粮站大门的时候,父亲停下了脚步,仰望着天空,正午的阳光映照下来,父亲的脸上立时呈现出一种雕塑般的光彩。那是1990年8月。那一年,我16岁。2013年夏天去正西街,看过文化馆残破的院落之后,我就径直去了街口。昔日的城厢粮站不知什么时候改建成了住宅小区,名字是响当当的四个字:龙府花园。门口的斜坡倒还是多年前的水泥地面,表面的坑洼似乎更多了。我站在街口望着斜坡,满脑子都是那个八月,父亲留在城厢粮站门口的身影。这时候,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从我身边经过,缓缓地、目不斜视地朝斜坡走去。老人颤颤巍巍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风一吹就可能随时倒掉的样子。擦身而过的瞬间,我注视着老人长满皱纹的脸,几乎惊叫而出——老人的面容,像极了记忆中的那个收粮员,只是,他的样子比我父亲的现在还要苍老。我不敢肯定,如果我真的惊叫而出,会不会把他吓着?
交通旅馆
以前,正西街两边都是木头房子,一家紧贴着一家,屋檐连着屋檐。沿街的屋檐槛就是街边的人行道,街窄小,木头房子更显不出丝毫的空阔和大气,文化馆、井阁商场、新华书店等处的楼房相继在正西街落成之后,就更加地衬托出木头房子的低矮和老旧来。隔几户人家的门前就栽了电线杆,线路按着户头,连着一家家的房子。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井阁商场门前最靠近街心的电线杆,上面挂了一块黑板,写着电影院正在上映的电影和放映时间,相邻的电线杆上挂着一块白色小灯箱,灯箱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即便有灯光的映照,“交通旅馆”四个红色的字体也模模糊糊的,很难辨认得清。
电线杆就立在井阁商场与紧挨着的木头房屋的交界处,灯箱上描画的箭头直直地指向木头房子屋檐下的门框,门框上挂着铁门扣,镶了木制门板,木板门向里开着,从没见锁上过。站在门口的屋檐槛上,轻轻一跳就能摸到木头房子的屋檐,再稍稍用点力,就能触及电线杆上的白色小灯箱。
门即是交通旅社的入口。门内的过道穿木头房子而过,曲里拐弯地通到交通旅馆的大门,因为窄逼和视觉里光线的强弱差异,站在街面上看过去,过道是黑漆漆的,怎么也望不到头。
进入新世纪之后,以县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为名,交通旅馆临街的木头房子被拆除,进出交通旅馆的大门于是豁然开朗,交通旅馆的真实面目这才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过往正西街的人们,一扭头就能瞅见交通旅馆的大门和高高的外墙。
外墙从头到脚由一色的砖块砌成,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砖块和砖缝间的水泥灰浆显露出被风化的痕迹,颜色浅淡不一,少部分是浅淡的灰白,大部分已变成淡黑色,烟熏过似的,如若不是门楣上方一抹石灰底的墙面上写着“交通旅馆”四个红色大字,定会有人误以为那是一块旧年遗留下来的碉堡。
进得门去,你会惊奇地发现,远近闻名的交通旅馆竟然也是一座四合院。院子四壁皆为三层小楼,房门皆朝里开着,门前是四面环绕的走廊。院坝右侧靠外的角上有一处悬梯(在墙缝间装上钢筋,用水泥灌注成梯步,安上扶手就成了),拾梯而上,可去到任何一层的房间;左侧靠里的角上还设有一处楼梯,楼梯以院角的立柱为中心,盘曲而上,同样可直达楼顶。一座纯粹中式的四合院,却糅杂着些许西式建筑的特色,真正是中西合璧了。
熟悉正西街的老辈人说,交通旅馆现在的楼房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时期的交通旅馆也是木头房子,完全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天全地处西进甘孜藏区的要冲,西进东去的人到了天全,总是要歇上一脚,充分休整之后再继续前行,那些公干出差的,大多去了纯国营性质的政府招待所和后来兴建的二旅社,交通旅馆则是那些自掏腰包的旅客和卖劳力为生者不二的留宿之地。
交通旅馆后来所以改建成楼房,起因是一场突起的大火,那场大火,让交通旅馆和周围相连成片的房屋顷刻间化成了灰烬。派出所的档案袋里,现在还存留着关于那场大火的调查记录,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是谁在故意纵火,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猛烈的火势最初起自哪里、怎么引起的,总之,那场代价沉重的大火就是一桩悬案,也可以说它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天灾。派出所的档案袋里同时还留存着其他一些有关交通旅馆的记录,被询问人不外乎是外地流窜来天全的扒手、****被捉的乡下民工、平常以餐馆服务员为身份掩护的娼妓、身背腊肉或鸡鸭牛羊的小偷……这些人,也基本就是那个时期交通旅馆的主要客源。每被捉一次,被捉的本性难移的那些人从此转移了阵地,从正西街上销声匿迹,更多的人因为残存的羞耻心和周围随时可能降临的道德攻击,让他们望而却步,少则三五月,或者一年半载,甚或一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交通旅馆的院坝里;派出所每到交通旅馆出一次警,逮住的也基本都是新面孔,从未在档案记录里出现过的,当年办案的警察至今都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
后来就市场经济了,首先受此冲击的是政府招待所和二旅社,政府招待所是干干脆脆地被取消,二旅社则被改了个名字,摇身一变,成了私体性质的天全宾馆,倒是交通旅馆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但其实质也随之由“集体”转成了“个体”。
变化最大的是入住的旅客。这时候,稍稍有些经济实力的人到了天全,就都去了天全宾馆或其他一些后来兴建起来的大大小小的酒店。和交通旅馆相比,那些地方无疑更亮堂更显品位,也更符合旅客们有钱人的身份,但价格却也是水涨船高的,去那些地方入住的人倒不在意这个,他们都是些过路客,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即便是豪掷千金,也是他们乐于为之的。而那些准备较长时间在天全立足又无经济后盾的人,好些就选择了交通旅馆,这里是不够气派但价格便宜,每人每天十块,天底下打着灯笼都难找着的,房间里的一切用具尽管老旧但都是刚刚用肥皂洗过的,而且不管你住一天、一月还是一年,或者更久,都是每天一换的。了解情况的、听了解情况的人介绍的、以前不了解情况住过一次后就记住了的,但凡进了天全县城,就都径直来到正西街,跨进交通旅馆的大门。如此一来,交通旅馆里常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回头客。共同在一个大门里进出,彼此见了面,都觉得相熟。后来就真的熟悉了,没事的时候,就不免三三两两地搬来小凳,坐在交通旅馆的院子里或者走廊间,喝着茶、抽着烟、天南海北地聊天,不知道详情的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是哪家的兄弟或者父子在开家庭会议呢。
交通旅馆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以后,人们便编了一句顺口溜:吃东风,住交通。顺口溜流传很广,上了些年纪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交通即是交通旅馆的简称,而东风则是位于东大街上一家的餐馆,所卖尽皆本地口味的家常吃食,全名东风食堂。两个地方相距不远,从交通旅馆出来,过旧县城十字街口,不几步就到了。
我从未作为旅客进到交通旅馆里去过,东风食堂倒是光顾过几次的,食堂上桌的食物无不满盘满碗的,口味也很地道,价格却和外面相差无几。最早时期的东风食堂也是临街的木头房子,后来也改建成了楼房,但食堂的生意并没有因此变得红火,后来干脆就关门歇业,从食客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与之齐名的交通旅馆却是一直坚持到了下来,时间对于交通旅馆似乎是慢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交通旅馆让时间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它仿佛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正西街乃至整个县城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而交通旅馆,除了外墙上渐渐加深的斑驳痕迹和院坝里不断变换的人影,院坝里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入住的价格依然是多年前定下的,每天十块,不管你住多久,也不管你的本地人还是外来客,床上用品老旧是老旧了,却依旧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交通旅馆现在的管理者(不知道是否就是老板本人或者老板家属)是一位年轻妇人,着粉红的连衣裙,身材高挑,长发披肩。我问她:“你就没想过变化一下吗?”她很肯定地摇摇头,有些答非所问:“不会!”我接着好奇地问:“你就不担心有一天开不下去?”年轻妇人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似是而非地回答:“谁知道呢。”她的话,像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