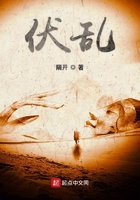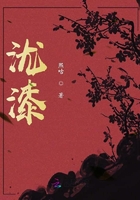一
没有赶上父亲出殡,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瑟缩在腊月的飘着飞雪的大漠小屋里,我头脑嗡嗡嘤嘤鸣响着,满眼泪水。我用拇指在手机上摁出了内心最悲戚的文字,传向四千公里外已回到父亲身边的妻子和女儿。那篇追念文字是由女儿代我陈述的,她哽咽的声音通过冥冥天穹又传回我耳边。那是我的心音,也传导了我的悲哀、绝望以及天崩地裂般的凄凉。
如今,站在没有父亲身影的家里,我觉得一切都变得虚假和惶悚。呆立着,我恍惚又觉得,父亲似乎还在,他肯定就蹒跚在为我买早餐的路上——那是一种被称为“果子”的油饼;或者他就蹲守在楼下炉灶旁煮稀饭,用手轻轻搅着饭勺;或者他正用火钳往炉膛里添加蜂窝煤,炉膛里升腾着暗红的火焰。
这种意象纠缠着我,啃噬着我的灵魂,使我无法安宁。母亲一边哭泣一边叙说着父亲临终的细节,我感觉那就像一部遥远的天书,冥冥地挂在萧索的天上,闪着冷寂的光,不能亲近,不能交流。
二
坐在老旧沙发上,我翻出了父亲遗存的照片——那些被称为遗像的东西。它们被父亲用报纸包裹在一个隐秘的空间里。它们是一叠伴随我出生、学步、启蒙的照片,它们隐匿着我五十年的幸福与欢悦,也隐匿着我肉体生长与灵魂洗练的微妙过程。由于年代久远,它们斑驳而黄旧。我熟识它们的一切。只需轻轻一弹,它们就会还原那些曾经的色彩,漂溢出那些缱绻的亲和之音。小时候,我经常盯着照片遐想,企图发现藏匿在影像背后的清新与私密。
最早的一张已十分黄旧,背后标有“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字样,是三寸黑白照,也是拍摄于照相馆的正规照片。站在照片里的青年军人眉清目秀,肤色细润,脸颊泛着柔和的肉质光泽,自信,青春。我想,它可能是用当年的修相技术在底片上加工后洗印的,不然不会那么清晰那么层次递渐,反差适中。青年军人身着老式棉军服,侧身而立,双腿呈微叉状,显示着男子汉的威严与顶天立地。军人最英武的一面被摄影师表现得淋漓尽致——那老式棉帽上的“八一”五星和左前胸“中国人民解放军”标牌,都炫示着那个年代边防军人的潜在自豪。我想,也可能它是一幅临时而为的照片,因为青年军人穿的是一身旧军装,那肥大宽松的棉衣上,有无数横竖交织的褶皱,并且极深,尤其那膝关节拐弯处,更是交错纵横,如若没有脚上锃亮的黑皮鞋映衬,就无法辨认出是一位军人,倒像个地道的农民。是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解放军大多都来源于农民,他们都是从烟雾弥漫的战场的尸体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军人。他们用拿锄把的手掀翻了蒋家王朝的病体。
照片上的军人不是我父亲,他应该是父亲的亲密战友。我想。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是他与父亲分别的日子。他转业了,退伍了,复员了,也可能调走了,总之,他留下这张三寸全身相。他把他自认为生命中最得意的形象留给了父亲,希望父亲铭记他。
父亲显然做到了。除了日期,父亲还用钢笔留下“摄于伊犁惠远古城”的字迹。这是父亲刻意记下的,它潜伏着深邃又多重的意味。惠远,那是一个在大清王朝乾隆年间就设置有军队的边陲重镇。父亲在那个叫惠远的地方镇守边关十六年之久。清朝时,惠远曾经是著名的西域首府,设有正一品高官——伊犁将军。它一七六三年兴建于伊犁河北岸,是乾隆亲赐的地名,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林则徐和左宗棠就曾被“惠及”到这里。我小时候看赵丹演的电影《林则徐》,电影结尾时林则徐凛然地走向西方。父亲说,林则徐就到我们惠远来了。我惊讶地问,林则徐住哪栋房子。父亲说,在东街。我就偷偷去找过几次,试图找到有关林则徐的只鳞片爪。我很徒劳。父亲在苍凉邈远的惠远十六年当中,从机枪手、炮兵班长、排长、连长一直干到营长,直至一九六五年离开。我清晰地铭记着那些依旧灵动的岁月,它像天幕一样印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
这个站立的惠远军人,我并不认识。一九五二年还没有我。我设想着他与父亲一同站岗的细节。父亲那时已经是排长了,不过父亲扛机枪摆弄子弹的经验却来自这个清秀的老战士,他曾教给父亲一些动枪的细节。在惠远某个天寒地冻的早晨,他们出操了,老战士说,戴上手套,不然钢壳就会粘掉手指的肉皮。老战士说得很随意,却充满真情。我想,这个老战士也许姓章,也许姓欧阳,也许姓郗。总之他成了一个谜。从黄旧的相纸与褪了色的笔迹分析,他与父亲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也许就是他救过父亲的命。父亲曾说,解放兰州战役中,在祁连山的某个断崖上,他的腿曾被子弹打过两个窟窿,是一个姓郗的战友背他下的山。也许他就是那个姓郗的老战士。
三
父亲也有一张那个年代的青年免冠照。二十郎当岁的父亲样子挺可爱,阳光,帅气,浓黑的头发像焗过油一般。当然,那时父亲不可能焗油。——父亲的头发在他七十六岁时仍然是全黑的,这让我很蹊跷。我在四十二岁那年鬓角就开始变白,我非常窝火,我不知道我的头发为什么没有随父亲。父亲的浓眉呈大刀状,眼窝有些微微凹陷,刚毅,智慧,英俊。我小时候看父亲这张照片,脑海里总会冒出一个“英俊”概念——父亲多英俊啊,我会这样自言自语。那时我八九岁,知道一个叫王杰的解放军战士、一个叫刘英俊的解放军战士和一个叫门合的解放军教导员。部队大院的孩子知道最多的当然是部队的事。王杰身扑炸药包救民兵牺牲了,刘英俊拦惊马救孩子被炮车压住牺牲了,门合为保护群众也扑到炸药包上牺牲了。我被他们的事迹撼动着,也时刻想为人民献身。我这点高远又傻气的想法,隐藏在心底许多年。我认为刘英俊的形象洒脱英俊,他的名字和他英俊的外表很吻合。而王杰就没有那么英俊,虽然他也是英雄和榜样。我没见过门合的照片,不好评价。——这又是我一个无知孩童不洁的想法和低级审美观。但我觉得父亲很英俊,他一点不比刘英俊差。父亲只要站在一群军人中间,我总能第一眼认出他,他不仅高大魁伟勇武,而且英俊。那时我经常会长时间地看父亲的照片。父亲在集体合影里,炫亮,夺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韵和气度。
写有“一九六三年八月”落款的照片也是父亲的笔记。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他的所有文化都是十八岁参军后在部队学的。那时父亲在野战军第六纵队的第一线,参加了西府陇东战役,后来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参加了扶郿战役,歼灭了胡宗南部,又攻打了兰州。父亲常说,部队是个大火炉,是熔炼人的地方。那一年,父亲的军衔是大尉。——看到照片,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当年的样子。那是一帧七人照。父亲在前排坐着,表情定格在抿嘴即将大笑的一瞬间。那个瞬间定格了父亲许多内涵。英俊、硬朗、活力、健康、磊落。夏日正午的树荫下,一位军报记者在采访父亲的模范连,父亲作为一名炮兵连长,带队伍很有一套。记者认为还需要一张连队首长的集体照。这个七人照片上,另有两人与父亲的表情一模一样,也定格在同样的抿嘴表情上。我猜想,他们和父亲一样,是被军报记者逗乐了,但并没有笑出声来。他们也同样充满阳光,充满爽朗。他们俩军衔分别是上尉和中尉。当年我甚至能叫出他们的姓名,但现在一点想不起来了。照片上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七人中有五人的军帽色泽已褪成了白色。那是伊犁盆地夏日酷暑暴晒的结果。父亲的军帽当然是最白的那一顶。因为父亲常年带战士在野外训练,摸爬滚打,上哨卡,种地,甚至长途拉练。那时父亲常常不由自主地哼一支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歌曲。父亲认为毒烈的太阳只能烤白鹅黄的军装,却烤不白他健壮而透红的皮肤。白色军帽意味着父亲是一位勇武且吃苦在前的模范连长。
四
“分别留念”的照片最多最抢眼。它们一张张叠加着,被留存在了纸包深处。其实照片定格的那一瞬间,可能就阐释了照片上的主人公将永远不会再见面的现实。那是一份痛苦永别的留念。他们都是父亲的战友或士兵。他们来了,他们又走了,只留下了身影,只留下了回忆。他们是陕西人,山东人,甘肃人,河南人……他们或许是从最贫瘠的黄土坡梁走来;或许是从沂蒙山区的沟壑走来;或许是从华北平原的小村庄走来……他们服役,扛枪打仗,也学文化学做人,并且成长了。但他们又该走了。他们就是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践行者。
一九六五年的照片居多。这一年父亲调出原来的部队,被安排去组建一个新的炮兵单位。今天我无法揣测父亲当年的心态——新的环境将如何面对,又如何适应?但父亲服从了组织,只身一人调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兵营。于是,战友们就纷纷给他送照片。他们是一起摸爬滚打过多年的战友。
照片背面的文字都十分简练。主题直奔主人心境,虽然字体字迹各不相同,但真挚,怀旧,温馨。——“送给老首长赵副营长留念”,“送给敬爱的首长分别留念”,“送给亲爱的副营长留念”……落款分别是“你的战友陈恢白”、“你的战友黄锡安”、“战友王应栋”、“战友闫明义”、“战友康炳南”……
留念,留念,分别留念。留念就是留下念想。这个念想可能今生今世就只是念想了。从此天各一方,再不相见。以当年的交通条件,父亲的新兵营距离老兵营一千多公里,分别几乎就是永别。军旅生涯就这样冷酷,你必须在变幻和不确定中适应这种人生的变数。父亲说,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强,请首长放心。看着照片,我恍惚又听到了父亲极富磁性的声音。父亲的嗓音洪亮、清脆、磁性。我认为我的长相不像父亲,但我的嗓音却酷似父亲。这是我最骄傲和自恋的资本。很多次打电话,总有女士对我说,你的嗓音很磁性,很有男人魅力。有一位美女作家曾对我说,你的声音太男性了,我很想见见你什么样。然而,当我们真的见面后,她却没有提此事,好像早就忘在脑后了。我挺失望。不过,我为遗传了父亲的这个特点而庆幸。
父亲的声音会传导得很远。我曾多次在数百米之外就分辨出父亲的咳嗽声。我对母亲说,爸爸今天要回家。母亲愕然地看着我,以为我在说胡话。果然,十分钟后,父亲就进门了,带回一股热气腾腾的暖意。那时父亲通常住连队,很少回家。他每晚要查房,查岗,甚至给战士掖被角,盖大衣。虽然我家也在营区内,但父亲最多两周回一次家,而且夜里很晚很晚才回来。那时没有双休日,也没有长假。自我记事起,父亲就很少在家吃饭,一日三餐都在连队。
五
一九六八年是奇特的一年。这一年父亲经历了两件大事。那同样是两张极有分量的集体照。父亲后来常常会端着小酒杯回味那一年的往事。父亲啧啧地喝着酒,利落地夹菜,利落地把菜送到嘴里,然后就有很响亮的抽筷子尾声,让人觉得他的饭很香。我曾许多次屏息静气观察父亲的这个举动,企图效仿一下,但总也没有那种愉快的尾声。父亲即便是吃最家常的萝卜白菜,也会如此这般地让人羡慕。
第一件事是父亲见到了******。那一年我十岁,我清晰地记得父亲回家的兴奋与欢悦。父亲说着在北京的感受,如一个孩童。父亲说,毛主席魁伟高大,精神抖擞,脸上很有神采。父亲还说,****就没有那样的气度,不过他打仗还行。父亲说这话时就吃着土豆丝,味道很香的样子。我们——母亲、我、大弟、小弟就很崇拜地盯着父亲的嘴。那一年,“****”进入了白热化程度,也是最波澜壮阔和汹涌澎湃的一年。****别有用心地推崇着“万寿无疆”的把戏,形成了一种山呼海啸的气势和模式。我在纪录片上经常看到那种沸腾场面。我激动万分。后来父亲又数次给母亲和我复述过在北京的细节,也多次重复过一句话:主席真是一个伟大的人。我知道,父亲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父亲从来不表扬人,包括对上级首长,也不阿谀奉承。那一年父亲是作为部队团以上干部代表进京接受******接见的。从北京回来后,全师受接见代表在乌鲁木齐“八楼”合影留念。“****”期间,“八楼”是新疆第一高楼,也曾经有许多年,它一直占据着新疆楼房的最高点。那是一幢庄重威严又令人敬仰之楼。歌手刀郎后来唱过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叫《二○○二年的第一场雪》,里面提到了“八楼”,如今它叫昆仑宾馆。虽然,如今它早已被林立的高楼所湮没,但威严依旧。后来,我几乎年年来这里开会,我不叫它昆仑宾馆,仍然习惯叫它八楼。
父亲站在第三排靠右的位置上。在百名军官队伍里,父亲很醒目,很英武。我一眼就能找到他的身影,也一眼就能看懂他的内心世界。虽然照片上也有许多我熟知的军官,他们大多是我同学的父亲,但我总觉得只有父亲光鲜,俊朗,骁勇。草绿的军装笔挺着,帽徽闪着熠熠的亮光,它们衬托出的是父亲独特而别有一番滋味的风韵。父亲头顶是一幅抢眼的横幅,写着黑体白色美术字——“最最幸福的时刻,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1968年8月11日16时”——多年后,我偶然翻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典》一书,“****”军史大事记一章里说: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在北京接见了解放军六地区陆海空三军******思想干部学习班全体人员。大典上还说,这一年,******分别接见过三次军队干部,总人数超过五万。我想,******这一年太辛苦,日理万机不说,还三次接见几万干部。我十分羡慕和敬仰每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热泪盈眶的人。父亲见到了毛主席,就像我也见到了一样,十岁的我感觉很得意很幸福很骄傲。毛主席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我为有这样一个光荣的父亲热血沸腾了很久。
父亲从北京带回了我终生难忘的两个记忆。一是北京特产“茯苓夹饼”,二是北京故宫紫禁城。茯苓夹饼是一种薄纸一样的食品,中间夹有一种深褐色夹心的甜软食物,很特异,很好吃。那是一种可食的“纸”。我品尝它奇怪的“外衣”,也记住了它的奇妙的名字。长大后我只要到北京,就会购买这种可清火、可明目的食品。二○○六年冬天,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会后抽两天时间回河北看望父亲,还专门买了几盒茯苓夹饼。
我说:爸,我们第一次见到它,就是您一九六八年带回新疆的。父亲笑着说,是啊,三十八年过去喽,现在我传给你啦。我说:您曾经说,这物件能通气,活血,理气,是好东西。父亲说,是吗?我真的说过吗?我说,是,不过现在包装好看了,可味道不如从前好吃了。父亲拿了一片茯苓夹饼,品吃了一会儿,才说,对,好像味道不如从前了。
听父亲说故宫,对于我这个视野仅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圹之地的孩子来说,简直就像听天书。父亲一边吃着苞谷面发糕,一边对母亲和我说,故宫里很大,一天也走不完,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有乾清宫、坤宁宫、储秀宫,是过去皇室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我无知而惊讶地问父亲,什么是妃子?父亲停顿了一下,说,就是皇帝的小老婆。我似懂非懂,老婆就是老婆,难道还有大小之分吗?不过我没有打断父亲对故宫的描述,我只是在自己心中营造了一个奢华皇宫里烟雨缥缈的故事。我想,这辈子我也要去故宫看看,看了我就知道是多大的房子,需要一天还走不完?也就知道什么是小老婆了。父亲还告诉我们一个细节——故宫是从天安门城楼的大门进入的,这令我感到惊奇无比。——天安门不是毛主席接见人民群众的地方吗?怎么是古代皇帝的宫门呢?天安门这个辉煌而崇高的地方,是祖国心脏中的心脏,如一片虹霓,高高悬挂在我的心头。毛主席就站在城楼上挥手指方向。可我没想到,它居然是过去昏庸腐败帝王的家门。我悲哀了很久。——这就是我这个洪荒、封闭年代孩子的可悲之处。这个可悲的疑问曾经潜伏我心底许多年,如同一个死结。
一九六八年,父亲的另一件大事,也是让我自豪一生的大事,这一大事载入了父亲荣誉史册的经历,也是父亲令我仰慕和折服的另一个精神亮点。这一年父亲受命到一个叫精河的天山北坡农牧业县“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父亲“军管”了精河。父亲准确的职务是精河县革委会主任。那一年父亲三十八岁。现在想来,他太年轻了,也太稚嫩了。我妻子说,她记忆中电影电视剧里的革委会主任都是那种很坏很狡诈的人。我说,那是他们瞎胡扯,那时还有很多忍辱负重的好干部。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县长。那照片是一张九人集体照,是当年革委会班子成员的集体照。
隆冬时节,父亲与其他革委会成员身穿五花八门的皮大衣、棉衣,头戴棉帽子,也分别是那种栽绒的、狗皮的、羊毛的。只有父亲一人是戴领章帽徽的军人。父亲身穿棉军服,整洁,威武,从容,洒脱。我以为父亲真正洒脱的标志就是棉军帽。那是一种羊皮制作的棕色皮帽,羊绒蜷曲着,呈现出温暖柔顺的样子,很像一个保暖的小火炉。这种棉军帽,我曾经戴过多年。我们野战部队军人子弟在小学时就开始享用这种特殊用品了。那时天山北坡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院里的孩子们都会使用父亲们积压节省下来的棉军帽、棉手套和大头鞋。那时这种福利也是我们唯一可以享用的优厚待遇。年年冬天,我们数十个孩子们就穿戴着它们,玩打仗,打尜尜,滑冰,或者去红柳梭梭林里打柴火,套野兔。那时野战部队的物品是地方老百姓最羡慕的高档奢侈品。我曾经偷偷用一双军用皮手套换过一个爬犁和一只野兔。我始终未敢把实情真相告诉父母,那也是我迄今为止犯过的最大错误。爬犁和野兔都拿回家了。我和两个弟弟坐爬犁在雪野上奔跑撒欢,然后就吃母亲做的野兔肉,那野兔肉与鸡肉同煮,味道十分鲜美。至今我仍然能回味起当年我饕餮野兔肉的情景。
那时,北疆冬天的积雪很厚,雪没膝盖是常有的事。用爬犁滑雪就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父亲的大皮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显得很松垮,动不动就遮挡住双眼的视线,我于是就有一个上推帽子的习惯动作。那动作后来多年不改,戴单帽子也会不由自主地做。不过,我没有不适的感觉,我觉得我的棉帽子很合适。那时小孩们还会互相攀比帽子质量的好坏,说谁的羊绒顺溜,光滑,谁的羊绒龌龊,肮脏。滑雪滑热了,我们就摘下棉帽子,于是就有一股热腾腾的水汽氤氲地在我们头顶升起,如一个烟囱,白晃晃的阳光射洒在水汽上,如一条升腾的雾霭在头顶漂移,很是艳美。
那个冬天,父亲就一直在那个叫精河的县城忙碌着,春节也没有回家。虽然我家距离父亲的县城仅仅一百多公里,但父亲就像进入了痴迷状态一般,忙碌着,总是说在组织“两派”群众大联合;总是说在访贫问苦;总是说在安排知青到村里插队落户;总是说在修一条叫南干渠的引水大渠。
寒冷的十二月八日,精河县城广场聚集了数万群众,父亲的忙碌有了成效。精河县开始欢庆“两派”群众实现大联合——“革委会”正式成立了。父亲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那时,“革委会”均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而成。它取代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县委和县人委的职权——那是由“****”的“****”走向好转的重要一天。现在看来,它可能还藏匿着诸多的瑕疵和可悲可叹之处,但它却带有那个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光点。父亲夜以继日工作的回报是——头发莫名地脱落。当我在十个月之后见到父亲时,他的头顶居然秃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父亲。一缕缕头发在清晨的枕边呈现窝巢状,如废弃的鸟巢。父亲爽朗地说笑着,就用手捋梳着头发说,哈哈,这一年掉的头发胜过过去十年的总和。父亲后来就不笑了,一边嚼着苞谷面发糕,一边深有感触地说:农村苦啊,老百姓苦啊,有的老百姓家里所有物品也就值五块钱,甚至还不到五块。父亲说着,表情就有些酸楚,让我感到那酸楚既无奈又力不从心。那酸楚也引出我的眼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着转。我默默组构着那个老百姓家里的样子,很恐惧。我想,新社会了,五星红旗下,怎么还会有生活这样贫困苦难的老乡呢?父亲那酸楚无奈的神情让我铭记了四十年。我知道,我肯定还会再铭记下去,直到我的肉体消亡。
照片上,身穿棉军装的父亲有些雄心勃勃。他是革委会集体中个头最高最魁梧的一个。紧挨父亲站立的是一位少数民族同胞,方脸,高颧骨,黝黑,粗壮。另一个年轻人,在灰黑色照片中脸部显得过于白净,并且消瘦,与实际年龄很不匹配。还有一个中年妇女,略显土气,但敦实,质朴。
六
犹豫了很久,我终于下决心将照片装进了我的背包。我看了一下母亲。母亲没有反对,母亲似乎希望我拿走更多的照片回新疆。
辗转数载之后,我奇迹般在精河县找到了一位当年与父亲共过事的干部,他已经是一位耄耋老者。观察了我很久,他才蠕动着皱纹稠密的嘴唇说,像,还挺像赵主任,只是皮肤比赵主任要白一些。我说,我的肤色随我母亲。
老者指着照片说,你父亲左边站的是蒙古族副主任巴德曼,右边的年轻人是群众组织代表副主任陈清甫,那女的叫邱忠和。我惊讶于这位白发老者的记忆力。他说话时如脱口秀一般,快捷准确地说出了他们的姓名。
老照片没了。它们像一个断带,隔断了以后的岁月。我觉得蹊跷,问母亲,母亲说,后来你爸去黑山头带人施工,到九工区施工,都没有留下照片。那时候,施工也都是保密的,你爸没有……带回一张照片。母亲红肿着双眼,不住地用手擦眼泪,我发现母亲苍老了许多,皱纹也更加浓密了。我知道,这是父亲离世,母亲心力交瘁的结果。我不再问母亲。
父亲转业回河北后的照片就基本是我探亲时拍照的了,那都是些彩照。第一次使用彩色胶片是一九八三年,我用海鸥120双镜头反光相机,在石德铁路线的铁道上为父母拍了两人合影。我很稀罕铁路,那时我所居住的准噶尔戈壁小城还没有铁路。父亲笑呵呵的,很知足的样子,比在新疆时瘦了但很健康。照片现在看来有些灰蒙蒙的,色彩还原得也不够真实。冀中平原的阳光似乎缺少准噶尔戈壁大漠的通透与旷远。因为是彩色的,我没有把它们划归老照片。
只有年轻英武的父亲还长留在我的胸间,定格在那些老旧照片上。仿佛,父亲的肉体依然存活着。在冰凉通透的阳光下,他迈着那种坚定的步履,并且老远就能听到他那响亮而磁性的声音。父亲永远呼吸着那些年轻而清新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