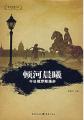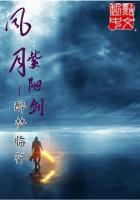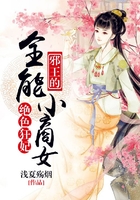萧岱·处女作·重艺术
蔡:先谈谈你印象中的萧岱吧。
程:他比较海派、比较开放,很容易接受新东西。我到《收获》的时候,他七十多岁。他总是觉得自己很保守。碰到作品时,他就说你们懂,你们看着办。他特别好,一些新的东西总是会和我们交谈,征求我们的意见,害怕自己太保守,错过了一些好的、比较新的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有一些关系户。比如领导什么的,总是会来问他说:“我的东西怎么没有给我发表?”陈沂就说过他。他嘴上会很客气,私下则会说:“这种稿子怎么能发?”他人非常正直。一九七九年之后,我们政治上的压力是挺大的,“精神污染”、“自由化”,一年、两年总要来上一次。当时来人都是很严厉的,质问“谁是责任编辑”,这个时候他会说:“我就是责任编辑。”比如张辛欣的作品就碰到压力。《文汇月刊》停刊,就是因为当时发表张辛欣、王若望的作品。还有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不仅仅是政治上、官方的压力,还有社会上其他的压力。当时冰心也打电话来问巴金:“这样的作品怎么能发?”现在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当时压力比现在大多了。
蔡:《收获》给人的印象好像大多是名家名作,新面孔、新人不太常见,是不是这样?
程:在《收获》发表处女作的很多,我们没有专门做过统计。有华东师大的本科生,河南的李洱,还有格非,他们最早的较好作品都是在《收获》上发的。还有王朔,虽然他前面在《当代》发了《空中小姐》,但《顽主》是在《收获》发的。包括萧岱在的时候,当时我们发了戏剧学院一个学生的作品《大巴山下》。还有二〇〇一年第一期的《物质生活》,是长篇处女作。老妞的也是发的处女作。还有叶辛,虽然以前也写过,但最主要的作品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
蔡:《收获》上发表的作品大多数在文学史上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它一直保持平稳的发展势头,这跟编辑部人员审稿的取向有什么关联?
程:跟《收获》的传统有关,很看重文学的艺术性。我们基本上能保证稿子的质量,基本上能体现出当代文学发展的大概走向,能保持这样一种水准。我们刊物现在这样的发行量已保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读者群是比较稳定的,这和编辑部选稿的质量有关,注重艺术性比较强的,我们不太愿意放低我们的标准。最鲜明的例子,包括柯云路的作品,我们从头到尾都没发过。前两天,他给我们打电话,说如果能在《收获》上发作品,他的梦就圆了。我说:“这不是由我来决定的。我们有一套自己的班子,最主要由作品的艺术性来决定。”我还说:“你的作品出去会有很多刊物要,有人会忙着帮助出书,但这和我们的判断无关。”我们所发的作品只体现我们的价值判断。如果要在《收获》上发,觉得还缺点东西。他说:“我不信就不能在《收获》上发表一次。”他跟其他的刊物是很牛的。他给《大家》打电话,说:“来看我的稿子。”他们派两个人乘飞机就过去了。但我们也发了很多新人的作品。在作品面前人人平等,这方面我们并没有什么局限。当然一些作品并不是很完美,我们也有很多遗漏的好作品,有的是因为刊物之间的竞争,互相拉稿子。总的来说水准比较稳定,当然会有很多遗憾。刊物的原因,作家自己的原因,当然,也会有我们的判断原因。每一期都会有不满足,比较欣慰的是,读者比较认可我们的判断。今后顺应整个时代的变化,让整个刊物办得有活力。核心的东西不变,但形式上要新,要吸引新的读者。我们希望有新的读者。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推出有潜力的新作家。比如二〇〇一年第四期,我们想推出“青年作者专号”,很多人对读者来说很陌生,有很多是处女作。
鲜活·朝气·李小林
蔡:《收获》给人的感觉是沉稳,总觉得活力不够。你能赞同这个看法吗?
程: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觉得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文学的调整期,但这是相对的,不妨碍作家个人的创作,也有好作品,有些作品也有很好的质量,比如贾平凹的《怀念狼》。九十年代年轻的作家很多,很丰富,但大多是昙花一现,没有太多好作品出现,包括卫慧。这种创作不会持久,一段时间很引人注目,但很快便会过去,只是一种姿态。文学作品要流传下去必须依靠的还是一种内涵,所以现在整个(进入九十年代的调整期)在各个刊物都有体现,一段时期内都看不到太好的作品,包括《花城》、《大家》。不能说大家都是这样,《收获》就有理由沉闷,我们自身也有原因,现在就在想如何把《收获》办得鲜活一些,有朝气,大的宗旨还放在那里,水准不会降低,争取年轻读者是我们目前最想做的事情,如何使作品适应他们的口味,而不是迎合他们。创作的主体——人本来就年轻化,让这个主体不断流动,这样的创作才有质感。我们也苦于没有年轻的持久的好作者。前几年艺术评判的标准也有些混乱,比如一段时期,陈染她们的“私小说”,我们考虑作为一种文本也可以发一些,但这种东西是不是写作的方向,能不能留下来成为经典,这就需要时间来检验。它是多元中的一元。不仅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批评、理论也都处于一种休整期,没有像样的批评,也没有像样的理论,和八十年代是不能比的,没有显示出一种阵容。回过头看当时是比较壮观的。作家对生活切入的角度有一种调整的需要。我跟池莉有一个谈话,其中说了这么一句话:“星空黯淡不影响星球闪烁。”整个的创作是一种调整的状态,我们尽可能做得好一些。体裁上吸引新的读者,比如栏目的设置搞一些变化,使读者不觉得过于厚重、沉重,而是可以轻松地接受。
蔡:新时期以来,《收获》在原有的基础上,有长足的进展,已经确立了它在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小林是伴随着新时期《收获》的再度复刊就来到编辑部的,她由编辑做起,直到现在成为副主编(巴金去世后,她接任主编——作者补),成为《收获》的当家人,请谈谈李小林对《收获》的贡献,以及她与萧岱有什么不同。
程:从一种传统的对杂志的敬业,整个文化品格的定位,包括做人,他们都有很多相同的东西。大的相同的地方较多,就是对期刊的热爱,很正直,可以顶住压力,他们是中国真正办刊物的人,跟世纪初的文化人一样,把办一本刊物当成一个真正的事业来做。从中国现有生活当中我所了解的其他刊物来看,这样做的已经很少了。除了大的方面倾注的热爱,还包括小的细节上的认真。我们都说李小林有一种特异功能——对错别字的敏感,我觉得她全身心的倾注——刊物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交作家朋友是个传统,李小林跟谌容、张洁、冯骥才、张贤亮都是很好的朋友。比如现在我们去北京做活动,许多作家以一种朋友之间的情谊帮助我们,有一种亲情的东西。比如余华在北京为了《收获》的事奔波,可以自己掏钱请朋友吃饭。他用不着这样,他已经名气很大,不需要这样做。这种感情已超过一般好朋友的关系,有一种亲情在里面。他们会把自己最好的作品给《收获》,这种编辑与作家做朋友的传统从萧岱时期就开始。不太相同的地方,是萧岱当时年纪较大,更多的是放在整个事业上,具体的工作是李小林在做。萧岱对文学作品的敏感性当然和李小林不能比。我们当时很年轻,也很鲁莽,我们总觉得当时和李小林沟通较容易,和萧岱就觉得有点儿累,总是要和他讲,给他解释。
蔡:请你谈谈李小林。
程:李小林在整个文学界的声望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是因为她和作家朋友的关系,另一个是她的家庭的背景、本身的修养都比较高。她对八十年代那些探索性的东西接受起来和年轻人没有任何差别。她的艺术直觉很好,比很多人的都好,她的品位、判断、文化上的修养都特别高。不了解的作家以为她名望高来自于她父亲,但了解的作家都知道她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收获》,当作生命的一部分。她的生活其实是很单纯的,余下的社会活动都没有,全都扑在《收获》上。她事无巨细,包括词的推敲、一个标点,她都斟酌,从这方面来说,我学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来自李小林;对作品的理解分析,与作家交友的方式,都来自李小林。比如说,她对一些作品的修改意见非常较真,她整个人浸在作品当中,对作品的分析非常到位。当然,我们之间也会有分歧,但大的方面不会出现大的偏差。她会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意见,这些意见来自于她对作品的责任感,完全浸在作品中。我想,以后不会有人再像她这样。她在意识上有着追求完美的癖性。她逐渐地显示出自己的声誉,对作品的影响,对作家、对文坛的影响,一部分是她父亲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她自己做出来的。格非写过一篇文章,曾说到李小林身上巨大的完美的人格力量。她性格很透明,一激动就喷涌而出,人极其善良,很为别人考虑,不会整人。她很公开、透明,有什么话就说,也鼓动你说。相对来说,我们《收获》就很单纯,我们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所以比较放松、自然。
专栏·探索作品·海一样广阔
蔡:《收获》发出来的小说比较多样化,相对而言,散文则倾向于发表那些体现出较为浓厚文化底蕴的作品,这里是否隐含着你们的编辑策略?
程:《收获》现在形成这样一种格局——百分之六十是小说,百分之四十是专栏,这是慢慢形成的,有一个过程。从以前的“朝花夕拾”栏目,到刘心武、余秋雨的专栏,其实我们最受启发的是余秋雨的专栏,影响很大。我们不能把散文搞得太杂,太纷乱,所以定位在文化散文这一类上,以此来扩大小说所不能到达的范围,同时和文学又联系得很紧,以此来区别于其他刊物,区别于其他休闲的杂志。二〇〇一年我们又策划了“好说歹说”专栏。这一类散文,读者的反映很好,文化圈子里反映也比较好,后来就形成了固定的形式。当然,我们也想做到,既保持文化性,同时又让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好说歹说”中阿城与陈村的对话就是这样考虑的。搞得轻松愉快一些,同时和读小说的感觉又有不同。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人生采访”一直在办,但好像预期的效果没有达到。当然,生动性、活泼性,与编辑的能力也有关。希望每一期都有一些兴奋点。
蔡:《收获》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曾连续发了不少实验性的探索作品,这是怎样考虑的?
程:我当时也比较年轻,接受国外的小说也多,和马原、余华、格非他们的关系也比较熟,我们当时看出一些新苗子,和他们的前辈已很不一样,通过一种新形式把作家推出去,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另外,我们《收获》本身需要这样一批作家来改变它的面貌。这两个方面促使我萌发这样的想法。像苏童是我的一个同学推荐给我的,后来我请苏童写了个短篇《青石与河流》,现在回过头看,也不是最优秀的,但当时吓我一跳。我想这个人不怎么写小说,以前只写过诗歌,但水准已很高。当时考虑,是不是河流下面涌动着一股暗流,促使我们想把一批作家推到水面上来。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一九八八连续三年的第五期、第六期推出他们,反响很大。我前面说过,《收获》以前有过一段时期总会受到一些外界的干涉,包括当时发出这一批作家的东西,压力很大。一位作协领导就说:“我没一篇看懂的。”当时确实有一些人不接受,因为反馈源源不断,所以隔了一年才又发表一组。后来气氛就较宽松,并且这一批作家的地位也得到巩固。我觉得一个刊物要有生命力,有活力,就应该不断地有新作品,我的这个想法是很强烈的。哪怕这种风格我是不喜欢的,不认可的,但只要有这种东西出来,并在这种写法、这种创作里面是比较好的,我们会用。《收获》能够像海一样广阔,才能容纳创作的景观,才显得大气。李小林就很支持我们的想法。如二〇〇〇年第一期棉棉的《糖》,炒作成那样,我们差一点也出问题。发之前,我一直关注棉棉,也找她谈过,本来我们第一期已经把文章都排好了,后来我听说她的长篇,专门让人从北京用特快专递寄来。我连夜看完,第二天打电话给李小林,说:“这一期的稿子是不是停一停,我有个长篇你看一看。”她看完之后,我问她的感受,我们的感受很相近。我觉得这样的稿子应该第一期就推出来,会有影响,有争鸣。后来把其他稿子撤了,重新编,推出《糖》。后来年轻作家、年纪大一些的作家都很惊奇:你们怎么会发这样非主流的东西。其实,在我的概念里,没有主流与边缘之分。在我的印象里,我有不喜欢的东西,但只要能接受,在它这一类作品中是出色的就可以发,保持《收获》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像二〇〇一年第一期长篇完全是处女作,只有在第一期第一个长篇推出新人新作才会有新的气象。新人的东西虽然不太成熟,但有一种活力,给作者也带来很大的好处,刺激读者,刺激发行。
有遗憾·错失《内奸》·把握当代脉络
蔡:《收获》在编辑过程中有没有遗珠之憾,如某一个好作品由于各种原因流失到其他刊物去了,然而又被证实那是优秀之作?
程:当然有。一方面是我们编辑自身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市场的需求问题,当中还有作家的问题,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把握,他认为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把不太好的、一般的东西给了其他杂志、刊物,但最后时间证明,一般的作品倒是好作品。这就是编辑工作的一个特殊性。比如余华、苏童的创作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中国有太多的作家、精英作家,我们不能做到。由于操作上的特殊性,我们做起来很困难。我们的修养、我们的素质不够,有遗憾。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朱文的一个小说《弟弟的演奏》,拿过来我们看,有六七万字,他自己很看重这个东西。我们确实对他的作品提了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一个是整个作品艺术上有一定问题,节奏很紧张,没有腾挪的空间,有点问题。还有一个是,明眼人一下就看出他在写什么,我们觉得要把这些痕迹抹掉。如果我们《收获》为了你这篇东西把刊物牺牲掉,我觉得代价太大。我们提的意见他不认可,后来发在《江南》上。他们圈子里认为,这是朱文写得有分量的作品,说《收获》没有眼力。但我觉得,这个稿子也许发在《江南》上没问题,发在《收获》上就会有问题。
蔡:我还听说李杭育有一个作品被你们退掉,请展开谈谈。
程:李杭育是有一个作品被我退掉,叫《沙灶遗风》。后来发在《人民文学》上,得了全国优秀小说奖,他曾经因为这件事跟茹志鹃告我们的状,茹志鹃也因为这件事到我们编辑部询问情况。我当初读了他的作品,觉得太沉闷,请他修改一下,加快节奏,但他不干,我们就没有发出来。我们的较大失误是错失方之的《内奸》。后来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我们的审稿变为一个稿子两个编辑轮着看,这样,总体来说,失误要少得多了。我们也“挽救”过一些作品,比如张石山的《一百单八蹬》。它先是被五六个刊物退稿,后来李小林给作者提出修改意见,提升很快,发在《收获》上,被很多刊物转载,包括余华的作品也有这种情况。
蔡:你怎么看待《收获》在当代文学期刊及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程: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为原创作品提供园地的重要刊物。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窗口,还是差距很大的,只能说是一个重要的刊物。新时期以来它没有落伍于文学的整个潮流走向,而是把握了这样一个流动过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如发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但总体说,把握了一种脉络,只能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有操作上的难度,受生存的大环境,受市场上的影响,很难做到反映创作的总体轨迹。市场法则起作用,在判断时会左右我们。有人说《收获》是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我说我们没有做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做到了,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大型刊物,其他刊物还没有起来。
§§后记
我对期刊媒介传播的探究始于十年前。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师承陈思和先生做博士生。在我之前,陈老师的学生中有不少涉及期刊的研究。但他们大多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期刊进行考察。我的研究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期刊。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时间段的延伸而已。但对我而言,其难度不小。因为当时对当代文学期刊的研究文章非常有限,个别的泛泛而谈或者做些简单的资料汇总的文章对于研究来说作用不大。在差不多是白手起家的情况下,我的研究进展十分吃力。好在开始研究《收获》这一大型期刊之前,陈老师曾经让我做过另一期刊《钟山》的研究。此后,我在陈老师的指导下,还分别考察了几个大型的、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如《花城》、《当代》、《十月》等,与此同时,我还对《人民文学》、《作家》、《大家》、《上海文学》等重要刊物也都下了些工夫。在几乎没有参考借鉴的情况下,我采取实证研究,摸着石头过河。我老老实实地逐年逐期翻阅一本本刊物,重要的文章都亲自阅读一番,进行核对、比较、分析,从中得到一些有限的信息。陈老师对我的研究又提出新的要求。他见我只是在书斋、图书馆中阅读资料感到不满意。他要我把期刊看成活的有生命的载体来认识。于是,后来我奔赴京津沪三地,走访了不同时期的当事人,涉及亲属、编辑、作家二十余人,录了不下于四十个小时的语音文档,然后逐一加以整理成文,给《收获》的研究写作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没想到的是,博士毕业后,有近三年时间,我自己也去做刊物,在上海文联的《上海戏剧》杂志社,担任编辑、记者和主笔工作,对刊物从文字到成刊整个流程有了一番切身体会和实践操作。
多年过去了,曾经也有不少人通过各种途径向我索要《收获》研究成果,我都只能告其在刊物发表了的小部分,他们往往很不满足。甚至连《南方周末》的记者为了采写《收获》五十周年的文章也来联系我,要我提供有关资料,但往往也是片言只语,很难道尽其中究竟。现在,幸蒙陈思和老师惠允,博学的周立民兄的鼎力相助,加上能干的师姐孙晶亲自担任责任编辑,终于可以使得巴金与《收获》的研究论稿被列入“巴金研究丛书”并得以出版,我内心的感激真是难以言表。岁月恍惚,过往的时日于我犹如一个有点模糊的记忆的插曲,这也是对我多年倾注心力于《收获》等期刊的一丝慰藉,于己于他善莫大焉。
在此,我特别要感谢陈思和先生的栽培。我要感谢在《收获》研究过程中给予我许多指导和帮助的贾植芳先生。我要感谢曾经提供给我许多各种各样期刊的潘旭澜先生。两位先生生前都对我多有恩惠,至今滋养我的人生,无以为报。我要感谢当年对我论文有所教益的王晓明先生、张德林先生、谢天振先生、唐金海先生。复旦大学周斌先生和郜元宝先生、苏州大学王尧先生等师长也有许多创见对我的论文颇有启迪。我还要感谢所有曾经向我提供援手和各种帮助的人:他们有接受我采访的各位作家、编辑及当事人或有关人士(老编辑郭卓也接受了采访。北京著名作家刘震云在暴雨下开着车接受我采访。著名编辑家王干也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的访谈录由于多种原因,此次未能收入书中。北京青年作家张者和我也有关于《收获》的交流,特意请我吃饭,陪我在北京大学校园转游),《收获》杂志社的李小林老师、孔柔老师、肖元敏老师、程永新老师及王彪、廖增湖、王继军、李国煣各位编辑老师都给予我许多热情帮助,近期一些资料是副主编钟红明学姐拨冗挂号寄给我的。新结识的李明兄从杭州专门回复我资料信息。我的旧房新主人林亨领及其妻兄茅胜权让我查阅并取回《收获》旧刊资料。还有曾经鼓励和支持我的新疆师范大学的许多旧日师长和同事,也是我内心一直感激不已的。另外,我也要感谢曾经发表过我的有关期刊研究文章的《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新文学史料》、《东方文化》、《巴金研究》和《文艺报》的师友们。
我的父亲是我能够不断向前的动力。父亲已经离我而去。我的母亲是位家庭妇女,她没有我父亲的见识,但她多年来从不苛求我为家里做些什么,这也是我有心力来完成学业的重要因素,可也是我的内心难以安宁的痛处。
全书主体部分写于十年前左右,后来虽多次检阅,但都又放回抽屉。最近一年来重新翻阅《收获》期刊,主要是面对近十年的新出期刊,揣摩其发展变化。除了补写了其中的一些延伸部分之外,新写的主要是最近十年最经典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书稿已发表的部分非常有限。访谈先前也只是刊发了很小的部分。此次悉数汇集一起,与过去总算有个交代。
父亲在天上看着我。我必须独自远行了。
二〇一〇—二〇一一年暑期于上海松江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