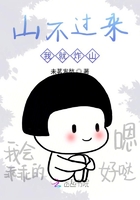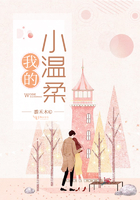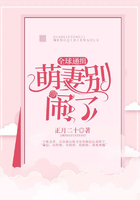在现代生活中,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给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指出:“没有事物不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归根到底都是政治的”(Jameson: 20),影视文化也不例外。按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影视文化正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视文化在宣扬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既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又是意识形态宣传的产物。美国意识形态宣传多年的沉淀和效果在影视作品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们通过影视作品生动表现了他们对社会和世界的态度,这使得影视作品在有意无意间宣传着意识形态,进一步影响或强化人们对社会和世界的态度,使之更趋意识形态化,并在以后的影视作品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反映。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使得主导意识形态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如此一来,意识形态宣传与影视作品两者循环周转,相辅相成,最后人们难以感觉到意识形态宣传的存在,因为它对人们的影响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这样的意识形态宣传往往更像是和风细雨,在不知不觉中点点滴滴地渗透、消融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对人们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是看着电影电视成长的一代。电影电视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娱乐休闲,还对他们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早在1944年就曾预言“电视迟早要产生巨大的影响”(霍克海默:138)。与此同时,他们对电视将会产生的影响却充满了担忧。影视文化到底是如何影响大众的?大众文化理论通常认为,最初是政府通过影视等大众文化传播意识形态,让观众受到政府期望他们接受的意识形态熏陶,从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听凭政府的操纵。当他们在思想上无意识地成为国家和政府自觉自愿的奴隶后,又会自觉地在影视作品中反映他们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世界观,从而进一步潜移默化地影响更多的人。让意识形态化了的人们自觉自愿地宣传意识形态,往往能收到奇效。制片商不仅心甘情愿地在作品中宣扬美国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还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国家和政府的工具。由于从小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已经难以意识到自己正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他们在制作影视作品时,自以为在自由表达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却不知早已成为意识形态的奴隶,只不过在重复主导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当他们把自己的“自由”思想和意志通过影视作品向人们表述时,由于它是打着自由思想幌子的意识形态渗透,其效果比直接生硬的意识形态宣传有效得多。
当代社会,影视文化的无处不在使人们难以逃避意识形态的渗透。现代人难免会受到影视文化的影响,处于心理和精神成长断乳期的青少年,尤其渴望从外界获得指导。这时,“电影、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丹?贝尔:116),为他们“提供一种定位的标准”(Adorno: 89)。“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丹?贝尔:115)“电影放映的运动图像有一种模仿的推动力,吸引观众和听众去模仿。”(Adorno: 158)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影视里的英雄人物无疑给他们提供了理想的自我,让他们去崇拜、模仿。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崇拜的英雄只是意识形态通过影视文化竭力打造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给他们制造一个虚拟现实。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模仿影视里的英雄,以为在实践人生抱负,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实际受到了政府宣扬的意识形态的操纵。这正是意识形态欺骗性的生动反映:“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虚假的意识’,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虚假再现,相反,它就是已经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的’现实自身。‘意识形态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它的存在暗示出了参与者对其本质的无知。”(Zizek: 21)青少年虽然对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一无所知,却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践行。
阿多尔诺把由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他认为“文化工业的全部效果就是反启蒙”(Adorno: 92)。启蒙运动的主题是鼓励人们自主思考,文化工业则剥夺了人们自主思考的能力,“阻碍了自主、独立的个人发展”(Adorno: 92),使大众沦为文化工业和政府意识形态的傀儡和奴隶。阿多尔诺尖锐地指出:“毋庸置疑,文化工业在揣测其引导的成千上万人的意识和无意识心态,但大众却绝不是第一位的,也不是第二位的,他们只是计算的客体,是机械的附加物”(Adorno: 85)。人们“一旦进了电影院,就自动服从”,因为“电影的面具是权威的象征”(Adorno: 82)。对权威的崇拜和信任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剥夺了想象力,放弃了自我判断的权利。人们原本是自己的主体,但影视文化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主体 (Subject)复制变成属民 (subject)”(路?阿尔都塞:176)。无独有偶,阿多尔诺也认为,在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工业里,人们“不是像文化工业试图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国王,不是它的主体,而是它的客体”(Adorno: 85)。尽管消费者在观看电影、电视,尽管几乎所有影视片都是制片商殚精竭虑为消费者量身定做,但消费者远远不是制片商的“上帝”。“梦想工业与其说是在制造消费者的梦想,不如说是把供应商的梦想在人们中间传播”(Adorno: 80)。
如此一来,似乎一切都是“制片商惹的祸”。然而,制片商也是普通的公众,同样会受到美国主导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当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意识形态时,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为政府作宣传,因为他们早已被纳入这一意识形态的体系之中了。我们还需意识到的是,影视等大众文化及传媒一方面在引导公众的舆论,但另一方面也是在迎合公众的期待视野,附和公众的想法。传媒与公众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控制与甘于被控制的关系,而这其中的缘由则是意识形态宣传对人们进行的潜移默化。正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公众希望听到、看到这样一些影视作品,制片商才满足了公众的愿望。正如鲍德里亚指出:传媒既是“权力的策略,旨在蒙蔽大众,灌输自己的真理”,又是“大众诡计的策略领域,因为大众拒绝承认真相,否定现实”(Baudrillard, 217)。制片商在制作影视作品时,必然考虑经济利益,投消费者所好,迎合消费者的期待。他们必然会仔细研究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并在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内表达制片商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因此,影视作品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制片商对消费者的选择和消费者对影视作品的选择。由于制片商和消费者都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乐意表达的、或乐意接受的作品也都沾上意识形态色彩。一个乐意制作,一个乐意接受,两厢情愿,双方在意识形态的游戏中自娱自乐,乐此不疲。如果一部作品过分地反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不仅国家和政府不乐意,而且普通公众也不会满意。也许在政府发出禁演令前,公众的批评或冷淡就足以使影片淡出。正是双方这样的默契,或者可以称为某种“共谋的”关系,使得意识形态通过影视作品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
越战期间,很多年轻人深受战争吸引,如同他们曾经天真的父辈一样。美国的文化传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美国殖民时期的拓荒起,美国人就对英雄推崇备至。而战场无疑是制造英雄的最好地方,很多年轻人都曾渴望成为英雄。五、六十年代出现大量二战题材的影片,集中反映了美国人记忆中光荣伟大的二战。多数美国人并没有亲历二战的炮火,也没有体会到国家沦陷的耻辱。二战给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崇高的道德和最后辉煌的胜利。他们愿意乐此不疲地回忆这些美好而荣耀的时刻。大量的二战影片就反映了人们这种心态。人们对二战的这种记忆当然离不开二战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的宣传,当这种宣传深入人心后,一些文学、艺术家们便把他们对二战的态度用影视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反过来,这些影视作品又影响着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战争的态度。
越战叙事文学生动反映了美国60年代的影视文化对越战士兵和越战一代的巨大影响。很多越战叙事作品都描写了士兵最初对战争的幻想和憧憬。他们这种天真直接来源于所接受的教育和观看的电影。约翰·M·德尔维基奥的小说《第13个山谷》中的詹姆斯·文森特·切里尼刚到越南时,就幻想自己是“二战电影中解放法国或比利时的士兵”(Del Vecchio: 8)。菲利普·卡普托在自传《战争的谣言》里也讲述了电影对他的影响。终于成为一名梦寐以求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后,他“希望在《瓜岛日记》、《撤退,地狱!》和其它二十来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事情都能发生”(Caputo: 14)。在战场上,他为了吸引敌人,故意毫无掩护地晃来晃去,这时他感到自己“是电影《硫黄岛之沙》里的约翰·韦恩,是《战斗哭泣》中的奥尔多·瑞”(Caputo: 269)。1965年,罗宾·莫尔反映越战的小说《绿色贝雷帽》热销全美。同年,好莱坞明星约翰?韦恩主动提出要把该小说改编成电影。他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中写道:“我们到那里(越南)是必需的,让不仅是美国人民,而且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就是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他又向约翰逊解释说:“我们可以通过激发美国同胞的爱国热情达到这一目的。”(Suid: 136)此举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全力支持。1968年电影摄制完成,果然鼓舞了一大批年轻人志愿报名入伍,开赴战场,去圆他们当战斗英雄的梦想。
约翰·韦恩经常扮演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英雄。他饰演的角色充满阳刚之气,在困境和险恶环境下总能表现出超常的智慧和勇气。他是硬汉子、真英雄的化身,常常让观众赞叹不已,更让青少年观众羡慕万分,渴望也经历他那样的历险,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他的名字频繁地在越战叙事作品中出现,甚至已成为动词和形容词:He was John Wayneing;Stupid John Wayne soldiering。每个周六下午,老兵罗恩·科维克都去看“约翰·韦恩和奥迪·墨菲的战争片”39:“《硫黄岛之沙》里的约翰·韦恩成了我的英雄。”(Kovic: 55)无独有偶,在詹姆斯?韦布的小说《火力场》里,主人公霍奇斯小时候,也会“与六、七个朋友在周末下午步行五英里”去看《硫黄岛之沙》、《道谷里桥》等战争片。对孩子们来说,“如果约翰?韦恩不是上帝,他至少也是先知”(James Webb: 34)。1960年,一群海军陆战队士兵被问及为何入伍时,“约一半的人都表示是因为看了约翰?韦恩的电影”(Novelli: 107)。罗恩?科维克在自传里直言不讳地称:“我想当英雄”(Kovic: 63)。约翰?韦恩一直是他效仿的榜样。高中毕业时,海军陆战队军官来学校招兵,科维克与他们握手时,“禁不住感到,我是在与约翰?韦恩和奥迪?墨菲握手。他们那天告诉我,海军陆战队从身体、意志、精神上塑造男人。我们可以像年轻的总统号召的那样为国效力”(Kovic: 74)。约翰?韦恩影响的不仅是几个崇拜英雄的孩子,而且是整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对越南战争的态度。
从越战叙事作品里,我们看到影视文化带给主人公最深的影响是英雄情结。发源于希腊文明的所有西方文明一直赞颂英雄,赞颂那些为国家和民族捐躯的爱国英雄。美国由于其独特的拓荒殖民历史,对具有超凡能力的孤胆英雄又有另一种景仰和推崇。越战期间,年轻人渴望成为的英雄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爱国保家的英雄;二是无私助人的英雄;三是英勇睿智的英雄。越战士兵在战前看的战争片多为反映二战题材的影片。二战通常被看作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为反抗残暴的法西斯分子进行了不屈的努力。美军士兵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取得了军事和道德上的双重胜利。如果说帮助弱者、抵抗邪恶、颂扬英雄原本无可厚非,那么,看着二战影片长大的年轻人却没有意识到,美国二战中的敌人不同于越战中的敌人。他们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也就混淆了二战与越战的本质区别。而那些越战影片,也通常故意忽略越战与二战的差异,鼓励人们像参加二战一样去参加越战。电影在表现战争目的时很巧妙。谈到战争片处理“我们为什么打仗”这一问题的策略时,评论家凯瑟琳?金尼指出,电影“通常用个人对象征社会的小部队表现出的忠诚和责任来表现,而不直接谈论历史或意识形态”(Kinney: 16)。正是在爱国、忠诚、责任等价值观的激励下,无数青年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印度支那,在异乡的土地上作战,保卫美国的国土不受共产主义势力的侵犯。只有到了越南后,一些士兵才似乎猛然感悟:“越共并没有强奸我的姐妹,胡志明也没有轰炸珍珠港”(Hasford: 67)。只有在这时,他们才开始产生疑惑。而此前,他们看的二战片通常只呈现了战争的英勇场面,把他们淹没在爱国情绪、激烈战斗和鲜花荣誉里,让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战争的本质。一位母亲就曾批评过影片“把越南置于与二战相同的道德框架下”,“用同样的色彩去描绘越南”(Emerson: 11)。
影视作品谈到越战时,一方面把越南问题与美国自身的安全相联系,另一方面又把政府派兵到越南与无私的国际援助和道德情操相结合。二战刚结束,美国人就认为他们应该勇于承担起拯救全世界的责任。很多美国人渴望“改进整个宇宙”(Greene: 13),并以做一个伟大的救世主而沾沾自喜。美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相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指派来给所有民族做榜样的伟大民族。很多电影反映了美国人这种以世界救星自居的自大情结,吸引年轻人去为世界民主献身。受其影响,很多年轻人最初也真诚地相信他们是为了提供无私的国际援助才来到越南,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越南人民。一些小说的主人公相信他们是“为了保证自由世界的疆界不会进一步缩小而战斗”(Moore: 13),“是为了正义与持久的和平而战,只有这样,爱和平的南越人民才能享受选举的民主,不用生活在共产党侵略的威胁下”(Huggett: 338)。他们甚至真诚地对越南人许诺:“我们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援助。我们来是为了保证安全和独立。”(Del Vecchio: 563)
战争片不仅把战争置于保卫国家安全、提供无私援助的语境下,还将此与士兵个人的理想和人生价值紧密结合,凸现了战争对男人的诱惑力。影视作品强调了残酷、艰险的战争对士兵个人提出的挑战性,强调了士兵在战场上表现出的英勇对维护男性尊严、男人身份的重要性。41 自殖民拓荒时期起,美国文化就赞扬男人面对挑战和危险时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气,这也成为美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民族特性的传统组成部分。大量西部片里的英雄和牛仔就是这种拓荒精神的化身。60年代,在美国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已消失之时,肯尼迪总统热情洋溢地鼓舞年轻人去开辟新边疆。许多人无疑把战场、把越南视为可以任由他们驰骋和冒险、体验非凡人生的新边疆。小说《伤亡统计》里的霍金斯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前往越南,就是因为他“想成为它(越战)的一部分,想体验它,感受生活的跳动”。“他想去是因为它具有挑战性,他想获得并掌握领导士兵、战胜敌人的艺术,以获得自我满足。”(Huggett: 78)一些年轻人渴望历险、体验战争的愿望甚至是无条件的。每个周末与朋友步行五、六英里去看战争片的霍奇斯宣称:“即使没有越南,他也得制造一个出来。…… 重要的是战斗,而不是原因。”(James Webb: 34)这些年轻人不在乎战争的意义,只渴望爆发那么一场战争,让自己有机会到疆场纵横驰骋,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男人。影视作品里像约翰?韦恩这样的铁血男儿都是在战争的险恶环境中,才充分展现了男人的魅力。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战争,战斗经历成为男人成长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可以炫耀一生的荣耀。可以说,影视作品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拒绝战争,就是拒绝成为男人,甘当懦夫;拥抱战争,才算接受了男人的挑战,才可称作男人。年轻人可以选择不当爱国志士、救世英雄,但他们却不得不当一个男人。影视作品对懦弱胆小者的嘲笑和鄙视,使很多年轻人没有勇气不做约翰?韦恩式的英雄。甚至一些父母也用约翰?韦恩为榜样来教育孩子。蒂姆?奥布莱恩借小说人物之口无奈地表示:“我害怕被认作是一个懦夫,我对此的恐惧甚至超过对懦弱本身的恐惧。”(O’Brien, 1978: 322)最后,他承认:“我是个懦夫,我去参战了。”(O’Brien, 1991: 63)人们把理想男性的形象投射在银幕上,以银幕上的理想男性为榜样去教育年轻人,给年轻人一种暗示:如果他不能像银幕上的英雄那样英勇无畏,他就不能被称作男人。正是这种无形的压力使很多原本不愿前往战争的年轻人除了奔赴疆场,别无选择。
影视文化给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留下直观的印象,让他们相信战争提供了开辟新边疆的一条途径,为实践爱国情怀、提供无私援助和迎接挑战冒险铺设了一个完美的平台。有的士兵对影视作品充满了信任,甚至将之视为“父亲的替身”,虔诚地接受教诲,从中学到“杀人正确和错误的方法”(Baker: 170)。还有人坦言:“我想杀坏人。你在电影电视里看到坏人和好人,我就是想去杀坏人。”(Baker: 41)然而,问题在于,究竟谁是坏人?影片由于要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包含众多信息,情节一般高度紧凑,因此会把许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的背景材料,其中就包括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对敌人的定义。影视作品没有去剖析为什么美国要与某个特定的个人或群体作战,通常只简单地把对手直接定义为“敌人”。美国政府宣布在越南的共产党是敌人,威胁着美国的安全,威胁着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后,人们也就顺理成章、不假思索地把越南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影视片也乐得不再多费口舌,把复杂的事物进行简单化处理。影视作品和人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告诉他们,人有好人坏人之分,敌人就是坏人,而坏人是应该被杀死的。最初的逻辑是这样:因为某人是坏人,所以他自然就是敌人。但渐渐地,人们却陷入了一种逻辑怪论:因为某人是敌人,敌人就等于坏人,杀死坏人不但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还是一种为民除恶、维护和平的英勇行为。
影视文化向人们展示了行为的蓝本,却没有解释隐藏在一切行为后面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它通常越过本质原因,简单地把敌人抽象化、概念化、面具化、甚至妖魔化,把观众的注意力直接吸引到如何消灭敌人上。越战中的胡志明被描述为一个恶魔,希特勒式的暴君。这样,美国便有了充分的理由和正义对之进行口诛笔伐、乃至枪击炮轰,因为他们是在试图杀一个坏人。只有到了越南战场后,士兵们才会发现在越南,要把敌人与朋友、好人与坏人区别开来,并非易事。罗恩?科维克就曾惊呼:“电影里从来就不是这样的。那里总是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有牛仔和印第安人之分,总是有敌人和好人在相互厮杀。”(Kovic: 194-195)(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我们可以注意到,科维克在不知不觉中,用“敌人”一词取代了“坏人”,因为对他来说,这两者是完全可以互换的同义词。但士兵们还会惊讶地发现,所谓的敌人并不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与敌人真正接触后,他们发现很多敌人其实也像他们一样,也是善良无辜、热爱生命的普通人。
影视文化除了让天真的青年对战争充满幻想和误解之外,还给了战场上的士兵扮演电影角色的幻觉。6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士兵可以通过电视看到自己作战的场面。战争新闻报道与影视片的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士兵演电影和“作秀”的意识。42“正因为电影总是想去制造常规观念的世界,所以,常看电影的人也会把外部世界当成他刚刚看过的影片的延伸。”(霍克海默:141)电影实际上给人们制造了一个虚拟现实,让人们生活在幻觉中。迈克尔·黑尔在新新闻体作品《新闻快报》里指出,一些士兵模糊了电影与现实的界限。对他们来说,生活犹似电影,战争仿如电影。有的士兵如果看到有记者在摄影,就会表现得勇猛异常,在战场上毫无掩护地冲锋陷阵。他仿如一名演员,不是在参加战斗,而是在拍电影。他们实际上把战争当作了电影,在头脑里演绎着自己的电影。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战争与电影的区别:真正的战争没有剪辑,如果你死了,就真的死了,从你的伤口里流出来的不是拍电影时用的颜料,而是真正的、鲜红的、火热的血。
影视作品定格了英雄的形象,一些士兵因天真地模仿影视里的英雄而无端地丧失了年轻的生命。有的士兵拒绝匍伏前进,躲避敌人的炮火,因为他看过的所有电影都告诉他英雄是不会匍伏前进的。他高喊:“我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官。我不会用肚子爬着前进”(Caputo: 159),结果却身负重伤,再也无法站起来。在斯蒂芬·赖特的《绿色沉思》里,怪人温德尔?佩恩是1069情报队的摄影员。他以战场为电影场景,让士兵作演员,把战争当剧情。他会指挥士兵像演员一样做出种种动作和姿势,来配合他摄像。实际上,越战时期,电影、电视摄影师到部队摄影时,让士兵弄虚作假,假装对敌射击,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大部分士兵也难以摆脱上镜、当一回演员的诱惑,都愿意听从摄影师的指挥。因此作秀已司空见惯。温德尔在自己受伤临死前,还不忘指挥战友格里芬把自己死亡的过程拍下来,扮演了自己电影作品里的最后一位角色。这些士兵明知战争不同于电影,却宁愿生活在美好的幻觉之中。他们在摄影机前表现神勇,似乎是为了观众、为了别人去表现,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自己。士兵表现“英勇”是希望把自己认同于银幕里的那些英雄,获得他们的认同,并以此来获得银幕前所有观众的认同,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可。这正显示了影视文化的强大影响。越战作家及记者黑尔看到这些“因来越南前看了17年战争片而永远逝去的孩子们”时,无比痛心:“我们都看了太多的电影,在电视城里呆得太久。”(Herr: 209)
来到越南后,士兵们发现自己非但不能成为所向披靡、英勇无畏的战斗英雄,也不可能给越南人带去自由与民主。如果说他们的到来给越南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不同,那就是制造了更多的孤儿、寡妇和灾难。然而,一些士兵即使意识到这一点后,仍难以摆脱当明星的诱惑。在加斯塔夫·哈斯福德的小说《短刑犯》里,士兵们争相和越南孤儿照相,好把照片寄回家乡,在报纸上登出来。照相时,他们摆好姿势,举起一块橡胶假糖递给孩子。正如在场的一名士兵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你们这些家伙可能杀了这孩子的亲人,但在你们的家乡,你们却是有着金子般心灵的强壮的海军陆战队士兵。”(Hasford: 56)这些吝啬得甚至不愿给孩子们一块真正糖果的“高尚士兵”把这样的照片寄回家乡、并刊登出来后,还会给更多的年轻人制造幻象。
然而,战争残酷的现实最终还是打破了许多曾经豪情万丈的年轻人的幻想,击碎了他们佩满奖章、荣归故里的英雄梦想。美军士兵发现根本不能像电影里那样与敌人短兵相接,尽显英雄气概。战斗中,他们还发现手榴弹并不是像电影里那样用牙咬掉引火线,他们也不能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毫无顾忌地冲锋陷阵。久而久之,他们不再渴望做英雄,他们所渴望、所祈求的只是能活着回国。战争的现实让他们意识到,约翰·韦恩式的英勇和所有那些影片表现的英雄主义都是虚幻,年轻人被吸引到军队和战场,然后又被无情地推出梦境,推进血淋淋的现实。这时,他们会深切感受到影视文化只给观众制造了一场幻象的越战,不会再把影视里的那种战争当作他们的战争和他们正在经历的现实。如果说,没有经历战争残酷的士兵尚且天真,那么,真切体会战争的士兵则最终在炮火中成熟起来,这时,“他不再需要一个外在的认同点,因为他已经实现了自我认同 —— 他‘已经变成了自己’,变成了一个自主的人”(Zizek: 110)。他们从影视文化的“属民”成长为独立自主的“主体”,不再需要从电影、电视里寻找英雄和模仿的对象。他们以天真和理想为代价,换取了对残酷现实的理解,从而抛弃影视文化制造的英雄梦想,开始勇敢地直面现实。
正因为士兵们认识到电影的欺骗性,所以后期的越战叙事作品常有对英雄主义影片的批评。加斯塔夫·哈斯福德笔下的士兵把电影《绿色贝雷帽》斥为“一部讲述热爱枪战的好莱坞肥皂剧”(Hasford: 38)。小说中,在观看该影片时,看电影的士兵肮脏不堪、着装凌乱、胡子拉喳,而约翰?韦恩饰演的越战士兵则英俊潇洒、军装笔挺、皮鞋锃亮。银幕内外的士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难怪士兵会大声嘲笑影片对越战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处理。影片中的一个人物鼓励士兵们说:“首先杀死该死的越共 …… 然后回家。”看到这里,“海军陆战队的观众哄然大笑。这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看的最滑稽的一部电影”(Hasford: 38)。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越共”杀之不尽,回家的日子遥不可及,士兵们才对这部反映英雄主义的影片嗤之以鼻。电影结尾处,约翰?韦恩领着一名满怀希望的越南孤儿,面朝东方,走进灿烂的“夕阳”。43 士兵们再次放声大笑,影片里的激情豪迈和温情脉脉与现实里的丑陋卑劣和残酷无情有着天壤之别。士兵们对影视文化的态度已从入伍前的崇拜和羡慕转变为此刻的讥笑和嘲讽,他们在银幕前爆发的笑声蕴含着深深的辛酸与无奈,因为,经历过战争的士兵都知道影视文化制造的幻象世界在现实中是多么地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