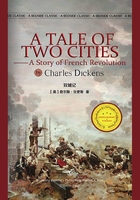第一部
“你到底是何许人?”
“我属于那种力的一部分,
它总想作恶,
却又总施善于人。”
——歌德《浮士德》
暮春的莫斯科。这一天,太阳已经平西了,却还热得出奇。此时,牧首[1]湖畔出现了两个男人。身材矮小的那个穿一身浅灰色夏季西装,膘肥体壮,光着秃头,手里郑重其事地托着顶相当昂贵的礼帽,脸刮得精光,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得出奇的角质黑框眼镜。另一个很年轻,宽肩膀,棕黄头发乱蓬蓬的,脑后歪戴一顶方格鸭舌帽,上身穿方格布料翻领牛仔衫,下面是一条皱巴巴的白西服裤,脚上蹬一双黑色平底鞋。
这头一位不是别人,正是柏辽兹[2]·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他是莫斯科几个主要的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之一“莫文联”的理事会主席,同时兼任某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他身旁的年轻人则是常以“无家汉”[3]的笔名发表作品的诗人波内列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两位作家一走进刚刚披起绿装的椴树林荫中,便朝着油得花花绿绿的商亭快步走去,商亭的招牌上写着:“啤酒,汽水”。
噢,对了,我必须首先交待一下在这个可怕的五月傍晚发生的头一桩怪事:这时,不仅商亭旁边没有人,就连与小铠甲街平行的那条林荫道上也不见一个人影;太阳把整个莫斯科晒得滚烫,现在正裹着干燥的烟尘向花园环行路西面沉去,人们热得似乎连喘气都费劲,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走进这椴树荫下,没有一个人坐到这张长椅上。整个林荫道空空荡荡。
“请给我们两瓶纳尔赞矿泉水[4]。”柏辽兹对柜台里面的女售货员说。
“没有纳尔赞矿泉水!”售货员回答,不知为什么她好像很生气。
“有啤酒吗?”无家汉用嘶哑的声音问。
“啤酒过一会儿才能运来。”妇女回答。
“那,有什么?”柏辽兹问。
“有杏汁水。不过,是温吞的。”妇女回答。
“行啊,来两瓶吧,两瓶!……”
打开杏汁水,冒出很多黄色泡沫,空气中顿时弥漫开一股理发馆的气味。杏汁水刚刚下肚,两位文学家就打起嗝来。他们付清账,坐到长椅上,面对湖水,背朝着铠甲街。
这时又发生了第二桩怪事,不过它只涉及柏辽兹一个人:忽然,柏辽兹不再打嗝了,只觉得心脏咚地跳了一下,便无影无踪了;过了一会儿心脏回到原处,上面却像是插了一根钝针。不仅如此,他还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恨不得马上不顾一切地逃离这牧首湖畔。他惶惑地回头望了望,仍不明白自己究竟怕什么。他的脸变得煞白,他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暗自想:“我这是怎么啦?从来没有过这类事呀……准是心脏出了毛病……劳累过度。看来是得大撒手了,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我呢,先到基斯洛沃德斯克去疗养疗养……”
忽然,他觉得闷热的空气仿佛浓缩起来,奇妙地在他眼前交织成了一个透明的男人,样子异常奇特:脑袋很小,却戴着一顶大檐骑手便帽,方格料子上衣十分瘦小,像空气一样轻飘飘的……身高足有两米开外[5],肩膀却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您注意,他那副神态活像在捉弄人。
柏辽兹的生活向来一帆风顺,所以他很不习惯于看到异常现象。他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了。他瞪着眼睛,心慌意乱,暗想:“这种事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种事确实在他眼前发生了:瞧,那个细高个儿的透明公民双脚飘离地面,正在他眼前左右摇晃呢!
柏辽兹吓得急忙闭上了眼睛。当他再睁开眼时,一切已经过去:幻影消失了,穿方格衣服的家伙不见了,插在心脏上的那根钝针也像同时被拔去了。
“咳,真见鬼!”主编大声说,“你看这事儿,伊万,刚才我差一点中暑!甚至出现了幻视!”虽然他强作笑容,眼神里却依然透着恐惧,两手还在抖动。
但他终于渐渐镇静下来,把手绢一挥,打起精神说:“好吧,咱们接着谈……”他继续谈起了刚才因喝杏汁水中断的话题。
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场有关基督耶稣的谈话。原来主编柏辽兹曾约请诗人为下期杂志创作一首反宗教题材的长诗。无家汉只用很短时间就写出了一首,但遗憾的是主编对这首诗很不满意。尽管无家汉在诗中描绘主要人物耶稣时所用的阴暗色调已经相当浓重,主编还是认为全诗必须重写。现在,主编就是在给无家汉上有关耶稣的“课”,指出这位年轻诗人的主要错误所在。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诗究竟为什么没有写好,这很难说。也许该怪他有天才而不善于表达,也许是因为他对所写的题材一无所知。总之,他笔下的耶稣虽说并不讨人喜欢,但却完全是个活生生的人。而柏辽兹现在就是要向他说明:主要问题不在于耶稣本人好坏,而是耶稣这个人物本身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所有关于耶稣的故事纯属虚构,全是不折不扣的神话。
应该说明,这位主编本是个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他的谈话自然是旁征博引,有根有据。譬如,他指出:著名的斐洛[6]和博学多才的约瑟夫·弗拉维[7]等古代学者的著作中就只字未提耶稣其人的存在。这位主编为了表明自己学贯古今,还顺便告诉诗人说:著名的塔西佗的《编年史》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中所写的处死耶稣之事[8]也无非是后世人的伪托编造。
对无家汉来说,柏辽兹所谈的一切全都闻所未闻,他唯有用一双机敏的绿眼睛盯着主编,专心致志地洗耳恭听,只是偶尔打个饱嗝,暗暗咒骂那该死的杏汁水。
“东方人的所有宗教中,”柏辽兹继续说,“总的说来,全都提到过贞洁处女生育神子的事。所以,并不是基督徒们首先想出了这个新花样,他们只不过用同样方法造就了一个自己的、实际上并未存在过的耶稣而已。因此,您的诗也就应该把重点放到这方面……”
柏辽兹的男高音在冷清清的林荫道上空飘悠、回荡着。他的宏论一步比一步玄远,一层比一层深奥,除非异常饱学而又不担心弄坏自己脑子的人,没有谁敢钻进如此奥秘的学术领域。诗人越听越有兴趣,所受的教益也越来越多:他不仅听到了关于埃及善神和天地之子奥西里斯[9]的故事,得知腓尼基人有个法姆斯神[10],知道了马尔都克[11],甚至还听到了关于不甚有名的、从前墨西哥的阿茨蒂克人[12]曾经十分尊崇的那位威严可怖的韦齐普齐神的故事。
恰恰是在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对诗人讲到阿茨蒂克人怎样用面团塑造韦齐普齐神的形象时,林荫道上出现了头一个身影。
关于这个人的外貌,坦率地说,只是到了后来,到了一切都已无法补救的时候,各有关机关才提出各自的描绘材料。可是,把这些材料一对照,又不禁使人瞠目结舌:一份材料说此人身材矮小,镶着金牙,右腿瘸;另一份材料则说他身躯魁伟,镶的是白金牙套,左腿瘸;还有一份材料只是简要地说此人没有任何特征。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材料统统一钱不值。
首先,这个人身材并不矮小,可也说不上魁伟,只不过略高一些,他的两条腿都不瘸。至于牙齿,则左边镶的是白金牙套,右边是黄金的。他穿着昂贵的灰色西装,脚上的外国皮鞋与西装颜色十分协调。头上一顶灰色无檐软帽歪向一旁,压到耳梢,显得整个人那么俏皮、矫健;他腋下还夹着一根手杖,手杖顶端镶着个乌黑的狮子狗头。看模样年纪在四十开外。嘴有点歪。脸刮得精光。一头黑发。他的右眼珠乌黑,而左眼珠却不知怎么呈现出嫩绿色。两道黑黑的浓眉,可又是一高一低的。总之,这是个外国人。
外国人从主编和诗人落座的长椅旁边走过时,朝他们瞥了一眼,随即收住脚步,竟在离两位朋友几步远的另一把长椅上坐了下来。
柏辽兹暗想:“是个德国人。”
无家汉想:“准是个英国人,看,还戴着手套,也不嫌热。”
这时,外国人朝湖水四周的高楼大厦环视了一下,露出初来乍到颇为好奇的神色。
他先是注视着高楼的上层,注视着上层那光灿夺目的玻璃窗中折射得歪歪扭扭的、正在一步步永远离开主编柏辽兹的夕阳。然后他把目光往下移,看到下层楼房的窗户已经暗淡下来,预示着黄昏的到来。他不知冲什么东西傲岸地笑了笑,然后眯上眼,两手搭在手杖镶头上,又把下巴放在手背上。
“你呀,伊万,”柏辽兹继续说,“有些地方写得很好,很有讽刺味道,比如,写神之子耶稣降生的那一节;但主要问题在于早在耶稣之前就已经降生过不少神之子了,诸如弗利基亚人的阿提斯[13]等等。简而言之,这些人,包括耶稣,都根本没有降生过,没有存在过。所以,你应该写的不是什么降生,不是什么东方占星家的来临[14]等等,而是必须表明:关于耶稣降生之类的传说完全荒唐无稽……不然,照你现在这样写法,好像真有个耶稣降生过似的!……”
此刻,深为打嗝所苦的无家汉正屏住呼吸想把一个嗝儿憋回去,谁知这样打出来的一声嗝儿反而更难听、更难受了。就在这个时候,柏辽兹停止了议论,因为旁边那个外国人忽然站起身,朝他们走过来。
两位作家惊讶地望着来人。
“请二位原谅,”来人讲话带点外国口音,但用词倒还正确,“我们虽然素不相识,可我还是不揣冒昧……因为我对二位的高论实在太感兴趣了……”来人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行了个礼。两位朋友也只好欠身还礼。
柏辽兹暗自琢磨:“不,他多半是个法国人……”
无家汉想:“也许是个波兰人?”
这里我还必须补充一点:方才外国人刚一搭腔,诗人便觉得他十分讨厌,而柏辽兹倒毋宁说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不,也还不能说是喜欢,而是……怎么说呢……就算是对他发生了兴趣吧。
“能让我坐一坐吗?”外国人彬彬有礼地问道。于是两位朋友像是不由自主地各自往旁边一闪,外国人便麻利地在他们中间坐下,并且立即攀谈起来。
“假如我没有听错,您刚才是在说根本没有过耶稣这个人?”外国人用绿色的左眼望着柏辽兹问道。
“对,您没有听错,我刚才是在谈这个问题。”柏辽兹客气地回答。
“啊,这太有意思啦!”外国人高兴地大声说。
无家汉不由得蹙起眉头,暗想:“见鬼,这干他什么事?”这时,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却朝右一转身,向无家汉问道:
“那么,您也同意这位朋友的看法?”
“百分之百!”诗人直言不讳。他讲话向来用语新颖,喜欢形象化。
“不胜惊讶!”不速之客激动地说。随后,他不知为什么贼眉鼠眼地四下瞅了瞅,压低他原本就很低沉的声音悄声说,“对不起,我可能有些过分纠缠,不过,请问,据我理解,您二位,别的且不说,也不信上帝吧?”他眼里流露出惶恐的神色,并且立即补充道,“我发誓,我对谁也不说。”
“不错,我们不信上帝。”柏辽兹回答。他见外国游客如此惊恐,便微笑着补充说,“其实,这种事完全可以公开谈论。”
外国人更加惊讶了,他轻轻尖叫一声,把身子往椅背上一仰,又问道:
“二位都是无神论者?”
“是的,我们是无神论者。”柏辽兹还是面带笑容地回答。无家汉却在气鼓鼓地想:“瞧这外国佬,纠缠起来没完啦!”
“噢,这可真妙!”奇怪的外国人又大声说,不住地朝两旁的文学家转动着脑袋,看看这位,又看看那位。
“在我们苏联,没有人对无神论感到奇怪。”柏辽兹用外交官的谦恭语调说,“我国大部分人民早就自觉地不再相信那些关于上帝的神话了。”
这时,外国人又表演了新的一招儿:他站起身来,伸手同愕然危坐的主编握了握手,对他说:
“请允许我向您致以由衷的谢意!”
“您这是为什么谢他?”无家汉眨了眨眼睛,问道。
外国怪客意味深长地举起一个手指头解释说:
“感谢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因为这情况是我这个旅游者非常感兴趣的。”
看来,这一“重要情况”确实对外国旅游者发生了很大作用:只见他用充满恐惧的目光望了望四周的高楼,仿佛在担心每个窗口都会冒出一个无神论者来。
这时,柏辽兹在想:“不对,他不像英国人……”无家汉则皱着眉头想:“这家伙在哪儿学的一口流利的俄语呢?这倒是个问题!”
“那么,请问,”外国客人经过一番紧张思索后又问道,“对那些说明上帝存在的论证该怎么办?我们知道,这类论证有五种[15]之多呢!”
“没办法啊!”柏辽兹似乎深表同情地说,“这类论证全都毫无价值。人类早就把它们送进档案库了。您大概也会同意吧,在理性领域中不可能有任何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
“高论!”外国人叫道,“高论!您完全表达了那个悲天悯人的老头子伊曼努尔[16]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过,叫人啼笑皆非的是,那老头子把五种论证彻底摧毁之后,却自我嘲笑似地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第六种论证!”
“康德的论证也同样没有说服力,”博学多才的主编笑呵呵地反驳说,“席勒[17]的话是不无道理的,他说过,康德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是只能使奴隶们感到满足的。而施特劳斯[18]对这类论证则只是付之一笑。”
柏辽兹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在想:他到底是何许人呢?俄语怎么讲得这么好?
这时,没想到无家汉忽然从旁嘟嘟哝哝地插了一句:
“像康德这种人,宣扬这类论证,就该抓起来,判他三年,送到索洛威茨[19]去!”
“伊万!”柏辽兹感到十分难堪,急忙小声制止他。
但是,听到年轻诗人提议把康德发配到索洛威茨岛去,外国人不但没有表示惊讶,反而高兴得不得了。他那只瞧着柏辽兹的绿色左眼熠熠发光,他高声喊道:
“就该这样!就该这样!让他待在那儿最合适不过!那天早晨一起用餐的时候我就对康德说过嘛,我说,‘您啊,教授,随您怎么看,反正您琢磨出来的那些东西不太合适!也许它合乎理性,但是太难懂了。人们会拿您取笑的。’”
柏辽兹目瞪口呆了,心想:“他在胡诌些什么?‘早晨一起用餐的时候’?……他‘对康德说’?……”
但外国人并没有因为柏辽兹的惊讶而稍显尴尬,他转身对诗人继续说:
“不过,把康德发配去索洛威茨岛恐怕是办不到了,因为他早已经在比索洛威茨更遥远的地方待了一百多年,而且,我敢肯定,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从那里弄出来!”
“真遗憾!”好斗的诗人回答。
“我也觉得遗憾!”来历不明的外国人闪着一只眼睛继续说,“不过,有个问题我还是不明白:如果说没有上帝,那么,请问,人生由谁来主宰,大地上万物的章法由谁来掌管呢?”
“人自己管理呗!”无家汉怒气冲冲地抢着回答,其实,他对这个问题也并不很清楚。
“对不起,”来历不明的外国人用很温和的语调说,“依鄙人之见,为了管理,无论如何总要定出某个时期的确切计划吧?这个时期可以很短,但也总得多少像个样子吧?而人呢,人不但没有可能制定一个短得可笑的时期的,比方说一千年的,计划,人甚至没有可能保证自己本身的明天的事。既然这样,请问,他又怎么能进行管理呢?而且,事实上,”外国佬说到这里又转向柏辽兹说,“譬如您吧,您不妨设想一下:您开始管理了,既管理别人,也支配自己,而且,似乎还很称心如意,可是,突然,嘿嘿!……您得了肺瘤!”外国佬说出“肺瘤”两个字时竟还甜蜜地一笑,仿佛得肺瘤的想法使他很得意。“是的,您得了肺瘤,”他猫似地眯起眼睛,又把这个刺耳的词儿重复了一遍,“于是,您的管理也就到此为止!从此以后,除了您自身的命运之外,您对谁的命运都不会再关心了。亲人们开始哄骗您,您感到不对头,到处去求名医,然后找江湖医生,甚至还可能去算卦问卜。您自己很清楚:名医也罢,巫医也罢,算命先生也罢,统统无济于事。一切最后只能以悲剧告终:曾几何时还自以为在管理着什么的那个人,突然之间便一动不动地躺在木头盒子里了;而他周围的人们,想到这个躺着的人已经毫无用处,便把他放进炉膛里烧掉。有时候甚至比这更糟呢:比方说,一个人刚刚打算去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疗养,”外国人又眯起眼看了看柏辽兹,“看来,这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吧,可就连这件事他也做不到,因为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会一下子滑到有轨电车底下去。难道您能说是他自己支配自己这样去做的吗?要说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在支配他,不是更显得合理些吗?”外国佬说到这里突然笑起来,笑得那么怪里怪气。
柏辽兹极其认真地听完了这番关于肺瘤和有轨电车的令人不快的话,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十分烦闷。他想:“此人绝不是外国人!不是!这家伙太奇怪了……不过,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看样子,您很想抽支烟?”外国人突如其来地转向无家汉问道,“您喜欢抽什么牌子的?”
“怎么,您带着好几种牌子的烟?”诗人板着脸反问道,他身上的烟刚好吸完了。
“您喜欢抽什么牌子的?”外国人又问了一句。
“喏,那就来支‘自家牌’吧。”无家汉气呼呼地回答。
外国人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递给诗人说:
“给您,‘自家牌’的。”
烟盒里装的恰恰是“自家牌”香烟。但是,使主编和诗人大吃一惊的与其说是烟盒里的烟这么凑巧,毋宁说是那烟盒本身。那是一个很大的纯金烟盒,打开时,盒盖上那个由钻石镶成的三角闪烁着蓝光和白光。
对此,两位文学家的反应又各自不同了。柏辽兹想:“不,还是个外国人!”无家汉则想:“嘿,见鬼!够意思!”
诗人和烟盒的主人各自点起一支烟。柏辽兹是不吸烟的,他正暗自盘算着该怎样回答刚才的话:“应该这样反驳他:是的,人皆有一死,对这一点谁也没有异议,但问题在于……”
然而,他这些话还没有出口,外国人却先开腔了:
“是的,人皆有一死。但如果仅此而已,倒也不足挂齿。糟糕的是人的死亡往往过于突如其来,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一般说来,一个人连他今晚将要做什么都没有可能说定。”
柏辽兹心想:“这种提法未免太荒唐……”便反驳说:
“唉,您这未免过甚其辞了吧。我就能够相当确切地说定我今晚要做的事。当然,如果路过铠甲街时有块砖头掉下来砸到我头上,那又自当别论了……”
“砖头嘛,”来历不明的人打断了他的话,一本正经地说,“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掉到任何人头上的。我请您相信,它至少对您绝无威胁。您将是另一种死法。”
“也许您就知道我会怎么死?”柏辽兹的语气理所当然地带着讥讽,他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确实荒唐的谈话。“也许,您还能对我说说?”
“愿效绵薄。”陌生人随口答应,接着便像要给柏辽兹裁衣服似地上下打量起他来,口中还喃喃地念念有词:“一、二……水星居于臣位……月宫隐而不现……六,主灾……黄昏,七……”然后他便高兴地大声宣布说:“您将被人切下脑袋!”
无家汉瞪起眼,气急败坏地盯着放肆无礼的陌生人。柏辽兹却苦笑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人呢?是敌人?外国武装干涉者?”
“都不是,”陌生人回答说,“是一位俄罗斯妇女,共青团员。”
“嗯……”为陌生人的这种玩笑所激怒的柏辽兹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个嘛,请原谅,不大可信。”
“我也得请您原谅,”外国人回答,“不过,事情确实如此呀。对啦,我还想问一下,如果不保密的话,您能告诉我今天晚上您想做什么吗?”
“不保密。我这就回花园街的私宅,然后,晚上十点钟,‘莫文联’有个会议,会议要由我主持。”
“不行了,这些事情都绝对不会发生了。”外国人以坚定的语气说。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外国人眯起眼望着空中,空中正有几只预感到凉爽的夜晚即将来临的黑鸟在他们头上无声地飞来飞去,“因为安奴什卡已经买了葵花子油,不仅买了,而且已经把它洒了。所以,您那个会议是开不成了。”
于是,很自然,椴树荫下的三个人完全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柏辽兹才凝视着胡言乱语的外国人的脸问道:
“对不起,葵花子油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再说,安奴什卡是什么人?”
“葵花子油跟这事的关系嘛,我可以告诉你。”无家汉再也憋不住,从旁插话了。他决心向身旁这位不速之客宣战,便问道:“我说,您这位公民,您从来没有在精神病院里待过吗?”
“伊万!”柏辽兹又赶紧小声制止他。
但外国人不仅毫未介意,反而极其开心地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用一只不笑的眼睛盯着诗人高声说:
“待过,待过,还不止一次呢!我什么地方都待过!可惜我一直没有得空儿去问问教授什么叫做‘精神分裂’。所以,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这个问题您就自己去问他吧!”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父称?”
“得啦,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谁还不认识您!”
外国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昨天的《文学报》。诗人看到:头版上登着自己的照片,下面是自己的诗。但是,昨日曾使诗人感到十分得意的这件光荣与声誉的佐证,此时此地却没有给诗人带来丝毫的愉快,他的脸色暗淡了。
“对不起,”诗人说,“您能稍等一下吗?我要和我的朋友讲两句话。”
“啊,很好!”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大声说,“这椴树荫下多舒适!再说,我也没什么要办的急事。”
诗人把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拉到一旁,悄声说:
“我告诉你,米沙[20],这家伙根本不是什么旅游者,是个特务!准是个逃出国外的白俄,又回到咱国内来啦。你去跟他要证件看看,不然他会溜掉……”
“你这么想?”柏辽兹压低声音问,他也感到有些不安了,心想:“伊万说的也有道理!”
“相信我吧,没错儿!”诗人对着柏辽兹的耳朵说,“这家伙装疯卖傻,就是想从话里套出点什么去。你听他的俄语讲得多好!”诗人边说边用眼角扫着来历不明的人,唯恐他溜掉,“走,咱们去扣住他,别叫他跑了……”
诗人拉着柏辽兹的胳膊朝长椅走去。
陌生人这时并没有坐在长椅上,他站在长椅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深灰皮小本子、一个上等牛皮纸信封和一张名片。见两人走过来,便用锐利的目光直视着他们,郑重地说:
“请二位原谅,刚才我只顾争论,竟忘了向二位作个自我介绍。这是鄙人的名片和护照,还有请我来莫斯科担任顾问的邀请信。”
两位文学家反而窘住了。柏辽兹想,“鬼东西,全让他听见了……”他急忙以很有礼貌的姿势向对方表示没有必要出示证件。当外国人伸着手把证件递给柏辽兹时,诗人瞟见了名片上的一个外文词“教授”和姓氏的头一个字母“B”。柏辽兹只好尴尬地嘟哝说:
“能认识您,我很高兴。”
外国人把证件装进衣袋。这样,双方算是恢复了关系,三个人重新坐到长椅上。
“教授,您是应邀到我们这里来担任顾问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问道。
“是的,担任顾问。”
“您是德国人吧?”无家汉问道。
“我吗?”教授反问了一句,忽然沉思起来。停了一下才说:“是啊,看来是德国人啊……”
“您的俄语讲得可真好。”无家汉说。
“噢,我是个多种语言学家,我懂许多种语言呢。”教授说。
“那您专攻哪一方面?”柏辽兹问。
“我最擅长魔术。”
柏辽兹脑子里轰地一声响,心想:“嘿,瞧这事儿!”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那么……那么,请您来就是搞这一专业的?”
“对,就是搞这一专业。”教授首肯说,接着又解释道,“是这么回事,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批手稿,据说是十世纪一位叫赫伯特·阿夫里拉克斯基的巫师的手迹。请我来进行鉴定。这方面的专家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了。”
“啊!这么说,您是历史学家?”柏辽兹像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毕恭毕敬地问。
“是研究历史的,”教授肯定说,但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补充了一句,“今天傍晚在这牧首湖畔就要发生一段有趣的史话!”
主编和诗人又一次被惊呆了。于是教授示意两人靠近自己。待他们俯过身来时,他低声说:
“请你们记住:耶稣这个人还是存在过的。”
“不瞒您说,教授,”柏辽兹强作笑容说,“您博古通今,我们十分敬佩。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持另一种观点的。”
“什么观点都不需要!”古怪的教授回答说,“这个人存在过,如此而已!”
“但总该有某种证明吧……”柏辽兹还想争辩。
“并不需要任何证明。”教授回答说。接着他便小声念叨起来,而且一点外国口音都没有了:“一切都很简单:他穿着白色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