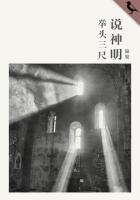楚昭王既死,楚国便即撤军。吴国本无意久战,原只是报陈国过去轻慢之罪,如今取了陈国两邑,陈又不敢兴兵再战,便也班师回朝。夫差伐陈,虽不至全发三军,但也有几百辆战车,上千的兵士,如今渡江归吴,浩浩荡荡的,也行了月余。待到回得吴宫,距出发之时,竟过了半年有多。及至归来,散去诸将,君臣互别,又好是一番功夫,待韩重随友回宫,已是精疲力尽了。
两人才刚刚坐下,就听蹬蹬的脚步声,却见紫玉已跑了进来。韩重霍的起身,向前迈开一步,猛然省起,硬生生将步子收住,却见紫玉已经跑到友的身边。紫玉已是十一岁了,身子渐长,颇露亭亭之姿。韩重细细瞧她,心中想道:“比之年初,倒似略高了一分。”室外日头西斜,余晖倾泻进来,照在紫玉身上,更觉她面若朝霞,整个人都熠熠生光,韩重不由瞧得痴了。但见紫玉靠在友的身边,嗔道:“友哥哥,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话虽对友说,双目却滴溜溜的在韩重身上打转,话音落时,将双眼轻轻一眨。韩重回过神来,脸上现出大大的笑容,踏回一步,重新坐到席上。
友仍是端坐席间,却将手携住紫玉,笑道:“我们前脚才入,你便跟进来啦。”紫玉仍是将嘴微微噘着,道:“你们一去就是好多个月,我闷在宫里,好生无聊啊。”说话间,又向韩重眨了个眼。友便笑道:“地和琼玉都在,怎会无聊?”紫玉将脚一跺,恼道:“你又不是我,怎会晓得。”友又问道:“可去见了父王?”紫玉“哎哟”一声,却笑嘻嘻说:“我、我想见友哥哥嘛。”虽未看着韩重,韩重却心头一跳,心中好生欢喜。友便摇了摇她的手,叹息道:“你呀,怎么这么任性?地和琼玉怕都去了,父王独不见你,不知怎么牵挂呢。还不赶紧过去。见过父王,再来找我,我们怕没时间麽?”紫玉答应一声,却扭捏着不肯走,悄悄瞄向韩重,却见他使了个眼色,便瞪了他一眼。
正蹉跎着,地和琼玉却也来了,一起喊了声“大哥”。地着深紫色的袍子,腰间系着丝带,身长玉立,方面大耳,友才见他,便惊道:“呀,才半年,你竟长高这许多?”放开紫玉,站起身来,走到地的身边,两人比肩而立,都是十五六岁的茁壮少年。友瞧着地笑道:“再两年,恐怕你要超过我了。”地便笑道:“长高些好。日后大哥主政宫中,我便替你上阵杀敌,长高些才有气势。”友摇头笑道:“何必一定要动干戈。”地笑笑不答。友看向琼玉,见她盈盈一笑,便携起她的手,一起走到席间。
琼玉一身青色衣裳,颈间佩着一块碧绿的玉玦,一对剪水双瞳,深不见底。看见紫玉,抿嘴一笑,道:“我们才见过父王,他不见你,可好生挂念呢。我看你还是赶紧过去的好。”紫玉皱皱鼻尖,道:“哥哥姐姐们都在这里,我也不要走了。”友便一手牵了琼玉过来,一手抓住她,一面向外推她,一面说:“好好,让琼玉陪你去。”琼玉便过来牵住紫玉,拉了她出去。韩重看着她二人身影,想道:“大王多时不曾见她,必是想念得紧,如今过去,一时半时,哪得回来?说不得只好晚间再去探她。”
这边地便问友这一路的情况。友道:“此行并无大战。原本陈候请了楚国来救。父王还道要同楚军作战,但楚军战前卜卦,战又不吉,退亦不吉,便一直拖着。后来楚王染疾,竟然不起,待楚王过世,楚军便退了。”地“噢”了一声,心中却想:“下次父王再度出征,怎么可让他带我一起去?”友又续道:“我到陈境,听闻鲁国的孔丘住在陈蔡之间。我久慕此人,曾同父王谈起,想请他入吴,但父王一直不在意。此次我令韩重去访他,谁想他先被楚王请了去,却在路上被陈蔡两国的大夫们遣人困住,一至绝粮,倒是韩重救得他们的性命。”韩重便道:“我到之时,他们已绝粮一日,诸人都是恐慌烦躁,唯有孔夫子,依旧弹琴弦歌,教导弟子,当真让人佩服。”地便笑道:“倘无你恰好赶到,他们岂非要活活饿死?”友便笑道:“幸好我遣了韩重去访他。可惜这次未曾请到,但望日后可请得他入吴。”
友又问地国中诸事。地便道:“那勾践令人送来了葛布十万,玉器无数,还修书说,要从越国选美女宝物,进与父王。”友将眉一皱,道:“这般厚礼,未免太过。”地冷笑道:“我瞧这勾践定不安好心,当初实在不该放他回去。都是那伯噽,成日在父王面前说些什么鸿恩高义德行远播的大话,哄得父王相信。依我说,到底是伍大夫说的是,纵虎归山,后患无穷啊。”友叹口气,道:“但一国君主,总不成一直拘在这里。况且鸿恩高义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地哼了一声,暗道:“这有什么麻烦的。当初夫椒之战,早该灭了越国才是。”但只看着友,并不说出来。
此时天已晚了,有人传饭进来,韩重便同友和地一起吃,一面想到紫玉:“她必是同大王一起用饭了。”饭后才回到自己的居处。也不忙休息,只一直枯坐,等入了夜,实在不能等了,方才悄悄出去,一路摸向紫玉的宫室,心道:“但愿她已从大王那里回来了。”
果见紫玉一个人呆在房中,见他来了,凝眸一笑,却不说话。韩重好容易同她独处,竟说不出话来,好半晌,只是盯住紫玉看,但觉烛光下她的脸也变的朦朦胧胧,恍如梦中,不觉呆了。紫玉嗔道:“才多久,你不识得我了?”韩重这才向前,牵住她一只手,又瞧了她一阵,期期艾艾,不能成句。紫玉“噗嗤”笑道:“友哥哥见了地哥哥,说半年不见,便长高许多。怎么半年不见你,却变得笨呆呆的?”韩重也笑出声来,终于回过神,牵了她一起坐下,积了半年多的话便滔滔不绝的倒出来,描绘这一路的见闻经过,说到孔子绝粮于陈蔡之间的事,更是眉飞色舞。紫玉听得出神,忽轻轻叹口气。韩重与她相处多年,何时见她愁过,慌忙问道:“怎么了?是不是不喜欢听我说故事?”紫玉摇摇头,轻声说道:“只是听你讲这许多故事,好生羡慕呢。可惜我却不能出去。”眉尖轻轻拢起,似叹似愁。韩重不曾见过她这等模样,手足无措,冲口便道:“日后我一定带你四处游玩便是。”紫玉展颜一笑:“当真?”韩重见她笑靥如花,哪里还顾得是否能成,只是一个劲的点头。紫玉便笑道:“那你接着说。”
韩重便道:“我在城父之外,见过一个农家少年,当时他满脸黑泥,好生奇怪。日后我暗自思量,却觉他身形甚似兴夷。”紫玉惊道:“怎会是他?他当日逃走,不该直奔越国吗?怎会在城父?你可告诉友哥哥了?”韩重摇头:“他若怕人追赶,故意绕道,也不奇怪。但我并不确定那人是否是他,所以未在太子面前多事。”紫玉嗯了一声,又道:“还有壬哥哥,不晓得在哪里。”想到子求同壬一起离开,韩重的愁肠也被勾起。室内烛光跳跃,这二人各自想到牵挂之人,一时都无语了。
齐国的都城临淄,热闹繁华,散布了来自各地之人。距宫室不远,有一家店,一进去但觉南腔北调,犹不知这已是齐国之界了。上到第二层,便清静许多。临窗的一面,有三个人盘腿而坐,身边各自摆放了一柄长剑,正低声交谈。只听其中一人说:“先王才死,新君正幼,其他的公子又散布各地,不知几时回来便起灾祸。委实令人担忧。”这正是子求。在他对面的,却是陈睢。
陈睢道:“岂止如此。那国夏、高张二人,依仗先王托孤,如今挟幼主以令群臣,祸起萧墙,只怕就在不日之内。”转向身边那人,“大哥,你常去与他们议政,可探知他二人之意麽?”他那大哥名唤陈乞,闻言只是摇首:“这国、高二氏,长久把持齐国之政,如今新君又只是个孩子,我看国政要皆从他们所出了。”叹口气道:“我屡次同他们说,诸位大夫都愿与他们和睦共处,但他二人就是不信,怕只怕我们容得下他们,他们容不下我们啊。”子求但只沉吟不语,陈睢就道:“看来不如催请公子阳生回来。众位公子当中,就属阳生德行最好,或者可望主持大局。大哥你不是给他写过信,他可有回音?”陈乞便摇头道:“虽有回信,但既未说要回来,亦未说不要。”陈睢便问子求:“你在鲁国见过阳生,可知他是否有意回来?”子求道:“如今齐国局势不明,鲁国执政季孙氏又对他甚是礼遇,他自然不敢贸然回来。依我之见,如今国中已有一君,倒不忙召其他公子,以免再添内乱。”陈睢和陈乞对看一眼,都未答话。
片刻之后,陈乞忽道:“子求啊,你不是带了个名壬的少年一起入齐?”见子求侧脸看他,续道:“恐怕你要多留神。”子求心下一惊,“怎么?”陈乞道:“也不知是否我多心,但国夏曾经问过我此事,我只搪塞而过,却不知他心中是否另有打算。”子求闻言,心中惊疑不定:“壬的身份绝不致暴露,难道是因我而来?只是我与国、夏二氏素无瓜葛,即使无意冲撞,也必是多年前旧事,怎会今日才来?”虽想不出结果,但觉心中惊悸难安,总要见到了壬才能放心,便同陈氏二人告辞,握着剑独自离去。
待他走了,陈睢才问:“那国夏真对子求有所图谋?”陈乞道:“不是他,是他身边的那个少年。”见陈睢不解,续道:“公子阳生的儿子,也是单名一个壬的。”陈睢“啊”了声道:“难道他以为子求带了阳生的儿子来到齐国?”陈乞道:“我看正是如此。虽是误会,但子求既与景公有旧,又是从鲁国入齐,也难怪国夏误会。”陈睢又问:“那大哥为何不向国夏解释清楚?”陈乞道:“他疑心既起,我若解释,岂不连我一起疑了?”陈睢又道:“如此我却要同子求说清,也让他知道如何防备。”陈乞看他一眼,道:“我们何必多事?”陈睢诧道:“大哥的意思是——”陈乞冷冷一哼,“子求武功甚好,人又精明,若肯全力助我,尚是大有用处。可他总是若即若离,我们也用他不上。若是让他对上国夏,对我们自然有莫大的好处。”陈睢“噢”了声,心中却想:“我与子求相交一场,这般利用他,岂不太过?”歉意顿起。
陈乞却不理他,想了一下,又问:“鲍氏那边,你可联络好了?”陈睢笑道:“大哥放心,那鲍牧全听大哥的吩咐。”齐国的大族,国氏、高氏是上卿,一直执有国政,陈氏紧随其后,再下面就要数到鲍氏。陈睢又道:“如今国中诸位大夫皆对国、高二氏不满,亦都已深信这二氏要把持国政,清除异己。形势已全在我们掌握之中。只要大哥布置妥当,随时可以动手。”陈乞到此时方才露出一丝笑容:“国、高二人到此时尚未疑我。如今事事具备,只差一个时机了。”陈睢又道:“莫非大哥在等公子阳生?但他不肯入齐,这却如何是好?”陈乞又是一声冷哼:“阳生性子本来优柔寡断,他不肯来,也在我意料之中。待大事底定,他怕我们召其他公子,自然会来。且等我们掌控局势,迎立阳生,日后自是我们掌政。如今只缺一个口实,可赖以兴兵清除国、高二氏的。”陈睢便连连点头。
他二人坐在二层靠窗的位置,眼下就是临淄闹市,人来人往,看得十分清楚。两人还在交谈间,就见街上过来一队人,中间一驾牛车,前后都簇拥了许多人,个个腰悬长剑,前呼后拥,将整个街道都占满了。陈睢便道:“瞧这些人的架式,当是哪个大族的家臣了?”陈乞道:“为首那人我见过,是国氏家臣。”忽见车上帘幕掀开,露出一张脸孔,年纪轻轻,浓眉宽额,双目炯炯有神。才只一瞬,就被人将帘放下。那人仍被陈睢看了个清楚,惊道:“那车中不是子求的学生麽?”陈乞忙问:“你可看清楚了?”陈睢道:“看清楚了,绝不会错。”陈乞大喜:“不料事情来得如此之快。好,你快去找子求,告诉他我愿同他去找国夏要人。我自去联络鲍氏诸人。看来大事可定,就在这几日了。”陈睢赶紧答应,抓了剑便即起身,未行两步,又被陈乞叫住:“你切莫同他提起你我谋划之事。”陈睢低声道:“我领会得。”抓起剑便自离开。陈乞端坐席上,沉思半晌,忽将酒樽仰起一饮而尽,置之席间,正了正冠,方才起身,将剑佩在腰间,慢慢走了出去。
齐国的宫室,建得甚是巍峨。夏日方炽,宫中枝繁叶茂,花意无限,只是自景公过世,便少礼乐,不然居此宫室,对此美景,再有礼乐相伴,当真是人间天上。自景公的小儿子荼被立为新君后,陈乞便常到此间,与国夏、高张一同议事。这一****仍如往常一般入得齐宫,只是身边多了一人,便是子求。
两人来到荼的宫室,正前方修了齐齐整整的一条道,尽头几级阶梯,直通到宫室里面,他二人却不走正中的道,只从侧面走到宫前,从侧梯上去,把腰间佩剑解下,放在门廊之上。陈乞低声说道:“进此房中必得解剑。等下如有甚变故,你要多加小心。”子求微一颔首,两人便即入内。
房中设有一个矮矮的几凳,几上摊了几册竹简,一个小孩子跪在前面,一身暗红的丝麻,绣着山川黼黻,正在读书。他旁边也跪了一人,十六、七岁模样,面方额宽,不是壬是谁?看到子求进来,立时起身:“先生你来了。”面上喜忧参半。子求也未料到壬会在这里,面色松动,忽一转眼看到房中还有两人,都是一身黑衣,冠下两条长长的带子垂在耳边,陈乞同他二人见礼,便知他们是国夏和高张了。子求也就一同见礼,口中说道:“不知我这弟子,是如何开罪了两位大人?”国夏就哈哈一笑,说道:“这都是误会,我们当他是旁人了。”子求忍住怒气,又道:“既是误会,那我带他离开,也就是了。”一招手,壬便站到了他的身边。国夏却又笑道:“先生之名,我也听过,今日好容易得到亲近,何必如此急着离开?我听说先生在鲁国见过公子阳生,但不知公子可有什么口信要先生带过来的?”子求将眉一皱道:“我只是偶遇公子,不晓得他有什么打算。”携着壬,转身要走。那高张却拦在他身后,冷冷说道:“各个公子皆欺国君年幼,心里不服,你当我们不知麽?你代阳生入齐,哪会无所图谋?”子求怒气暗生,喝道:“你待如何?”
陈乞忽的开口:“国夏大人,高张大人,可否容我一言?”国夏将眉一挑:“你说。”陈乞便道:“自先王过世,诸公子四散而逃,国中大夫人心不稳,两位大人在此之际,如此大张旗鼓的盘问公子阳生的士人,传了出去,只怕人心更乱,委实不宜。”高张轻轻一哼,问道:“依你之见呢?”陈乞慢慢踱了几步,恰恰停在了荼的身边,才道:“若是两位大人交出国政,再召回诸位公子,国中大夫们自然心安了。”子求见陈乞此时发难,便知被他利用,心中暗恼,看看壬,瞧他仍是神色如常,暗道:“他小小年纪,倒比我还能沉得住气。”
高张冷笑道:“好你个陈乞,我早疑你故意接纳我们,心有所图。你便可代表国中诸大夫麽?”陈乞道:“这段时日,常有大夫向我抱怨,我屡次安抚,总是不成。逼不得已出来向两位大人进言。其实先王托孤于你二人,待国中人心安定,两位大人自会得回政事,何必执着于一时?”高张便喝道:“我看最不安定人心的就是你。”将双掌一击,从内室忽的拥出近十个人来,各个手执长剑,逼住陈乞和子求。高张就笑道:“你以为我们真是毫无准备?”一挥手,那些人剑光暴长,冲向前来。子求将壬轻轻一推,推到后面,抄起房中矮几,横于胸前,挡住攻过来的几柄剑。荼便哇的一声大哭出来,陈乞一弯身就将他抱起,微微笑道:“此处太吵,不如我带国君先避一避。”国、高二人不料他有此一招,心下惊惶,同声喝道:“快将大王放下!”持剑诸人,也顿时止住。
陈乞笑道:“你当我也毫无防备麽?”此时便听阵阵呐喊呼喝隐隐传来,似越来越近,国、高二人对望一眼,都是惊疑不定,陈乞就道:“你们在宫中伏下的甲兵,此时怕所剩无几了。”高张大怒,叫道:“陈乞,你敢作乱!”陈乞正色道:“你二人挟幼主以令群臣,我乃是为国除乱。”一低头,看到荼在他怀里双眼瞪得乌圆,面上犹有泪痕,脸色苍白,似害怕已极,便柔声说道:“大王莫怕,我且带你避一避。”一面说,一面慢慢向门边退去。子求同壬,也就一同向后退。房中执剑诸人,皆看着国、高二人。国夏将牙一咬,喝道:“切不可令他们跑了。”众人一拥而上。子求将手中的矮几,挥得虎虎生风,一面抵御,一面冲壬喊道:“你快走。”却有一人已冲到壬的面前,子求被人缠住,不得脱身,心下不由大急,脚下一乱,竟被人划了一剑。
壬从怀中倏的掏出一物,人人但觉寒光骤起,他身前那人眼前一盲,手中长剑胡乱挥出,却觉被一物绊住,叮的一声,剑竟断成两截。定一定神,才发现壬手中一柄短短的匕首,薄如丝绵,寒若流水,不觉呆住。子求看到,心下一喜:“果然是柄宝剑。”原来这正是当日韩重从吴王阖闾的墓中偷出的鱼肠剑,给了紫玉,紫玉又给了壬。
又有几人冲向陈乞,却见他将荼高高举起,荼在他掌中哇哇直叫,陈乞喝道:“你们不要大王的性命了?”那几人看向国夏,见他把手一挥,便向前冲去。陈乞将荼一丢,一下子跑到门外,捡起适才解下的佩剑,却见宫室之外,陈、鲍诸臣,远远的杀过来了,心下顿时一喜。那几人见荼直直飞来,去势顿收,眼见荼就要摔在地上,却听壬大叫一声,直跃过来,刚巧接住了他,却见他双目呆滞,早吓呆了。国夏便叫:“抢回大王。”那几人长剑顿展,壬将鱼肠剑一挥,精光划过,将那几人摄住。国夏又喊:“你们人多,不必怕他。给我将那宝剑一并抢过来。”众人便又压上去,壬将鱼肠剑在空中乱挥,虽然寒光凛凛,摄人心魄,却已完全不能抵抗。
子求见此自是大惊。他此时早抢了一个人的剑,顾不得缠住他的人,横剑一封,将诸人暂且迫退,便硬生生转身,扑在壬的身前,替他将那几人一并挡住。却不料他身后之人如影随形,几柄剑一起招呼到他的背心。子求招已使老,无力回剑,大叫一声,背上已中了几下。壬大骇,喊道:“先生!”把荼往边上推去,将鱼肠剑一挥,却被人在手臂上狠狠一划,手上吃痛,鱼肠剑飞落而下,“叮”的一声,不知被谁的剑斜撞出去,便听噗嗤一声,却见荼躺在地上,哼都未哼一声,身上已流出殷红的血来。那鱼肠剑竟直直的插在他的前胸。变故陡生,众人皆都惊住。忽听呐喊连天,陈氏和鲍氏的家臣们已杀了进来,见国、高诸人四下而散,便即追去。陈睢也在众人之中,此时同陈乞复入此室,见荼躺在血泊之中,大惊道:“国君死了麽?”
壬跪在他身边,伸手探他鼻息,果然已经死了。但见他面白如纸,小小的身子还是温的,心中大是难过,暗道:“他一个小孩子,这些事情一概不知,就这么死了。呀,当年孙将军带我出宫,怕的不就是我也有这么一日麽?”正自难过,陈乞已走上前来,霍的拔出荼身上的剑,从怀中掏出一块丝帕,将剑上血迹拭干,一面细细观看,一面啧啧称奇:“这便是鱼肠剑麽?如此宝物,连刺两位国君,莫非真是命数?”这鱼肠剑乃是当年吴国勇士专诸找巧匠所炼,将它铸的薄薄的,藏在鱼腹,将鱼献给吴王僚的时候,趁机将僚杀了,阖闾方才可以继位。如今荼又死于此剑之下,故陈乞有此一言。壬一跃而起,劈手夺过宝剑。陈乞一惊,却不计较,转头对陈睢道:“马上给公子阳生再送一封信,催他入齐。”却听陈睢叫道:“子求,你没事麽?”壬遽然一省,反转身,子求就倒在身边,赶紧扶住他。
但见子求身上多处剑伤,鲜血正自汩汩冒出,壬颤声叫道:“先生,你且撑一撑,我即刻就请大夫来。”陈睢连忙着人去叫。子求却摇手道:“罢了,我已油尽灯枯,等不得了。”瞧壬的手臂一条长长的剑伤,兀自流着血,说道:“你这手臂,要赶紧包一下。”壬心里一痛,低声道:“我没事的。”陈睢趋身过来,见子求紧盯着自己,心中慚愧,不敢看他。子求便道:“你我也算有二十几年的交情。今日之事,我不怪你,但你要保壬的安全。”陈睢连连点头,含泪道:“你放心。”壬擎着他,滴下泪来,低低说道:“先生,都是我累了你了。”
子求摇了摇头,说道:“我心中只是牵挂重儿。他日你若见到他,可俱告他今日之事,要他且莫步我后尘。”壬连忙答应着。子求便从怀中摸出一块玉佩,递了给壬。壬见那玉佩雕成猛虎的形状,玉质剔透,不觉怔住。子求问道:“你那块呢?”壬便从腰间解下,也是一模一样的虎形玉佩,只是一个头朝左,一个头向右。子求将两块玉佩背对背的合在一起,纹丝和缝,刚好对住,又成一只猛虎。壬陡然明白:“原来先生对我如此之好,竟是为此。”心中顿觉十分难过。子求缓缓说道:“这二十年来,我无一日不在想着她。我当年携重儿入吴,还道若是天可怜见,或者还能让我见她一面,谁想她却早不在了。呀,若能重来,我,我,——”一口血喷出来,话音顿歇,双眼仍直直瞪住前方。壬将那对玉佩握在手中,另一手轻轻抚过子求双目,泪却如雨般,成串的滴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