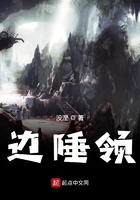栅栏村杨树道上,我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由东向西行驶,那是回家的方向。
我突然感觉眼前一红,脚下的自行车轮胎轧上了一截红地毯,地毯刚刚被雨水冲刷过,毯面一尘不染,还没有完全干,鲜红得耀眼。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村里组织活动铺红毯,而且铺这么远,一定是迎接非常尊贵的客人或者特别隆重的活动。好像父亲刚刚操办过一项大型活动。他们一定认为红毯铺在土路上就等同于报废了,而且又不是全新的,认为没有回收的必要,才铺在地上没人管的。前面还铺着两截,每截约2米宽、10米长,想必断了截的那些都被其他村民各取所需了。
但是通过这次淋雨,表面的污垢尽数清除,地毯的本色露出来了,并没有被人们践踏得致死、致残,铺在院子里当通道最好不过了,从此生活也有了仪式感。我在后座练上了蒙古民族马上取物的功夫,动作是那个动作,但效果比他们神奇多了。父亲在地毯上骑车轧过,我探身用手一抄,就把地毯卷起来,并收在身后。第二截如法炮制,轻轻松松把两捆红毯放在身后座位上(现在想想我的手法不可思议是一方面,自行车后座也是够长的)。
我们的自行车向北拐,路右边有家人正要浇地,在路上挖了一道阳沟,还没有引水。父亲骑车顺着阳沟下去又上来,没有感觉有多颠簸,但上下倾斜的角度稍微大点。过了阳沟,对面碰上王建国、王克杰骑车过来,与我们打了招呼,跨过阳沟向南驶去。快到枣树林时,我觉得后面空荡荡的,伸手摸去,两捆地毯不翼而飞。
“爸爸,地毯没了!”
“什么地毯?”
“刚才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收起来的。”
“那还回去找吗?”
“还是找找吧,那地毯挺好的。”
我骑着父亲的车,飞速地踅回去,目标直指阳沟,我坚信是在那里掉的,别的地方十分平坦,几乎不可能。自行车上的视野非常好,远远地看见阳沟附近除了土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减速,手提前把,脚提后轮,直接飞跃过去。在阳沟上方,我发现它还是很宽的,沟底反射着亮光,可见浇地的人家非常讲究,也非常懂行,底面越光滑密实,渗水越少,水流越通畅。道理谁都懂,但肯下功夫做好的没有几家,这一片都是种园子的好手,能把菜种好是有道行的。我不禁向左瞥一眼正在打畦背的人,穿一身青色大褂、青色裤子,戴着宽边草帽,正在低头忙碌着。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王建国和王克杰,他们已经转到杨树道,走出去很远。与我们错身的时候,我没有注意他们车后驮着什么,但现在远远看去,他们的自行车后架上都有一捆东西,神似我丢的地毯。我虽然还不能确定,但已经脑补了当时的画面。我们过沟时,地毯掉在地上,他们正好看见,但是没告诉我们,蔫不禁的捡起来,然后继续前行。我的车迅速拐上杨树道,在北面道边的草丛里看见一捆绑得牢牢的地毯,显得非常破旧,而且底部被泥土包围着,很明显是有人收拾道路丢弃在路边的,不是我的其中一捆。
终于在杨树道尽头追上了他们,王克杰回头问:“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来找地毯。”我还没有看清他们后面驮的东西,更不能说因为怀疑专门追过来。但很快,我发现他们驮的并不是我要找的。
“地毯啊,刚搞完活动,有的是,你要那个干什么?看,前面就有一堆儿。”王建国刹住车,一只脚支在地上说。
唉,我也知道有的是,可是这些都太破了。我看着建国爷指的那几卷,在万村路东边的草坑里,都快糟透了,比刚才我看见的那一捆还要不入眼。我脑筋飞转,又想到浇地的青衣人,告别王建国和王克杰,掉头往回走。
我又脑补了当时的画面,我过沟时,地毯掉落,青衣人正好看见,也没告诉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蔫不禁地收起来,然后装作没事人一样继续干活,伪装的真好。他现在是最大也是唯一的嫌疑人,即使不显山不露水,再不引人注目,再会隐身之术,也该走入聚光灯,在舞台中央转一圈了。
我在当院转悠,看着娘在克贤院里的菜园子走出,手中拿着几根豆角、两颗芹菜、一个西红柿。这么点儿菜怎么做饭啊,我们现在可都是虎狼般的胃口,菜园子藤叶繁茂、郁郁葱葱,呈现出一派丰收之景,产出却少得可怜。我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必须想办法找点菜,为母亲大人解忧。
我转悠到舅舅家,舅舅刚晒完粮食,正一袋袋往屋里搬。拿人的手短,我总不能见忙不帮而张口要菜,再说也没进屋,还不知道舅舅家到底有没有菜。帮个忙也好说话,正好进屋探虚实,于是舅舅问我有没有事时,我只说没有,上来就帮着搬蛇皮袋子。平时都是舅舅家帮我们干活,我现在的行为很不常见,所以哑巴看我费力地搬袋子,用肩头的毛巾擦擦汗,憨厚地笑起来。
舅舅家屋里太黑了,什么都看不清,进门就是锅台,能感觉到锅台是冷的,灶火堂里没有火。
“我妗子呢?”
“她出去卖货还没回来。”舅舅说。
妗子虽然做饭又脏又不好吃,但绝对是家庭主妇,唯一会下厨的人,妗子回不来,他们连饭都吃不上。还不像我们家,谁都可以做饭,缺了谁也能凑活吃一顿。水瓮旁边,菜板子底下,我没看见一样能吃的东西。算了,还是走吧,时间长了,娘也不会等。
我又想去王传龙家转转,万一能扫两样菜呢,舅舅家与王传龙家隔着两条过道,往西走不到100米就到了。王传龙二叔家后身的东街口,我妗子推着三轮车,后面放着个大笸箩,笸箩上蒙着瘪塌的白布,想是货品快卖完了。笸箩后面跟着她娘(实际生活中已经去世),帮着推三轮车。我很好奇妗子卖的什么,以前从没见过她做买卖,看样子是吃的东西,大饼、馒头类的,那样卖不完也可以回家自己吃,正好家里等着她做饭呢。
我好像问了一句,妗子说的什么也忘了,因为我要急着去王传龙家,也就没有多说。我很倒霉,刚进王传龙家外面就下起了大雨,雨点噼噼啪啪打在窗户和房顶上。
“要是雨不停,晚上就在我家睡吧。”王传龙说。
“是啊,正好跟传龙做个伴。”王传龙的父亲说,然后他走到桌案前,拿起毛笔写起了大字。
王传龙也从卧室绕过屏风,在他父亲右边的桌案前拿起笔,像模像样的写了起来。
我新奇的看着他们家,都知道他父亲是个木匠,心灵手巧,不过这才几天没见,屋里变成这样了。卧室与客厅隔着一道雕花窗格的屏风,客厅风格融合了书房功能,加入古典文房四宝元素,桌案上的笔架垂挂着三四只毛笔。此间氛围已经超脱农村家居格局,书卷气息非常浓厚,让人忍不住地想拿书读、拿笔写。
“你们吃饭了吗?”我问出最关心的话题。
“没有呢,你来的正好,等会儿雨停了,你跟传龙去A家把锅要回来,他一个人还不敢去。”
“你们家的锅怎么在他家?”我没听清王传龙父亲说的是谁,但心里已然凉了半截。
具体原因我也没听太懂,大概是两家有过交易,锅作为抵押品扣在了A家。
雨停了,我和王传龙出门,顺着东街往南走,经过两家人向西转入过道。我在过道口等着,王传龙在北面第二家敲院门,院门是传统的黑色木门,这一块住户我分不清,所以仍然不知道A是谁。
敲门声音响起后,王传龙所在位置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只听到门开狗叫的声音,不一会儿,王传龙就从黑暗中走出,手里提着锅。
“他们家的狗太厉害了,养那么多干什么,三只,差点把我咬死,你看看给我咬的。”王传龙向我展示着胳膊肘和裤腿。
“这到底是谁家?”
“他家你都不认识,这不是木兰家嘛!”
“木兰?”似曾相识的名字,难道是我们小学同学,可是名字上差一个字啊。仔细辨认住家位置,不是她家又是谁呢,别的人也没有“兰”字啊。“她在家吗,你看见她了吗?”
“她没出来,但应该在家。”
应该在家?按时间推算,那个美丽的女孩应该出嫁了,村里的女孩结婚都早,难道是回娘家了?我有点迷糊,想起那个坐在我后桌,写了一手好字,把手指关节咬出茧子的女孩。
回到家,娘还在做饭屋忙活,放气炉子的位置,她面朝墙炒着菜,我站在饭厨旁边水瓮处,没看见锅底着着火。我家的做饭屋熏得越来越黑了,墙面、顶棚、房梁都被厚厚的油烟蒙蔽,几乎看不见本来的泥土、苇席和木头。我哥从里间屋走出来,我们都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我娘不安地说:“是不是煤气管道泄露了?”我们立刻全都觉得,确实是天然气管道泄漏了,于是开始忙乱地查找原因。
后记:我在想,是不是我一贯的想法促成了此梦。我经常和别人说,不要总觉得自家过得不好,其实别人家也好不到哪去,绝大多数人缺钱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只是你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