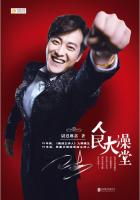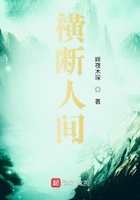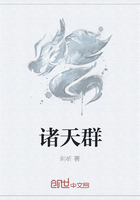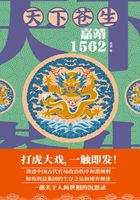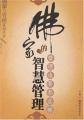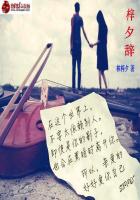第一节 作为地理与文化空间的闽西
“闽”,自古以来就是福建的简称。“闽”的最早记载见于中国上古时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山海经》:“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海内南经》)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闽,东南越,蛇种。”许慎的解释中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闽人是居住于东南的越人中的一支;二是闽人以蛇为图腾。在中原文化的观念中,闽地福建属于边缘少数族群的聚居地。闽地在唐代才得到全面开发,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下。在唐开元前,整个闽地设四州、十七县,即闽州、建州、泉州、漳州和闽县、侯官、长乐、连江、建安、建阳、将乐、沙县、莆田、南安、龙溪、唐兴、长溪、万安、清源、怀恩等,十七县中闽北有六县,其余十一县均分布在由南至北的沿海区域,而整个闽西区域,基本上还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因此清代顾祖禹有言:“福建僻处海隅,褊浅迫隘,用以争雄天下,则甲兵糗粮,不足供也。用以固守一隅,则山川间阻,不足恃也。”(《读史方舆纪要·福建方舆纪要叙》)直至盛唐时期,国力提升,统治者雄心大展,经略天下,僻处海隅的福建才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下,由此才得到全面开发。
闽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获得了独特的地理文化意义。
闽西一般指福建西部和西南部区域,即西南部之永定、上杭、武平、连城、长汀,西部之宁化、清流、明溪、建宁及漳平、永安、三元、将乐、沙县等县西部、西南部区域,人口约400万,土地面积约3万平方千米。很多时候,闽西又指今龙岩市所辖四县二区一市,即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四县和新罗、永定二区及漳平市。地理上,闽西位于武夷山脉的中段和南段,玳瑁山、博平岭、彩眉山等沿东北—西南走向,横贯整个区域,全境地势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格局。武夷山绵延于闽赣边界,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泰宁、建宁属于武夷山脉中段区域,而宁化、长汀、武平则属于南段区域。武夷山是闽江、韩江(在闽西境内为汀江)、赣江水系的分水岭。武夷山中段,闽西北部属闽江水系,著名的河流有沙溪河、金溪等;武夷山南段,闽西中部、南部属韩江水系,著名的河流系汀江;武夷山以西的溪流则汇入赣江水系。武夷山自北而南蜿蜒跌宕,大部分地段属于中山区域,海拔在800米以上;中段建宁的金铙山海拔1858米,系闽西第一高峰,也是闽江发源地。但武夷山脉也有少数隘口跌宕起伏,海拔在800米以下,成为闽赣两省的交通要道。绵延于闽西的玳瑁山、博平岭、彩眉山、松毛岭等山脉,均属于中山区域,海拔大多在800米以上,位于武夷山中段、南段东部、东南部区域,在漳平、连城、上杭、永定、新罗等县区境域。其中玳瑁山是闽西中南部之最大的山体,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49座,其主峰狗子脑峰,海拔1811米;博平岭则蜿蜒于漳平县南部、新罗区东南部、永定东南部,与漳州市华安、南靖、平和县交界,系闽南与闽西之天然分界线。长汀东部、宁化东南部、上杭北部、新罗西部、连城中部以低山和丘陵为主。建宁东部、将乐南部、沙县西部,也以低山为主。整个闽西区域,是一个以中山为主,低山、丘陵错落分布,峡谷交错,溪流纵横,地貌类型多样的山区,向来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
闽西山高谷深,峡谷中溪流蜿蜒,奔腾萦回,是众水之发源地。明嘉靖邵有道编纂之《汀州府志·形胜》中,对此有生动形象的描述:“汀州为郡,崇冈复岭,居山谷斗绝之地,水之所归,南走潮海,西下豫章,东北注于剑浦,西北奔于彭蠡,其源皆出于此,实东南上游之地。是以山重复而险阻,水迅疾而浅涩,山川大势固以奇绝。”
闽西著名的河流有汀江、九龙溪、沙溪、金溪等。
汀江,闽西最大河流,福建四大水系之一,为韩江的上游。发源于宁化治平乡境内木马山北坡,南流纳武平小澜溪,至上杭纳旧县溪,经永定纳黄潭河和永定河,然后进入广东大埔县三河坝与梅江汇合后称韩江。在福建境内干流长285千米,流域总面积9022平方千米。汀江流向从北向南,故按八卦方位,称为“丁水”,后“丁”加水成“汀”,谓之“汀江”。
九龙溪发源于武夷山脉南段的建宁县台田村,经宁化、清流、永安等县,自西北和永安县第二大河流文川溪汇集于城西,形如燕尾,谓之沙溪。九龙溪因中游有著名的九龙十八滩而得名。民间称九龙分别为雾龙、马龙、三门龙、大长龙、五伯龙、贰龙、香龙、小长龙、安龙,民间歌谣有“九龙十八滩,滩滩鬼门关,十船进入九船翻,运气不好难生还”之说。
沙溪河位于福建省中部,系闽江上游的南源支流。其上游九龙溪流经三明市、沙县,到沙溪口与富屯溪汇合,东流到南平市和建溪汇合,称为闽江。沙溪全长328千米,集水面积11793平方千米,占闽江流域总面积的19.33%。
金溪因上游产砂金而得名,属三明市第二大河流,也是闽江上游富屯溪重要的支流之一。其源头有二:一为宁溪,发源于宁化县安远乡武夷山麓;二是澜溪,发源于建宁县客坊乡中畲,自源头至沙洲河段称都溪,沙洲至合水口河段称为澜溪。二溪自合水口汇合后始为金溪。金溪在三明市境内河道长245千米,流域面积约6920平方千米。习惯上将建宁县濉城镇以下金溪河段称为濉溪。
在古代,闽西的航运无力开发,流贯闽西的这些溪河,耸立两岸的崇冈复岭,一直被古人视为“穷山恶水”,闽西之汀江等溪河被称为“恶溪”。柳宗元《愚溪对》中言:“予闻闽有水,生毒雾厉气,中之者,温屯呕泄。藏石走濑,连舻糜解。有鱼焉,锯齿锋尾而兽蹄,是食人,必断而跃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恶溪’。”[94]著名史学家饶宗颐先生认为,柳宗元所称之“恶溪”,“盖指汀江而言”。[95]闽西山险水恶,人烟稀少,故一直是虎豹出没之地。闽西区域普遍崇祀的定光佛,就是一个降虎消灾之神。定光古佛于宋乾德二年(964)来到武平,“睹南岩石壁峭峻,岩冗嵌崆”,遂发誓言,“摄衣趺坐。数夕后,大蟒前蟠,猛虎旁睨,良久,皆俯伏而去”。“淳化间,去岩十里立草庵牧牛,夜常有虎守卫”,后因“牛被虎所中”,定光古佛“削木书偈,厥明,虎毙于路”。[96]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闽西区域的虎患仍不绝。正因如此,古人说潮汀之交有“三恶”:“瘴雾毒,恶一也;滩石险,恶二也;鳄鱼狞,恶三也。潮汀之交,下流滨海,其上则据万山之中,昔时舟行所苦三恶者,盖随处辄有之。”[97]这其实是古代闽西地理状况的真实写照。
在唐中期以前,闽西人烟稀少,加之湿热,多雨多雾,多鸟兽虫蛇,历来被称为“烟瘴”之地。据《太平寰宇记》引《牛肃纪闻》记载:“江东采访使奏于处州南山洞[峒]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杂罗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同书“汀州杂罗故城”条下注曰:“《牛肃纪闻》云:‘开元末,杂罗县令孙奉先昼日坐厅事,有神见庭中,被戈执殳,状甚可畏。奉先见之惊起。神曰:吾杂罗山神也。今从府主求一牛为食,能见祭乎?祭,吾当佑尔。’奉先对曰:‘神既有请,诚不敢违。然格令有文,杀牛事大,请以羊豕代牛,可乎?’神怒曰:‘惜一牛不以祭,我不佑尔,其能宰乎?因灭。于是瘴疠大起,月余不息,奉先病死,其家二十口尽亡。’”[98]这里的描述是否可信,暂且不论,但其暗示了闽西瘴疠盛行的现实。朱熹在《运判宋公墓志铭》中言:“汀州远且多盗,又名瘴乡,常时使者按行,多避不往,至是群盗甫平,死伤横道,疫疠大作,又非常岁之比。公(指宋若水)独慨然引车深入,煮药自随,亲问病者饮之。”就是到了明代,国家仍然将闽西看作瘴疠地区,视同边陲,给予在闽西为官者一定优待。明朝规定,在瘴疠地区为官者,在升迁上有特殊待遇:“凡远方官考满。洪武十六年(1383)奏准两广所属有司官,地有瘴疠者,俱以三年升调,虽系两广而无瘴疠者,仍以九年为满。福建汀、漳二府,湖广郴州,江西龙南、安远二县,地亦接瘴疠,一体三年升调。”[99]也就是说,在闽西等偏远蛮荒之瘴疠地区为官,满三年就可以获得升调,而在其他无瘴疠地区为官,比如就近的泉州,则要九年才考满,才能够获得升调。
山险水急,瘴疠横行,虎豹出没,偏僻闭塞,这几乎是历代官府文献和文人士大夫对于闽西地理环境的认知和想象。受知识、视野、观念的局限,这种狭隘的认知和想象,使历史上的闽西自然成为“内地的边缘”区域。闽西的“内地的边缘”的特征,在上一章中已有论述。这里想进一步阐述的是,“内地的边缘”的事实,很大程度上也是闽西文化上的特征,是闽西文化空间呈现出来的符号形态。
在汉人还没有进入闽西之前,即闽西尚未开发时,闽西被由汉族所代表的核心区域看作纯粹的蛮荒之地,是还没有完全进化为“人”的“山都木客”的居所。关于山都木客,时常见诸文人学士的描述中,在唐宋时期记载得比较多,明清后有所减少。山都木客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郭璞《山海经》注中。《山海经》原文载:“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郭璞注曰:“《周书》曰:‘州靡髴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则上唇掩其面。’《尔雅》云:‘髴髴’。《大传》曰:‘《周书》,成王时州靡国献之。’《海内经》谓之赣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长丈许,脚跟反向,健走被发,好笑。雌者能作汁,洒中人即病,土俗呼为山都。”[100]显然,郭璞描述的髴髴、赣巨人、山都,系指同一物类,具有人的特征,似乎又不全然似人。南北朝时,邓德明作《南康记》,对山都木客有记述,但其原书已经散佚,只能从后人的记述中了解。唐人欧阳询就曾引文言:“邓德明《南康记》曰:‘雩都君山上有玉台,方广数丈,周回尽是白石柱,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瑶眺峨峨,仿像羽人之馆,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舞唱之节。”[101]山都木客生活于高山大谷,雨雾迷蒙,神秘莫测,让人不得其所在。以记载奇闻逸事而闻名的宋人洪迈,在其《夷坚志》中,描述汀州的“山魈”,更是活灵活现:“汀州多山魈。其居郡治者为七姑子,倅厅后有皂荚树,极大,干分为三,正蔽堂屋,亦有物居之。陈吉老为通判,女已嫁矣,与婿皆来。夜半,女在床外睡,觉有撼其几者,颇惧,移身入里间,则如人登焉,席荐皆震动,夫妻连声呼有贼。吉老遽起,与长子录曹者偕往,无所见。’诧曰:‘公廨守卫严,贼安得至?若鬼也,争敢尔?’老兵马吉方宿直,命诣厨温酒。厨与堂接屋,马吉方及门,失声大叫。录曹素有胆气,自篝火视之,吉仆绝于地,涎液纵横,灌以良药,久之始能言,曰‘一黑汉模糊长大,出屋直来压己,不知所以然。’吉老犹不信,录曹见白衣人,长七尺,自厨出,趋堂开门而出,真以为盗,急逐之,而堂门元闭自若也。启之,又见其物开厅门去,复逐之,亦闭如故。洎至厅上,白衣径奏东箱卒伍持更处,一卒即惊魇,众救之,已绝矣。后数年,赵子璋为倅摄郡,时属邑寇作,江西大将程师回自赣上来逐捕,将班师,小休倅厅,出所携二妾与赵饮。正行酒,有小妾长才二尺许,褐衫素裙,缓步且前。程迎击以杖,乃一猫跃出,衣服皆委地。”[102]这则传奇故事,有情节,有场景,有人物,令人惊惧心悸。就是到了明清,关于山都木客的想象,还一直充斥于各种文献札记中。谈迁作《枣林杂俎》,还引明代何乔远《闽书》中的记载,对山都木客的故事津津乐道:“汀州郡治初造,大树千余,其树皆山都所居,有三种,下曰猪都,中曰人都,其高者为鸟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妇自为配偶。猪都皆身如猪,鸟都人首能言,闻其声不见其形。人都或时见形,当伐木时,有术者周元大能禹步为厉术,以左合赤索围木而砍之,树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执而煮之牛镬内。”[103]从千年来的各种文献记述来看,山都木客似乎是一种现实存在。但山都木客究竟是一种从汉族中心主义来看还没有被认知的人群,还是一类当时人还不能分辨的动物,各个朝代的记述描绘都语焉不详。山都木客近乎传奇的故事不断被记述,一方面,显示出闽西——扩大开来看,应该是闽粤赣边区——的偏僻闭塞、鸿蒙未开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原汉族中心主义立场对边缘区域充满偏见和歧视的狭隘的文化想象。学者温春香说:“对唐宋之后而言,山都木客对应的并非实体性的人群,而是人们对赣闽粤交界区早期人群的想象。”[104]无论是朝廷官方还是儒生文士,站在中原立场上来看,闽粤赣边区这个处于内地的边缘的地理空间,在文化上就是一种异类,与中原文化是有区别的。
事实上,盛唐以来,随着国力强盛,人口增多,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作为百越之地的福建渐渐跻身于核心区域。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朝廷偏安江南,福建很快跃升为江浙外最重要的经济核心区和文化核心区,大量人口从不同途径、以不同方式涌入闽西,闽西由此成为当时人口增速最快的区域。历史文献中,关于汀州人口记载总计有六处。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980—989),汀州计有主客户24007户,比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户数2618户增加了817%,这是汀州户数的第一次大增长。到神宗元丰时期(1078—1085),户数增长到81454户,仅百年间增长了239%,为汀州人口的第二次大增长;同期,全国人口增长155%,福建路增长123%,汀州人口的增速均高于全国和福建路的水平。而到南宋隆兴二年(1164),汀州的户数迅速增长到174517户,比元丰时增长了114%。宝祐年间(1253—1258),汀州户口数增长到223433户,人口当在100万以上。[105]如果从大闽西的范围来看,人口可能有近200万。由此可以想象南宋时闽西的繁盛。宋时汀州太守陈轩就曾赋诗赞颂汀州的繁华:“十万人家溪两岸,绿杨烟锁济川桥。”并说此时的汀州“风声习气颇类中州”。从人口户数及汀州的繁华情景可以看出,至南宋时期,汀州已经是一个得到开发的区域了。
当然,我们不否认南宋一朝汀州出现过繁华景象,也不否认汀州人口的急剧增长,但汀州——扩大开来看,应该是整个闽西——作为“内地的边缘”的现实却从未改变过。这是从文化地理上对闽西的整体定位。
从汀州聚集的人群来看,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置汀州时,人口才区区三千余户,且均是检括与逃亡者。“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始立汀州,“管县三:长汀、沙、宁化”。[106]到了宋代,汀州人口迅速增长,由区区万人超过百万规模。但汀州的人口仍然以逃亡避役的迁徙人群为主,人口构成复杂。而这样的区域,一般被统治者看作难于治理的顽梗之地,强梁出没,是盗匪贼寇之渊薮。汀州城虽有“中州气象”,但整个闽西区域则被统治者看作顽梗不化之地。《临汀志》“风俗形势”条云:“汀,山峻水急,习气劲毅而狷介,其君子则安分义励廉隅,耻为浮侠;其小人则质直果毅,不以侈靡崇饰相高……积贮有限,服用无华。外邑山谷之间,亦时有弄兵珥笔为里间挠者,旧志谓险隘荒陋,轻生尚武。”[107]这表明,一是汀州是尚武之地,随时可能发生各种械斗、暴乱;二是各种人群都汇聚于汀州境域,既有遵礼守法的士大夫、君子,也有在种种政策的夹缝中生存游离的刀笔吏,更有动辄就起而反抗斗争、轻生尚武的强梁之徒。一个由移民和各种逃亡者、避役者构成的社会必然会呈现出这种现实。在汀州,让统治者感觉最桀骜不驯的是“汀赣贼”。谢重光先生说:“‘汀赣贼’,顾名思义,就是居住或主要活动于汀赣地区,富于反抗精神,经常起来对抗官府的百姓。”“‘汀赣贼’不是溪峒种类,不是山贼,不是畲民,它本应是‘省民’,但在‘省民’中,它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安分守己,常常铤而走险、群聚剽劫,是‘梗化民’。”[108]整个南宋一朝,汀州境域始终处于动乱中,主要就是由“汀赣贼”的活动所致。宁宗、理宗时期有李元砺黑风峒饥民起事、晏头陀盐寇起事、赣南陈三枪起事等,让统治者莫可奈何。
从社会环境来看,汀州是由溪峒社会演化而来的。溪峒社会长期实行羁縻统治,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松散。多数情况下,人们将实行羁縻制的地方看作化外之地,看作非汉族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闽西一直被看作一个溪峒社会,是畲、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上一章关于客家的污名化中已有阐述)但闽西的这种多族群聚居的环境,某种程度上也形塑了闽西的人文风气,即朴野质拙、强梁好斗、轻生尚武、顽梗难驯。这也是几乎所有内地的边缘区域呈现出来的风气和特征。
从生计方式来看,闽西是一个亚热带气候山地地区,以中山为主,兼有低山和丘陵地带,山高谷深,切割强烈,土地资源奇缺,生存环境相对恶劣。长期以来,畲民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唐宋以后,大量汉人涌入,带来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对闽西的生产发展有较大促进作用。但闽西区域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生产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社会矛盾突出,族群关系紧张。南方社会几乎都是以水稻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但闽西的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使闽西人不能单纯以水稻耕作作为唯一的生计模式,必须依靠多种生产方式才能生存,比如旱地耕作、山林采伐、采矿冶炼、放排航运、贩夫走卒等。混杂的多样化的生计模式,既使闽西人的文化呈现出多样形态,也使闽西人拥有更多的谋生技能,培养出他们隐忍坚毅、刻苦耐劳的性格和品质。这是客家精神品质的核心。学者邹春生在论述赣闽粤边区的儒学实践与客家族群形成的关系时说:“随着唐宋以来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赣江—大庾岭通道的开凿,赣闽粤边区的经济和交通地位日益上升。然而,自唐宋以来,这一地区大量外来族群的迁入,又出现了长期的社会动乱。为了维护赣闽粤边区的社会稳定……中央政府通过军事、政治和文化措施,加强了对这里的控制和管理,实现了直接统治。这些统治措施也推动了儒家文化在赣闽粤边区的广泛传播,对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尽管客家文化体系包含了多元族群文化因子,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汉族文化则是该文化体系的主导文化。这种文化既是国家主导下儒家文化在赣闽粤边区广泛传播的结果,也是我们今天判断客家族群民族属性的最主要依据。”[109]从文化意义上说,闽西既有“野”的一面,即朴野质拙、强梁好斗的个性;也有“文”的一面,即执着隐忍、沉静节气的品质。地理空间的闽西与文化空间的闽西是相统一的。地理环境形塑了闽西的文化个性,而闽西的社会历史发展,又赋予闽西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历史色彩。
第二节 闽西客家:以汀州为中心的考察
闽粤赣边界区域是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区域,而闽西又是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区域之核心,这既是全球客家的普遍共识,也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客家获得自觉的族群意识,主动以客家身份在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表达自身,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家研究表明,客家的称谓不是来源于晋代的给客制度,而是客家超出其传统边界后获得的一种他称。客家作为族群称谓,是由他称转为自称的。在这方面,房学嘉、谢重光、王东、刘丽川、黄志繁等学者都有过深入的研究,且得到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有学者甚至认为客家之名是从传教士的称谓或者海外的称谓中获得的,如梁肇庭、饭岛典子等。这里就不再冗述。
所有关于客家的研究,无论是探讨客家的源流历史,还是分析客家的文化习俗,探究客家文化精神,塑造客家文化形象,都绕不过闽西,都必须以汀州为原点来展开论述。确实,无论是文献典籍中的客家,还是学术研究中的客家;无论是地方精英观念中的客家,还是族谱传说中的客家;无论是方言俚语中的客家,还是仆仆行走于路上的客家,古汀州于它们都具有原点——客家起源的原点、客家学建构的原点,也是客家人观念的原点、客家族群意识的原点——的意义。
客家作为一个族群,起源和形成于古汀州区域。
前面已论述,由于唐以后,中央王朝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福建由偏远之地成为东南核心区域,人口大增,而闽西则是接纳各种迁徙人口最多的区域,真正出现了“地狭人稠”之境况,至南宋末年,闽西境域人口竟超过百万。可以说,这是内陆山区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古汀州有“十万人家溪两岸,绿杨烟锁济川桥”的繁盛景象,自然成为闽粤赣边界区域的核心地区,这为客家人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靳阳春博士认为:“随北宋末期以来汀州经济形势的变化,到元丰时期,汀州社会风气已经在改变之中。南宋,汀州社会形成一种融贯土客的新风气,促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客家文化;这个过程中,汀州各族群在相互斗争、协作中慢慢融合,最终在南宋以汀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拥有独特文化的新族群——客家民系。”[110]客家族群是不是在南宋时期形成,还可以进一步商榷,但在南宋时期,汀州作为闽粤赣边区的中心区域的地位则是不容置疑的。古汀州“地狭人稠”而又环境恶劣、资源贫瘠,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这种压力既导致这一区域一时间盗贼横行、强梁出没,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同时,又迫使更多的迁入人群,为谋求生存发展,再次向更深远偏僻、地广人稀之境寻求落脚安居之所。
古汀州聚居流民向东部和东南部迁徙,有两条路径:一是到闽省域内的漳州府区域,一是出闽省到粤东北区域。
漳州与闽西相邻,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博平岭是闽西与闽南漳州的天然分界线。由于闽西人口增多,闽西东部的博平岭山区不断被开发,渐渐成为人烟稠密之地,永定县就是在此背景下于明成化年间设置的,前一章已经论述。历史上,闽南的开发早于闽西,在客家人还在以古汀州为中心的区域孕育的时期,福佬人作为一个族群已经形成,其分布范围广泛,不但覆盖了整个闽江南部区域,而且延展到粤东,即韩江下游的广阔区域。福佬人主要由泉州人和漳州人融合而成。福建形成福、建、泉、漳、汀五州建制时,泉州户数达50754户,居五州之首,[111]是闽省最繁华富庶之区域。唐宋时代,泉州的海上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接纳了大量的海外商人。由于贸易发达,大量北方汉人涌入,使泉州“越人”“夷种”占多数的人口格局得到根本改变,泉州成为各种人群的汇集之地。本地越人、南来汉人、域外番客等人群长期接触、融合,最终形成闽南特有的方言和习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泉州人。谢重光先生认为,泉州人的形成当在五代时期。[112]在晋江流域得到开发之后,其南的九龙江流域的开发也渐次开始。九龙江流域即漳州的开发,与陈元光密切关联。漳州与闽西一样,在唐以前,主要是所谓“蛮越”人的聚居地。在唐初年,闽南、粤东地区发生了蛮越动乱,陈元光率军平蛮有功,被封为刺史,并世袭其位,掌控漳州,被称为“开漳圣王”。陈元光主政漳州后,漳州区域内的汉、越等人群渐渐融合,其文化互相涵化,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即漳州人。关于陈元光的身世和身份,谢重光等学者有深入研究考证。温春香说:“对陈元光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漳州土著——当地汉人及部分畲民也完成了整体的祖先重构的过程,言必固始的祖先移民传说被一再表述。传说中带领将士南下‘征蛮’的陈元光成为中原衣冠之象征,而与之对抗的则是明代被典范化的畲民雷万兴、蓝奉高。对陈元光身份建构背后的撰写者的意识结构进行研究,无疑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把握华南土著与王朝一体化的进程,因此,考察陈元光建构的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被移民传说正统化了的漳州土著与被平蛮化的畲民,这两个看似相反实则同一的实践背后的文化过程。”[113]陈元光去世之后,对陈元光身份的建构随即开始,这一方面是漳州区域主动纳入国家化进程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也体现这一区域开发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于正统身份的一种渴望,因为这个身份可以将他们与蛮人区别开来。谢重光先生说:“漳州人对陈元光的神化大约始于五代,到北宋中叶朝廷首次给予陈元光应侯的封号,标志着‘漳州人’族群大约在五代到北宋中叶基本形成。”[114]泉、漳相邻,许多漳州人是由泉州迁移过去的,而泉州的经济又整体上较漳州更发达,泉州人的形成又早于漳州人,其语言、习俗、文化等都对漳州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泉、漳融合就是一种自然的文化过程,福佬人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了。谢重光说:“唐五代宋初,漳泉二州曾自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促进了两州经济文化的进步和整合,逐渐形成了本区域独特的方言,独特的有较强商品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色彩的经济形态,重文的士风和重商的民俗也已形成,政治上完成了权利结构的本土化过程,在对中原向心力不断强化的背景下,社会各姓皆祖述光州固始的集体记忆也已逐步形成,因而这个地区的人民已经自成一个独特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后世所说的福佬民系。”[115]
漳泉人不断向南迁移,在粤东聚居,使粤东区域即潮汕地区也渐次福佬化。谢重光认为:“‘福佬’一词的本义是‘貉獠’,最初是客家人对潮汕人和闽南人带有贬义的称呼。用久了,本义逐渐被人淡忘,闽南人和潮汕人也接受了这一称呼,不过排斥了‘貉’‘獠’这种不雅的字义,代之以‘福’‘河’‘佬’‘洛’等文雅之字,而生出种种新解。”[116]
随着福佬人的壮大,泉州、漳州沿海平原丘陵区域也渐渐感受到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压力,长于商贸的福佬人不得不向西部山区扩展,在平和、南靖一线,福佬人越过了尚未开发的博平岭;与此同时,聚居于古汀州区域的流民也迫于生态压力,向东越过博平岭,进入福佬人的区域,形成了福佬人与客家人错居杂处之格局。客家人第一次走出边界,作为独立的族群与另一个族群交汇。也正因这种交汇,客家人获得了自己的族群身份。陈支平说:“宋元以来漳州府内陆山区处于沿海闽南人和闽西客家人的两个民系之间的空间地带,客家人固然可以举族迁居于这些地方,沿海的闽南人也同样举族迁居于此地,这就形成了两个民系由西北和东南两个不同的方向向这些地方的移民。随着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这两个民系的移民扩展终于在某一个地方汇合了。于是,临近于闽西汀州和粤东的漳州府诏安、平和、南靖三县,就必然成为客家人和闽南人杂处的混合区域。明清时期,这些外来不同民系的移民在当地的繁衍发展过程中不断磨合调整,最终形成了现在各自民系的认同。”[117]客家人与福佬人交汇,彼此都超出了传统边界,因此自身身份的确定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彼此发现对方与自己是不同的群体。人类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强调,形成族群的,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不是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如果族群意味着行为上的标志性差异,即持续性的文化差异,那么它作为有意义的单位就可以持续下去”。[118]台湾学者王明珂也说:“一个族群并非完全由文化传播与生物性繁衍而‘生成’,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由人群对内外的互动关系所‘造成’。”“当我们在白纸上画一个圆时,最方便而有效的方法,便是画出一个圆的边缘线条。在这圆圈之内,无论如何涂鸦,都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圆圈的事实。相同的,在族群关系之中,一旦以某种主观标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人们需要强调自身的族群特征。”[119]当客家人与福佬人交汇时,他们都认为对方和自己不一样。显然,福佬人应该是先期到达博平岭区域的,而越过博平岭东部的古汀州人是后到的,从西部更深远的山区中来。而在福佬人的传统观念中,凡是从西部山野中来者,都属于“蛮”种,是被“开漳圣王”陈元光所驱赶的流寇,与来自中原光州固始的福佬人不一样。因此客家人被称作“畲客”或“□”。客家人的身份就此凸显。正如谢重光说:“在明清之际,粤东的福佬人(即讲闽语的方言群)已称与他们错居杂处、大多分布在粤东西北部山区的另一方言群为‘’……”“客家族群移民到粤中、粤西,被广府人称为‘客家’,移民到闽南、潮汕平原及台湾,被福佬人称为‘客’‘客子’‘客仔’‘客民’,都是族群间互相隔膜和互相歧视的产物,两者之间谁先谁后,虽无文字记载可资确证,从族群接触先后的历史事实推测,应是福佬人先有此称,广府人继有此称。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不存在互相影响的问题,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客家与畲族都居住在赣闽粤边界的山区,以其居处之邻接和生产、生活习惯之相似,而被福佬人和广府人误认为同一族群,由畲族的‘畲客’‘山客’之称而将客家族群称为‘客仔’‘客民’‘客家’。”[120]客家在以古汀州为中心的闽西区域孕育形成,而在闽西与福佬人的互动中则获得了的族群身份。
古汀州流民越过博平岭,一部分在闽省区域的平和、南靖、诏安西部与福佬人错居杂处,而更多的古汀州流民则继续向粤东北、粤中迁移。这个时期的粤东北,即梅州区域,大体上还是瘴疠之地,“土旷人稀,地有遗利”[121],自然就成为接纳汀州过剩人口的首选区域。当时,由汀州往粤地的道路有两条:“直北而西,由梅及循,谓之上路;南至潮阳,历惠之海丰,谓之下路。绵亘俱八百余里。上路重冈复岭,峻险难登,林木蓊翳,瘴雾袭人,行者惮焉。下路坦夷,烟岚稀远,行人多喜由之。”处于上路的粤东北区域,正与汀州相邻,地理环境相一致,正适合无地可耕、无山可伐的流民来垦殖。古汀州流民迁入粤东北,主要是顺汀江而下,而以宋元以后的流民为主体。《崇正同人谱系》亦云:“梅州民族,当宋末元初之间曾经一度更擅,而能为今兹繁盛者,殆由元、明以来,始再以汀、赣二州之源源而至,是则此为‘后客’。”[122]南宋祝穆谈论梅州:“土旷民惰,业农者鲜,悉借汀赣侨寓者耕焉。”[123]清代《嘉应州志》云:“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召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众。至兵败,所遗余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宁化石壁乡人。”[124]元明时,赣南区域由于赋役、疾病、战乱,人口急剧减少,出现“土旷人稀,地有遗利”之现象,于是,大量由赣迁闽之流民,又大量回迁赣南。邹春生博士说:“在宋元以前的赣闽粤边区内部人口流动中,赣南因为地处赣江—大庾岭通道这条南北交通线上,能够吸引大量北方战乱移民,所以往往成为向闽西和粤东北输送人口的区域。而到元明时期,因为中国获得空前大统一,北方几乎未再出现长期的战乱,所以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南迁高潮就再也没有出现,赣南地区原有的重要人口补给源断绝了。而根据学者的研究,赣南从元代以至明初,由于战争和鼠疫,人口一直在下降。到了明朝中后期以后,由于军屯弊病丛生,以及赣南赋役太重,又导致大量人口逃亡。清初受‘三藩之乱’,赣南的人口也受到较大损失。”[125]由此,大量在汀州无法生存之流民,又不断向赣南区域回迁。闽粤赣区域间人口互相流动迁移的现象,促进这一区域的人群间形成共性的文化因素,如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祖先认同,这是客家在这一区域孕育形成的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形成,显然是以闽西为原点发散开的。闽西和古汀州的意义当不言而喻。
其实,香港崇正总会成立后,于1924年修订并正式出版《崇正同人系谱》,在论述到客家的源流和客家人的不同层次时,特别强调了以汀州为中心的客家核心区域的重要意义。“赣、汀、韶、连各州之吾系民族,乃当日中原南来初经一次为客之民族也,而未再转徙且已成今日最先之土著矣,然实则客家中之主也;今日梅、循二州与珠江、西江上游及福建、潮、琼同系各族,乃皆当日度岭逾南再经二次为客之民族也,而不复转徙则亦成为土著矣,然实仍客中之客也;今日增城、东莞、番禺、新安、龙门、从化、清远以及一概插处之客族,乃又近代生齿日繁、人稠地逼,因图发展,更经三次、四次为客之民族也,而转徙不已,又若成为频动之客族矣,是则客中之客而愈客也。”[126]这一段文字表明,赣、汀、韶、连是客家聚居的核心区,中原南来的各种人群在这里聚居,遂成为客家人,许多人由此世代聚居,其身份早不再是客,而成为土著,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这一批人群构成了最初的客家人,是“客中之主”。聚居于赣、汀等地的客家,为图生存发展,部分人在短暂聚居后又再度度岭而南,辗转于梅州、循州区域,以及福建西南部、粤省潮汕区域和琼州区域。这是最早走出客家传统聚居区域的客家人,其翻越之岭即博平岭、大庾岭、南岭,是最早与福佬人、广府人交汇错处的客家人,他们的迁移,使客家的语言、文化、习俗等获得了向外呈现的机遇,划出了客家新的族群边界。这批人群在明清时期已聚居于客家边界区域,也已然成为土著居民,是二次迁徙而为客之客家,因此,可算作“客中之客”。至于此后再向粤东、粤中、粤南、粤西扩展的客家以及再后向其他区域——粤省之外乃至海外——迁移的客家,则其已然经历多次频繁迁移,为“频动之客族”,系“客中之客而愈客”之客家人。显然,客家是以古汀州为原点逐渐扩散发展开去的。
早在19世纪,为建构客家观念而发表宣言的徐旭曾在其《丰湖杂记》中就清晰阐述了客家的源流历史:
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耆调解,始息。院内诸生询余何谓土与客?答以客者对土而言,寄居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
余口述,博罗韩生以笔记之。(嘉庆乙亥五月廿日)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而烟瘴潮湿,又多生疾病,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隔阂,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
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闽、赣、湘、粤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义之后,其孰能之?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古人“负耒横经”之教也。客人多精技击,传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月农暇,相率练习拳脚、刀剑、矛梃之术。即古人“农隙讲武”之意也。客人妇女,其先亦缠足者。自经国变,艰苦备尝,始知缠足之害,厥后,生女不论贫富,皆以缠足为戒。自幼至长,教以立身持家之道。其于归夫家,凡耕种、樵牧、井臼、炊衅、纺织、缝纫之事,皆一身而兼之;事翁姑,教儿女,经理家政,井井有条,其聪明才力,真胜于男子矣,夫岂他处之妇女所可及哉!又客人之妇女,未有为娼妓者,虽曰礼教自持,亦由其勤俭足以自立也。
要之,客人之风俗俭勤朴厚,故其人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余昔在户部供职,奉派视察河工,稽查漕运鹾务,屡至汴、济、淮、徐各地,见其乡村市集间,冠婚丧祭,年节往来之习俗,多有与客人相同者,益信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说,为不诬也。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风俗语言,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
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因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
嘉应宋芷湾检讨,曲江周慎轩学博,尝为余书:嘉应、汀州、韶州之客人,尚有自东晋后迁来者,但为数不多也。[127]
《丰湖杂记》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构建了客家来自中原,系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的形象,强调客家是中华精神的继承者和守护者,凝聚了中华文化的优良品质。同时,《丰湖杂记》还透露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是被称为客家的人群主要聚居于闽粤赣湘边区,尤其是闽粤赣边区。二是被称为客家的人群是在宋元时代,主要是南宋时期为避元兵追杀而在闽粤赣边区聚居落脚的。三是被称为客家的人群迁居至闽粤赣边区时,这一片区域基本上还是荒旷之地,人烟稀少。四是客家之被称为“客”,是相对于“土著”的当地人而言,“客人”在中国东南区域聚居要晚于当地“土人”,即福佬人、广府人,所以当地人才称之为“客”,久而久之,客家也自称为“客”,这与晋代的给客制度无关。五是在明清时期,在土客交错杂处区域,土客之间为争夺资源曾经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六是被称为客的人群,其语言、习俗、生活方式等,与中原的汴、济、淮、徐等地类似,而与当地土人有很大的区别,土客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界线和族群界线。
剔除徐旭曾文化正统论之观念,客观地看,客家作为一个族群形成自觉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应该是在明清时期,即客家人走出其传统区域,与福佬人、广府人发生广泛的接触,在谋求生存发展而展开的资源竞争中,客家人的族群边界明晰起来。而客家人之文化精神和思想品格,则是在以古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区孕育、积淀、凝聚的。以古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区是客家文化和精神的渊薮,是客家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原点。
第三节 族谱中的客家:石壁文化符号的建构
客家作为族群被其他族群承认并获得族群称谓,是在客家人走出传统聚居区域,因为资源竞争与其他族群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客家称谓是由他称转而自称的。置身于族群边界的客家人,即与福佬人、广府人交汇错处的客家人,更注重维护和强调自己的客家身份,有自觉的族群意识,其他族群也更多地将之看作相异群体。但在以古汀州为中心的客家聚居区域,人们普遍没有那么强烈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甚至关于客家的观念也较为淡薄。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客家称谓和客家观念已经通过走出族群边界以及流落海外的客家人,在客家核心聚居区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地客家人开始接受客家的称谓,主动以客家人自称。19世纪末期,客家精英温仲和在编撰《嘉应州志》时,对客家的习俗、礼仪及方言有较详实充分的论述,这是来自准官方的、第一次对客家的具有正面意义的论述和介绍。这说明客家的自觉的族群意识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并获得官方的认可。梁肇庭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岭南地区出现的客家人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并非是在所有客家地区都同时出现的现象。‘客家’这一标签出现于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不同地区的客家人对其作为族群性的需求是截然不同的。”[128]对整个客家聚居区域的考察也是如此,整个赣南区域就一直没有形成共同的客家族群意识。其族群意识的获得,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现代客家运动发生之后,后面的章节将详述。在客家形成和发展的16—19世纪,将闽粤赣边区的客家人凝聚在一起的,其实主要不是“客家”这个族群身份,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宗族组织,是以宗族为单元编撰修订的族谱。可以说,客家人通过族谱,通过族谱中所记载的祖先来源、宗支流脉、世代沿袭、迁徙路径来获得认同感。族谱在客家精神的凝结、客家归属感的形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所有关于客家的研究,都绕不过客家族谱。
人类文明进程的大致趋势,是社会组织关系的主体由血缘向地缘转变。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源于父系家长制的亲族血缘联系的宗法制度却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定势。宗法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实行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建立严格的家族制度,家国同构,国家就是一个放大的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人必须属于一个家庭,而一个家庭又必须属于一个家族,而每个家族又必然认同一个共同的宗祖。宗,《说文解字》说“尊祖庙也”,《白虎通义》说“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宗有根本、主旨之意。家族宗奉之宗,显然就是早先那个居于尊长地位的“父”,是那个最初的氏族长老。《白虎通义·宗族篇》曰:“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在一个宗族中,最重要的是血缘,是血缘将人们汇聚在一起,是血缘赋予人们身份感、认同感,归宿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神不祀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由一个男性先祖的子孙团聚而成的家族构成的文化集团,是中国传统社会机体生生不息的细胞,由遥远的商周时代一直绵延到近现代。
宗族组织在商代就已存在,但在唐以前,宗族组织一直被看作豪门贵族的一种特权,普通民众是不能附会于宗族的,甚至不能祭祀。在宋以前,祭祀一直被当作一种特权,只有君王贵族才能进行和参与。宋以前,祭祀祖先有严格的限制,天子祭祀祖先百世不祧,诸侯五世而祧,大夫祭曾、祖、父三世,士只能祭父亲一世,而庶人无庙制,当然不能超过父亲一世。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祭祀法则和宗族组织,社会层次越低,祭祀祖先的权利越小。由于祭祀上的限制,宋以前,中国民间的宗族组织一直得不到发展。在宋代,理学家张载开始提出重建宗族制度的主张。他认为宗法不立,祭祀制度亦无从立,主张庶人“亦祭及三代”;士大夫有大事,可以祫祭其高祖,即四代祖先。到朱熹,则进一步完善了这种祭祀制度。他的《家礼》提出了建立宗族祠堂和祭祀的具体设想,为重建民间宗族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民间宗族和普通民众可以立祠堂、建家庙、置墓田,地方宗族组织在福建迅速发展,成为地方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建构地方社会秩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形成的这种具有民间基础的宗族制度,至明清时进一步发展。明代中叶,允许臣民祭祀始祖,“庶民户皆有权置祠庙,在一村镇中几乎所有农民都被纳入一个族姓的宗祠或家庙,由祠庙所联系的大众大为增加”[129]。清承明制,实行相同的宗族政策,准许民间建设祠堂,追祀远代先祖,一时间,形成了“族皆有祠”的气象。嘉道时期关注世道的文士张海珊说:“今者强宗大族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或者万余家,少亦数百家。”[130]而哪里有聚族而居,哪里就一定有祠堂,“聚族而居,族必有祠”[131]。宗族组织具有广泛的乡村基础,是明清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宗族组织的发达,作为宗族重要象征符号的族谱的修撰编写就成为中国乡村社会几百年来一直沿袭且长盛兴旺的文化现象。
福建民间族谱修纂兴起于宋代,但主要限于显宗贵族。宋以后,由于元代社会的动乱及对汉人的歧视和限制,福建民间族谱修纂处于低谷期。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主张恢复儒学礼仪传统,族谱修纂活动渐次发扬,尤其是进入16世纪,帝国经济进入上行期,福建民间族谱修纂活动也随之兴盛,普通宗族纷纷修纂族谱,形成一股热潮。陈支平说:“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修谱活动出现了普遍化的趋向,许多福建家族都是在这一时期首次修纂族谱。如上杭县中都何氏家族,第一次修纂族谱是明代嘉靖三十三年(1554)。”[132]但随后明末的社会动乱又使刚刚兴起的族谱修纂活动陷于停滞。明末清初,福建一直是南明政权反清的重要基地,加上经营台湾的郑氏父子不断骚扰,倭寇袭击抢掠,福建社会的动荡一直持续了数十年。直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统一台湾,解除海禁后,福建的经济才得以恢复和发展。进入康乾盛世,福建民间又兴大规模的族谱修纂活动。其表现出几个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家族都投入到族谱的修纂中,这个时期,只要达到一定人数的家族,都会以举族之力,通过各种方式修纂族谱;二是原来已修谱的家族,普遍开始重修族谱,在体例、规模、印刷等方面,都相比前代更完善;三是统谱和联谱的兴起和流行,即将同一姓氏的不同族谱统一编修,或者同一姓氏但不同宗支的家族联合在一起修纂族谱。此次修谱热潮,一直持续到晚清。
聚居于闽粤赣边区,以古汀州为中心的客家人,在遍及华南的修谱热潮中,是最热衷修谱活动的族群。考证今天留存下来的客家族谱,大部分修纂于清代中晚期。这个时期,无论是聚居于闽粤赣边区的客家人,还是由闽粤赣边区迁徙出去的客家人,都把立祠堂、修族谱作为联宗收族的重要文化策略,祠堂和族谱成为家族的最重要的符号和徽章,也是凝聚人们文化认同、明确族群身份的最重要的方式。如连城培田村,是闽西区域最有影响的客家村落,是客家吴氏聚居地。据传,吴氏族谱最早编修于明万历年间,但已不存于世。现留存于世的吴氏族谱有三种版本:乾隆戊申(1788)本,共10册;同治甲戌(1874)本,共8册;光绪丙午(1906)本,共14册。这是一套传承有序的宗族族谱,收录了历代族人的世系、行述、像赞、祭文、志铭、诔、颂、传、诰命、诗词等个人生活史资料,以及历次修谱的序、例、图、记、家训、家法、族规、纪略、源流等家族史资料,乃至于族内各支流派和各社团的合议字、分关引、尝田录等,内容十分丰富。吴姓始祖为“八四郎公”,系元末由于战乱而由浙江迁徙至宁化,再由宁化来到长汀宜河里。在培田附近的上篱村看到水口龟蛇交合,认为是发人的风水宝地,就向地主魏氏租地建屋,并娶魏氏女为妻定居下来,由此开族,号为“吴家坊”。我们分析吴氏族谱所记载的迁徙、开族、定居故事,发现这个模式,其实是南方所有移民传说的共同故事模式。客家区域各姓氏族谱中所记载的迁徙、开族、定居故事,总体上都与吴氏族谱所叙述的模式相一致。在客家族谱中,其祖先基本上都来自中原或者江浙一带,早期先祖都有显赫的为官经历或者曾经立下赫赫战功,为避战乱在宋元时代开始迁徙,先至宁化——多半是宁化石壁——然后再由宁化迁徙至其他区域,最后在现在所居之地定居。最早迁徙到宁化石壁的祖先普遍被看作始迁祖。
《李氏族谱》载:南来之祖,始于唐末,有宗室李孟,因避黄巢之乱,由长安迁徙汴梁,继入宁化石壁。李孟之孙火德,由石壁迁上杭胜运里之丰朗乡,由此奉为李氏南迁入闽一世祖。
《张氏族谱》载:始迁祖显卿公,于明洪武初由宁化迁居上杭,生二子,长子文贵,迁居漳州;次子德生于洪武十四年,迁到古坊村。德生为古坊开基祖。
《梅州刘氏族谱》载:闽粤刘氏后裔,均以祥公为始迁之祖。刘祥于唐乾符年间迁宁化石壁,为天下刘氏入闽开基始祖。
《巫氏族谱》载:巫氏入闽始祖,一世罗俊。入粤各地世系,英德高坎世系,一世仕聪,宁化十四世大一郎长子。惠州一世仕政,大一郎三子;潮州一世仕宗,大一郎四子;丰顺汤坑一世仕敬,大一郎六子。
《罗氏族谱》载:罗氏于晋永嘉年间始入赣南,唐僖宗时迁宁都,不久入宁化石壁乡。五代后分迁各地,支派甚众。闽系罗氏,皆出汀州宁化石壁。
《温氏族谱》载:四十三世,南宋由石城迁福建宁化石壁乡。子三,次子瑾,讳同保,其裔孙分布闽、粤、赣各地,故闽、粤、赣之温氏均奉同保为大始祖。
《谢氏族谱》载:开书,宋末元初,由浙江始宁迁宁化石壁村,传二世孙逢春,迁居大埔,其子朴六任梅州尉令,迁居梅县。后衍平选、惠州、蕉岭、潮州、河源、兴宁、五华及江西。
……
闽西的地方文史学者说,客家主要姓氏中,同宁化石壁有渊源关系的达210个姓氏以上。其中,有98姓都在全国人口最多的前100种姓氏之中。客家姓氏人口应同汉族总体姓氏人口类似,所以,可以估算,同宁化石壁有渊源关系的100姓中的98姓,另外再加上100姓以外的其他100多姓的人口,有充分理由认为,同宁化及石壁有渊源关系的姓氏人口占客家总人口的80%以上。[133]按照地方学者的推算,可以想象,由宁化及石壁迁徙出去的,将是多么庞大的人群;也可以想象,客家的人数将是怎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从这个意义上说,祖先来自中原,普遍定居落籍于宁化石壁,再由石壁播迁其他客家区域,显然是一个故事传说,一个自我创造的关于祖先历史的神话,是客家人在选择与遗忘中共同确定的历史记忆。
在客家族谱中,宁化石壁是一个重要存在,是南迁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20世纪初,客家学先驱罗香林先生研究客家源流,主要依赖于客家族谱中的史料,把古汀州尤其是宁化石壁作为判定客家的一个标尺,凡是由北南迁,在古汀州尤其是宁化石壁聚居,有过短暂停留,再由宁化石壁播迁客家其他地区的,就是客家人,反之则不是客家人。
关于宁化石壁现象,在近代文化中,也有几个极其类似的例子,如广东南雄的珠玑巷、山西洪洞的大槐树、河南光州的固始、湖北孝感的麻城等。对于这种普遍存在的祖先来自一个共同地方的文化叙事,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多不支持,认为那仅是为了促进族群认同,凝聚族群力量,提升族群身份,彰显族群优势,扩大族群影响力的一种文化策略。陈支平认为,族谱修纂中这种虚假冒托成分的造祖风气,“既是家族发展的一种现实需求,又是与敬宗收族、慎终追远、标榜血缘纯洁性的修谱原则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134]谢重光在论述石壁现象时说:“由于中华文化传统中中原正统论的作用,自然以来自中原者之身份、血统为贵。在这样的身份、血统论证中,很可能最先一批经由宁化石壁而演变成客家人的中原移民成为身份高贵的楷模。其后,未经宁化石壁而由赣入闽再迁往各地演化为客家人者,一方面由于记忆模糊,一方面由于自高身份的需要,也把本族入闽的途径说成是经由宁化石壁。久而久之,造成了不经宁化石壁者就不是来自中原的思维定势,并形成一股巨大的舆论压力,于是各种来源的客家人纷纷认同这一传说,声称本宗本族也是经由宁化石壁而散播各地的。”[135]客家人强调本族来自宁化石壁这种人为制造畛域的修谱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自己纯正的中原血统,另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与其他一直遭受污名的未开化族群区别开来。中山大学学者刘志伟说:“宗族的建立是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建设的结果。现代人读族谱资料,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把迁移和定居的祖先作为宗族历史的开创,其实宗族的历史是由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华南区域,“在明代以前,我们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宗族’的存在。宋元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其实还处在开发初期的状态,这一地区的乡村社会,大致上仍处在一个‘传说’时代”。[136]因此,在族谱中,无论是关于南雄珠玑巷,还是关于宁化石壁村的祖先叙述,都不是历史的记述,而是一种有意识建构起来的集体记忆,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联,与建立人们共同的宗族认同、凝聚宗族力量相关联。这种关于祖先源流来历的传说故事,实际上是关于户籍来历的故事,直接关联的是明代以来一直存在的移民入户籍问题。这对移民而言是非常迫切而现实的,祖先的故事显然为无籍的移民提供了入籍的理由,具有相当的现实功利性。同时,这种故事传说,是广大移民获得正当身份的重要途径,是纳入国家化进程的方式,也是宗族表达存在的一种方式,还是宗族在地方建构社会身份,建立和寻求话语权的一种方式,是乡村社会祖先进行自治和自觉建构地方秩序的重要方式。香港学者科大卫说:“本地人口建构出一批文化符号,显示自己是实践王朝所认可的正当礼仪的、安土重迁的;这样,才有客家人迁移的历史可言。这同样一批文化符号,既然被用来奠定本地人的‘本地人’身份,当然也会被用来把移民定义成‘外地人’。到了19世纪初,当客家人亦利用起本地人利用过的意识形态礼仪,并且利用‘来自中原’的神话为自己建造其道德优越地位时,客家人不仅把自己和本地人分开,也把自己和輋[畲]人分开……”[137]宁化石壁已然成为客家人的最重要的祖源地。但宁化石壁作为客家的祖源地,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并不是真有那么多族姓的客家人的祖先都在宁化石壁生活居住,仅是显示他们对宗族渊源的认同,对族群的共同历史的认同,是客家人自觉建构起来的历史记忆。文化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说,一个共同体,内部成员坚信他们共享的历史、文化或族源,这种共享的载体并非历史本身,而是他们拥有共同的记忆。这个共同体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族群。[138]将实在的、可以感知到的祖先与一个具体的地名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其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族群共同体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或者建构起来。“客家人认同于石壁的祖籍符号,其实就是对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的共享,而这种共享,就赋予了以石壁为祖源地的共同体一个共同的文化身份——客家人。”[139]除在客家族谱中建构起石壁这个象征性符号外,客家人在向闽粤赣边区之外播迁的过程中,也建构起其他符号,比如瓦子街(有说瓦子坪、瓦子巷等),只是,比起石壁村来,它们的影响力远远不够。石壁村与大槐树、珠玑巷、固始、麻城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移民确定身份的最著名的文化符号,是移民的共同的文化认同,是中国人关于故乡、关于乡愁的重要象征。关于石壁符号的现代建构,后面的章节会进一步阐述。
通过对客家族谱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闽粤赣边区,尤其是在以古汀州为中心的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区域,客家人的族群意识,客家人的身份建构,主要不是通过族群边界的划分来获得,而是通过建构共同的历史记忆来获得的。而这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就是客家人在族谱中有意识地建构的:祖先来自中原,并且在不同时期迁居到宁化石壁,再由宁化石壁播迁到其他地区。正是以汀州为中心区域,以宁化石壁(含瓦子街、汀州等)为中原入闽始祖始迁地,再由此播迁到其他区域,这种共同的历史认同和祖先认同,使闽粤赣边区在明清时期大体完成其客家化进程。在这个时期,闽粤赣边区已然建立起一个在观念上以中原文化为正宗和以来自中原为正统的客家社会。但作为族群的客家自我意识的获得,还是在走出客家生活的传统区域,在资源竞争中与福佬人、广府人发生普遍交集以后的事。那些处在族群边界上的群体,更深切地感受到其身份归属、历史记忆、文化渊源、祖先来历、语言习俗等与汀州及石壁的紧密联系。如果说汀州和石壁是核心、圆心,那么,只有处于这个巨大的族群圆圈边上的人群,才会深刻意识到他们与核心是一致的,是以这个圆心为核心的巨大圆圈的一部分,汀州和石壁是凝聚他们身份归属和文化信仰的真正的圆心。有了圆心,才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而有了圆圈,才会有大家共处于一个巨大圆圈内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宁化石壁,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化成一个有意味的文化符号,一种关于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象征性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具有和认同这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的,就是客家人,反之,则不是客家人。石壁的传说故事,有意无意地成为客家人构建族群身份的一种文化叙事策略,也成为客家人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客家人是一种文化的建构,是有文化人类学的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