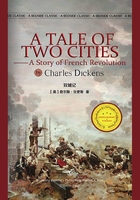我走进亚当的房间,桌上有一堆纸和书,还有几个空的咖啡杯,他刚参加完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
“怎么样,亚当?”
他耸了耸肩:“太难了,我只能说我写完了。”
“反正你也不想去,如果你去爱丁堡会更快乐的。”
他看上去对自己很不满意,我应该更关心他的。
亚当被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录取了,攻读化学专业,正如妈妈和爸爸所期望的那样。他还是那样看上去满不在乎,对自己的成就表现得谦逊又低调。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朝着什么方向继续走下去。
在升学前,他决定用一年的时间旅游,先去了法国,之后又去了印度。在他去旅游的这段时间里,我异常想念他。我在学校里准备着大学入学考试,只有我和爸爸两个人在家。母亲节是最难熬的,尤其是亚当不在的这个母亲节。我觉得空虚又孤独,多么希望他能在身边。那天他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尔,刚刚读完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还在他的日记本里摘录了书中的选段。
母亲节,1988年
对我来说……
他们不屑跟一个外人建立一段感情和寻常的友谊,总是不断追求一些深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一般人似乎又浅薄又平凡,并且微不足道。因此他们在最简单的社交方面也很不习惯,显得格格不入。简直活受罪,然而又自认高人一等,傲慢不逊。他们在心里倒也渴望精神上的亲密,可这种亲密他们又没办法得到。因为他们太麻木不仁,对待别人一概愚蠢地表示蔑视,所以把每一条密切交往的门路都堵死了。他们要的是真正的亲密,可是他们连一个人都没好好接近过,因为他们不屑走出第一步,他们看不起与人们建立普通交情的琐碎小事。
和我一样,亚当也渴望能在母亲节有亲密感,能与别人有联系,渴望着拥有更深层的东西。于是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想从书中找到能表达他内心难以描述的渴望:
天哪,多么希望我是这些故事中的人啊。不难理解,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他们的现实会更真实吗?我们是否只是他们的非戏剧化版?只是无法像他们那样表达我们的情感而已。
亚当在书中找到了一丝能将自己的现实与之相联系的微弱的情感,书能宣泄出他无法向这个世界表达的情感。我找不到归属感,哥哥也一样。他唾弃自己无法与周围的人和事产生共鸣。但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共鸣。
他从法国回来后,在家待了几个月,为了存钱去印度。这是我最快乐的几个月,因为有哥哥在身边。他会带着他的妹妹去酒吧,几乎每天都要跟她解释什么是电极电位。7月,他和他最好的朋友丹尼以及他的日记本去了印度。
我好想他,没有他的房子感觉空荡荡的,但他会给我寄一些满载着他奇特幽默感的信,称呼我为“大妹妹”。
我亲爱的,最爱的妹妹:
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信给你,我发现我这辈子从未收到过你的回信,对不对,小懒虫?等等……在我记忆的某处有个“嗨,好好玩,爱你的塔拉”。嗯……没错,我想这个可以等同于回信了,写得非常好!天啊,希望希腊不会让人难以忍受,也不会有任何有违常理的事发生,比如酒啊,毒品啊,和男人共度良宵啊之类的。但文化体验我倒是非常喜欢,因为它是这次旅行的目的。说到这点就不得不提到提吉节了。嗯……你知道9月16日,一个平凡的日子,也是一个好日子……是我的生日(我觉得你不会忘记的)。鉴于那天我正搭乘着一辆非常“有味道”的印度火车去德里,所以我觉得18号回家的时候,应该会有一桌丰盛的晚餐或者是类似的东西在等着我。是不是很美妙,塔拉?对,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主意的。可恶,信纸要用完了,到时见啦。
爱你的哥哥
我笑了,我并不知道原来他也需要我。有一次,妈妈生病了,我们所有人都忘记了亚当的生日。那天已经过了一半了,他轻轻地提醒我们“我现在要变成一个大男孩了”,妈妈又内疚又担忧。从那以后,这就成了家里的经典笑话。我也用同样轻松的语气回了信:
如果你表现良好的话,我可能会准备一顿晚餐等着你回来。
我得意地笑着。他好像没有不高兴,因为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了:
很快我就要20岁了,青春期将成为过去式,但本质上我还是我。其实生日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本身,改变的是别人对他的期待。对我来说,20岁已经老了,但我明明还很年轻。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正如尼赫鲁所说,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的高潮,这三个我们必须经历的阶段一直不断循环,让我们感激生活的多姿多彩。所以,年龄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它只是“现在”的其中一种时态。
我知道他对印度有多着迷,在印度他能自由自在,摆脱在伦敦的所有压力。但这一年不同,那种无忧无虑的魅力消失了,被一种让人不安的黑暗阴霾所取代:
我还是能感到剧烈的痛苦和空虚,却无法完完全全找到它的来源。世界各地的生命突然变得渺小,变得无关紧要了。这里的一切都很奇怪,还有一种可怜的悲哀感,就算在这里死去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上帝啊,多希望有人能陪陪我,我想见乔,见塔拉,见爸爸,我那可爱的爸爸。
我在哭泣的时候,亚当在奋笔疾书,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在踢那扇该死的门。印度唤醒了他爱分析的大脑,一个19岁的男孩,不停地质疑人生,被妈妈的临终希望折磨着。
我知道生活是自己建立的,但它还是让我感到恐惧。我不停地质疑:我可以成为我吗?我真的能做那些我想做的事吗?我配得上我拥有的机会吗?在这里,在印度,我看到了狂热的人。他们跟随着自己所想,不质疑,不困惑,不去管自己是否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或得到他们被认为应该得到的,他们有的只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应该丢掉所有的疑虑,鼓起勇气去追求我想要的,不要在乎结果。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很幸运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应该让自己成为一个勇敢的人。虽然生来不勇敢,但可以通过努力变得勇敢,勇敢地向着这个世界迈进。我亏欠了太多人,不能辜负他们。
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混乱,他一直掩藏着。人们只能看到那个积极向上、有爱心的亚当,那个在爬喜马拉雅山时会停下来往山下走,帮助他的老师完成多年来一直没有成功的登顶梦的亚当,那个永远照顾着自己的妹妹和朋友的亚当……这是身边的人看见的亚当。
只有他的文字才能暴露那个矛盾的、充满质疑的真实的亚当,与他向世人展示出来的自己是那么的不一样。他总是在孜孜不倦地寻求对世事的理解,寻求内心的纯净,寻求真正的明晰。
这一刻,我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流逝,好像我作为一个人的属性正在消失。上帝啊,保佑我不要再一次变成没用的外星人。我也想变得狂热,但我的心智时而成熟时而幼稚,时而不在状态,时而又焦虑不安,这样是无法得到纯净的感受的。
20岁生日之后的几天,他从印度回来了。我无比想念他,每天都在数着日子等他回来。
他进门时我非常吃惊,不只是他所穿的印度服饰让他看起来像个陌生人——他的脸色惨白,眼窝凹陷,看上去异常憔悴。我的兴奋瞬间变成了恐惧,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在机场被搜身了。他们在我的包里找到了一个烟斗,然后就让我脱光衣服接受搜身,他们看了我的日记。”
“亚当,你在发抖。”我困惑又担心地看着他。
他的表情很茫然,好像灵魂不在这儿一样。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让我觉得不像我的哥哥。
“很高兴回家了。”他说,但他的声音和身体语言看上去一点儿也不高兴。
我站在那儿等待着他说些别的,他的确又说了些话,但不带任何感情:“我走在街上,有个小个子的老妇人经过我身边时对我说,‘不要像那些在这里的印度人那样’。”
我暴跳如雷:“亚当,你应该告诉她你就要去牛津大学了,还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看看她会怎么说!”
我气得要爆炸了,她怎么能这么说?她难道不知道他很完美吗?
他那鬼魅般的脸上满是绝望,我就站在那儿,看着他的意志在我眼前崩溃。我想要他重新变回亚当,变回那个正常的、幽默的哥哥。我想要伸手去抓住他,把他从那个糟糕的世界里拉回来,但他好像在一道防震玻璃的后面,我怎么也无法靠近。他看着我,眼里毫无生气。
“我们给你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你可以在牛津大学里骑。”
“谢谢。”他回答道,没有一丝兴奋。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看上去、感觉上,他都完全与我隔离了,也与这个世界隔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