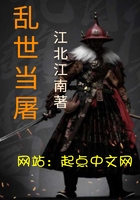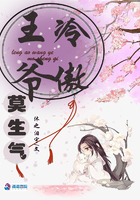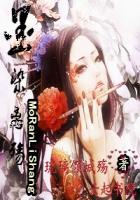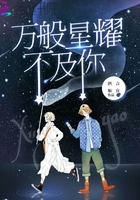第十三章
我为什么写小人物系列杂文
—《浮世杂绘——小人物系列杂文》后记
收在《浮世杂绘》中的50篇小人物系列杂文,是我近两年杂文创新尝试的初步成果。1998年初,我写了《小款情结》一文,以白描手法塑造了“小款”这一新时期特定的历史形象。所谓“小款”,是指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涌现出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受惠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多半供职于外企,思想观念新颖,生活方式新潮,举手投足新派。他们懂外语、会开车、玩电脑,对物质生活质量有着比一般人更强烈的追求。严格说来,他们算不上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也有别于传统的劳动者。对他们的存在,当时还难以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有人羡慕他们,认为他们不是白领,起码是准白领;也有人鄙视他们,觉得他们不过是一群向往物质生活、思想观念前卫、行为方式另类的一群。在当时,虽然全社会对这个人群不无关注,但似乎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小款”这个未必准确的概念。《小款情结》一文不仅较为敏感地注意到了小款阶层的存在,而且较早提出“小款”概念,比较全面地为小款画像,这在当时是多少有点新意的。此文在天津《今晚报》发表后,受到编者和读者的好评,至少有六家报刊予以转载,还有韩三洲等同志撰文与我商榷。在“猫不闻”全国杂文征文大赛中,此文获二等奖。获奖文集也以此文命名。
1999年元月,上海《文汇报》开设“杂文人物谱”专栏,旨在倡导文艺性的杂文。该栏目选介的第一篇杂文,就是《小款情结》。为了突出文章的分量,编者朱大路先生还特意约请牧惠先生撰写评论文章,请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为本文配画,同时还配发了作者小传。2000年第一期《新闻与写作》杂志再次刊发此文,并由栏目主持人陆士华先生撰写评论文章,由我写创作谈。一报一刊推介后,此文产生了更大影响,一些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绩的文集大都选收了这篇文章。
1998年夏,《今晚报》编辑张金丰先生约我去天津参加杂文学会组织的杂文创作沙龙活动。在那次会议上,我比较坦率地谈了自己十余年创作杂文的一些心得体会。说到杂文创新问题,我认为杂文不仅可以走议论的路子,也可以走描写的路子;不仅可以以论理见长,也可以通过白描等传统手法塑造典型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就不乏这种杂文传统,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等都可视为这类杂文的典范。遗憾的是,在此后的杂文创作中,特别是当代杂文创作中,自觉继承这一优秀传统的杂文家似乎并不多,能够形成规模的作品就更少。
在那次会议上我还提出:近年来的杂文评论中,大家普遍认为新时期的杂文创作是建国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不仅表现为数量的空前增多,也体现为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但与此同时,杂文作为文艺性的政论,其文艺性、文学性还不够强,杂而无“文”的现象普遍存在,报刊言论式的杂文俯拾皆是。
怎样改变这种局面?我以为继承白描传统、塑造典型形象,不失为值得一试的方法。
就是在那次沙龙活动上,我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创新思路,同时提出已有计划,准备了几十个题目。这可以说是写作这组文章的最初缘起。
写作小人物系列杂文还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芸芸众生之中,我本人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熟悉小人物的生活,理解他们的状态,同情他们的遭遇。在对他们的发现与描写之中,寄予了我本人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或者可以说,我笔下的小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我自己的影子。我是带有批判与反省的精神去描写他们的。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无助与无奈、丑陋与卑微,使我既理解又鄙视,既同情又厌恶。这样的感觉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
在我看来,写小人物系列杂文还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我把小人物杂文自喻为“发现体杂文”。这样说当然不是表白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发现。所谓“发现体杂文”,是说对生活中人们习焉不察的人和事予以发现,把他们揭示出来,描写出来,使读者有一种“原来是这样”、“我怎么没注意”的感觉。罗丹说过:“生活中从来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我所描写的小人物很难说是美是丑,我在写作中也力图采取一种客观的视角去观察和描写他们,尽量避免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我所做的不过是“发现”的工作,是对大家没有关注或关注得不够的人和事给予更多、更自觉、更明确的关注。我观察普通人的言谈举止、外在形貌,揣摩他们的心理活动、内在世界,并用白描的手法把他们描写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个人认为这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此前十年的杂文创作中,我写了不少以议论为主的文章。说句老实话,那些文章不无耳提面命的色彩,有时可能还多少有一点教师爷的腔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资格对读者说三道四,以先知自居。虽然没有人说过,但我自己总有一种“朱铁志一思考,读者就发笑”的恐惧。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世界,我的信息量未必比读者大,获取信息的速度未必比读者快,议论与思考未必比读者深刻。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乱发议论呢?而写作小人物系列杂文,把我的发现尽量鲜活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过是向读者提供思考的元素而已,是非善恶,读者自会思考、自会判断,无须我饶舌。我把这理解为对读者理智程度和思考水平的尊重,也是我提醒自己多一点自知之明的努力。
我想,小人物系列杂文也许不失为观察当代生活的一个独特视角。我所描写的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他们表面上是孤立的“这一个”,但集中在一起,就有可能成为当代生活的全景画面——当然,那是属于我眼中的全景画面而已。
那次沙龙活动之后,金丰先生以一个资深编辑特有的敏感抓住了小人物系列杂文这个选题,多次与我联系,鼓励我抓紧时间把这组文章写出来。1999年初,他专程来京催促我,并建议我向方成先生求画,以便图文并茂地在他供职的《今晚报》上连续发表。他的建议使我兴奋不已,同时也感到心里没底。方老是国内最优秀的漫画大家之一,而且已届耄耋之年。说句老实话,以我的资历和水平,去向方老求画是很费踌躇的。金丰看出了我的心思,极力怂恿我鼓足勇气试一试。没想到方老一点架子也没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并对我的写作计划予以肯定。方老的肯定和提携,对我是莫大的鼓舞,也使我对写好这组文章更加充满信心。如果没有方老的提携和支持,我能否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写完这组文章可能还是个问题。
从1999年上半年起,小人物系列杂文开始在《今晚报》首发,随后又在山东的《齐鲁晚报》、辽宁的《党风月报》发表。《武汉晨报》也选发了其中部分篇章。2000年上半年,潘多拉同志选择其中10篇在《北京青年报》发表。年底,王乾荣先生又为这组文章配诗在《法制日报》重新发表。在此期间,长春的《杂文选刊》、石家庄的《杂文月刊》、《广州日报》、《读者》、《作家文摘》、《青年博览》、搜狐网、新浪网等媒体都对小人物系列杂文进行转载。杂文界的一些前辈和朋友也对这组文章给予肯定。更令我感动的是,一些普通读者对这组文章的厚爱。辽宁辽中县采油厂二矿退休职工萧殿忠同志致函《法制日报》编者说:“请把‘小人儿串子’连续写下去!这是我要说的话。这些文章真是好看,令人叫绝。我已悉数剪下,准备剪贴成册,并已写好‘前言’,现抄录如下:好一个‘铿锵三人行’!——朱铁志写文,方成作画,看罢令人拍案叫绝!把一群‘小XXX’写得活灵活现,这一‘小人儿串子’成了某一层次人的真实写照。文章精彩绝伦,笔锋犀利,令人看后忍俊不禁又带点苦涩的味道;讽刺诗幽默风趣,给人以深刻启迪;漫画惟妙惟肖,活脱脱地展现在你面前一个个‘小’来……好久没有读到这么泼辣生动、刻画细腻、入木三分、轻松活泼的文章了。好,真就是好!”普通读者对小人物杂文的肯定和喜爱使我十分欣慰,也非常感动,我觉得自己为普通百姓立言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这本小书即将出版的时候,请允许我真诚地向著名漫画家方成老表示感谢,向帮助我下定决心写作这组文章的金丰先生表示感谢,向为这组文章配诗并为本书慷慨作序的乾荣先生表示感谢,向《文汇报》朱大路先生、《齐鲁晚报》张金岭先生、《北京青年报》潘多拉先生、《党风月报》姜成刚先生、《武汉晨报》刘洪波先生表示感谢。向所有对小人物杂文予以关注——不论是热情鼓励,还是严厉批评的广大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提携我出版本书的何满子先生、接受本书的福建人民出版社表示感谢。
我知道自己的尝试还很不成熟,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我期待着各位方家和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
(《浮世杂绘》,朱铁志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系何满子主编“瞻顾文丛”之一。)
我的杂文观
——《精神的归宿》自序
中国人直立的历史还不长,多数中国人脑后仍拖着一条无形的辫子。
传统文化向来缺少独立的姿态;
传统文人也不多见独立的品格。
封建主义依然是现代化的敌人,是中国人民迈步走向明天的无时不在的拦路虎。如果不能彻底解除封建主义的桎梏,如果稍微减缓了对它的自觉斗争,那么,何谈人的现代化?何谈民族的未来?
杂文,是射向封建主义及其直系亲属官僚主义的枪弹。也许对于强大的敌人来说,这枪弹的威力未免太微弱、杀伤力太有限。然而伟大的战役从来不排斥弱小的力量。不能毙命,使其负伤也好;不能断其一指,伤其一指也不错。诚如王蒙所说:“没有微言大义,微言小义也可;不能入木三分,入木三厘也行。”
不能发现真理,起码可以捍卫真理;不能全说真话,起码可以不说假话,少说废话,尽量捍卫说真话的自由和权利。
不被鬼脸所吓,也不做鬼脸吓人;不被媚态所惑,也不谄媚于人。
杂文的骨髓里不仅有钙,而且有钢、有铁、有一切宁折不弯的材料和品质。
见不得冷脸的人,不要写杂文;
耐不住寂寞的人,不要写杂文;
见官腿软的人,不要写杂文;
见钱眼开的人,也不要写杂文。
不做吹捧者吹捧的奴隶,也不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喜也杂文,悲也杂文,荣也杂文,辱也杂文,然后近乎杂文家。
杂文虽小,但不拒广博。专业的杂文家其实不是好的杂文家,没有专业的人士难以成为杂文家。然则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就能当好杂文家吗?也未见得。
学养固然重要,人格更不可缺。
笃信“学而优则仕”的人,当不了杂文家;
希冀“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当不了杂文家;
梦想学而优则商、学而优则名的人就当得了杂文家吗?
世间砖头万种,唯有杂文这块砖头最硬;
然而用于“敲门”,最不灵。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笑;
搬起杂文砸自己的脚,可敬。
杂文不是手电筒,要照亮别人,先要照亮自己;要解剖社会,先要解剖自己。杂文崇尚“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更要“三省乎己”,把自己“撕碎了给人看”。
杂文的“戏剧理论”中,推崇本色演员,而对演技派嗤之以鼻。可以像生活那样演戏,但不能像演戏那样生活。如果大胆把杂文比作一种特殊的“戏剧”,那么像杂文那样生活也许不是坏事。
没有理论的创作是经验主义的瞎子摸象;
没有创作的理论连苍白贫血都谈不上。
有杂文家,也有杂文官、杂文商、杂文骗子……如果把杂文比作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最后与之结为伉俪的,只能是真正的杂文家。不羡官位,不贪钱财,不事“瞒”与“骗”,这是杂文的风骨所在、魅力所在。
人生得一知己足以,杂文庶几近之,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精神的归宿》,朱铁志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2001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我的自白
—《拯救自我》自序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杂文不算什么学问,无非是不成系统的雕虫小技而已。而在另一些人的自我标榜中,又把杂文说得天花乱坠,好像它可以普度众生、救民众于水火。对两种看法,我都不敢贸然说什么。在我的观念中,杂文的确不是黑格尔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被概念、判断、推理所充斥的学术体系,但它也绝不是百无一用。
我不曾把杂文当做所谓的“纯学术”来经营,因为它原本不是。我也不曾带着轻慢的态度玩儿杂文,因为它本身所特有的凛然正气,决定了它不会成为任何人把玩的对象。写杂文的人一旦产生了“玩儿”的念头,事实上已成了杂文的弃儿。
杂文虽然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也决非什么人都可以随便为之。也许它配不上“匕首、投枪”的称谓,算不上“银针、手术刀”,但它总还可以寄托正直人的正直情感,有益于世道人心。有好人喜欢它,有坏人讨厌它,有不好不坏的人容忍接受它,这就够了。
对我而言,少年的抱负、青年的理想、中年的责任,都体现在杂文写作中。不说作品的客观效果如何,单就主观感受而言,杂文的确成了我拯救自己的有效手段。也许有人会问:你迷失自我了吗?那么请允许我反问一句:您不曾迷失自我吗?您从来没有产生过寻找自我的冲动吗?您始终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主宰吗?如果您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无话可说;如果您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无须我再说什吗。
每个人寻找自我、维护自尊的方式与途径不同。对我而言,就是热爱杂文、写作杂文,在它可能存在的良性社会效应中享受快乐。
(《拯救自我》,朱铁志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系王剑冰主编“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获奖者丛书”之一种。)
我思故我在
—《你以为你是谁》自序
我一向对序言不感兴趣。一本书写完了,该说的话已囊括在书里边,读者不是傻瓜,自会从书中看出作者那点意思。如果那意思很有意思,作者或可因为不写序言而意外获得一份“含蓄”的夸赞;如果那意思很没意思,作者又恰好在书前喋喋不休一番,岂不是自取其辱?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总是不写序言,希望作者径直走进书里。
而这一次却不行。丛书的其他作者都有话要说,编者为了统一体例,要求我也对读者有所交代。想来想去,还是说说自己为什么写杂文吧。
杂文之于我,首先是长期摸索、尝试、选择的结果。从少年时起,我就是一个真心实意喜欢写作的人。尽管那个时候条件不好,思想资源十分匮乏,但并不妨碍一个敏感的心灵对外在世界有所感悟。从初中三年级到高中毕业,连抄带写,我零七八碎地涂满了好几大本,有小说、散文、独幕话剧、相声,甚至还有一个电影剧本,汇集起来总有一二十万字吧。这些“作品”的幼稚可笑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创作过程中所寄予的对文学的真诚热爱,却毫不逊色于任何伟大作家。后来我阴差阳错地考上了大学哲学系,而没能如愿考取中文系,为此着实苦恼了一阵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喜欢上了哲学,从心底认同了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毕业以后,我被分到一家政治理论刊物工作。表面看来,这个工作与文学似乎毫不搭界,而事实上一颗真正热爱文学的心并不那么容易为工作性质所阻隔,白天搞理论,晚上弄文学,不断尝试、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学道路,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这期间,又散乱地写过一些诗歌、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等。虽然这些东西也能比较顺利地发表在报刊上,但我总有一种没有找到感觉的感觉。
到底什么体裁才是适合我的文学样式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到一位我永远尊敬的前辈,这就是牧惠先生。当我在文学道路上苦苦追寻、四处徘徊的时候,意外发现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杂文作品的牧惠先生就是我们单位的林文山同志。他不仅以富有思想深度的杂文作品让我叹服,而且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写作方式让我受到启发。从那时起,我才开始真正冷静地分析自己的知识准备、性格特点,决定把文学创作定位于杂文写作上。这既可以发挥自己学习哲学长于思辨的优势,又可利用多年喜欢文学形成的艺术感觉,两相结合,或许能够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文学道路来。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大体是不错的。
杂文之于我,是写作兴趣的具体寄托。古来的文人总喜欢把写作弄得很崇高、很悲壮的样子,什么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啊,什么“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啊,好像写文章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说老实话,在我的心目中,从来没把文章放到这样的高度。一个人写作,首先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劳作方式,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这种方式适合于自己,能够带来快乐。当然我并不否认有些人是怀着十分崇高的理想而写作的,他们同样能够写得很好。但对多数人而言,写作首先是一种兴趣的寄托,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杂文之于我就是这样,我喜欢这种短小精悍的文学样式,它能够让我在写作中充分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享受写作的快乐。迄今为止,只有三样东西能够长久地给我带来快乐,一是杂文,二是古典音乐,三是足球。不仅如此,我还有一种固执的看法:只有那些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事业,才能被人长久地热爱,使人痴迷其中、乐此不疲。
杂文之于我,是思想的体操、精神的锻炼。有人说人生原本无所谓价值,所谓人生的价值,都是人们在实践中自己赋予的。而我以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不论他从事什么行当,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总是其存在的根本依据。一个有知识而没智慧,有智慧而没思想,有思想而没自由的知识分子,他的存在价值是令人怀疑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有赖于在风雨中磨炼,在实践中探索,在挫折中锻造。写杂文的人和所有写其他文章的人一样,都是心中有所感,而笔下有所言的。要写出好的杂文,就必须时刻保持对社会的敏感,没有一颗敏感的心、一双锐利的眼,就不可能写出像样的杂文。黄一龙先生说过,杂文家的血沸点很低,只要50度就沸腾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杂文家的爱憎更鲜明、心灵更敏感。杂文对于我来说,是思想的体操、精神的锻炼,是保持鲜活思想和独立品格的最好载体。
杂文之于我,是与社会紧密联系的重要媒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脱离社会生活的所谓“个人化写作”其实是不可能的。如果写作杂文仅仅成为自娱自乐的玩意儿,那它的社会价值当然是谈不上的。人要写文章,总是源于他对这个社会有话说。从最朴素的道理出发,无非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对我而言,写作杂文是对社会发言的一种形式,我要把自己心中的爱憎好恶都形之于笔端,诉诸读者,“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尽管我的声音很微弱,有时甚至不免近于无声,但说了总比不说好,哪怕只有一个读者读到了,并为我所彰显的正确思想所感染,那我也是欣慰的。
杂文之于我,是自身价值实现的有效渠道。人在温饱之余,总是期望自身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不同,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和方法也不同。音乐家的价值在乐坛上,球星的价值在绿茵场上,对我而言,人生的价值在于杂文写作中。只有在不断的写作、不断的自我超越中,才感到自己正在走一条积极向上的人生道路,正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行进在自我实现的征途中。而这种实现,不是关起门来的孤芳自赏,也不是脱离群众、脱离社会的顾影自怜。我在一封封来自底层的读者来信中感到了作为杂文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感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思考,让我找到了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位置;写作,或许是迄今为止唯一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我思考,我存在;我思考,我快乐;我将沿着这条羊肠小道一直走下去。
(《你以为你是谁》,朱铁志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