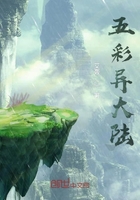抗战胜利六十年了,土尔吉也老了,六十年间他一直住在缅东北的小镇——巴默。
在巴默镇东被当地人称为“乱造坟”的无名山(滇西大反攻时称五六六高地)山坡上,脸上长满黄褐色老年斑的老军人土尔吉按时出现在这里。虽然老人年事已高但腰板还算挺直,无论是雨季还是旱季,只要不遇到瓢泼大雨或生病躺在床上,他几乎每天都像一座精准的时钟在天麻麻亮的时候来到五六六高地,围着战友们的亡灵转上数圈。
六十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他来山上的真正目的,也没有任何人有兴趣去探究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贫困老兵的内心隐秘。岁月流逝,从他逐渐蹒跚的步履一看就知道他正慢慢地老去,正亦步亦趋地走向死亡,走向与昔日的战友们同归的极乐世界。从他慈善的容貌透出,他正平心静气地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五六六高地无疑是他的最终归宿。
五六六高地上东歪西斜的“乱造坟”,空前的寂静是当地人对它“敬而远之”造成的,寂静、隐秘恰好与老兵的只身孤影形成一道孤寂的“风景”。同清晨睡在垃圾桶边无人问津的流浪狗一样,这道“风景”被健忘的人们忘却在历史的尘埃中整整六十年了,唯有这位老兵用身心守护这道有话要说的“伤痕”,似乎这道“伤痕”被喧嚣的世界遗忘了,巴默也不例外。唯有高地上那些面朝东南方向的坟头里的亡灵在耐心倾听土尔吉的脚步声,他背负着永存于记忆里的爆炸声和惨叫声凝视着一位位躺在地下的战友,心在问:战争到底给人类留下了什么?是胜者的快乐还是败者的伤痛?必须对战争彻底说不!毫无疑问,战争就是罪恶!战争是人类永恒的耻辱!
昨晚,巴默远处的群山阵阵轰鸣的雷声预示着缅北的雨季提前了。清晨刚刚下过一阵雨,为了躲过那阵雨老土尔吉上山晚了一些。空气中透出丝丝凉意,他穿上一件稍厚的白短袖衬衫,一条咖啡色的隆基(筒裙),趿着一双人字拖鞋,右手拿着一串佛珠,左手握着一把雨伞出门了。这装束,如果不是脖子上挂着一根金刚结连接着当年阿妈送给他的铸拓和情人送的小银嘎乌这些藏人特有的精神饰物外,没人能分辨出他不是一位缅甸人。
五六六高地那场称为“夺命竞赛”的战役胜利后,土尔吉就为自己立下一个终身的誓言:永远定居巴默。准备用接下来的人生为阵亡在五六六高地的战友守灵,用藏人祭奠亡灵的方式为他们超度,为他们吟诵《度亡经》,立誓在今后的岁月里只要还能移动自己的双腿,超度的经声就会像经堂里供佛的油灯那样不灭。六十个寒暑弹指般过去了,土尔吉——作为一名藏族远征军老兵,用意志、体能和承诺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五六六高地上泥土的“硝烟”一直弥漫在他的记忆里,记忆里他同战友们拥挤在一起。他常常在同“乱造坟”里的战友通白(活人讲给亡灵的话)时说:“嘿嘿嘿,伙计们,我的余生只剩下了使命,如果到了血管里的血液不再流动的时候,你们就在天堂的门口排队迎接我吧。”
踏上五六六高地,在他六十年如梦如幻的感觉中,三营的战友们个个像刚入伍的新兵一样,穿着崭新的军服抢着跟他聊天,不同的是他们的姿态各个不同而已。的确是这样的,他每天踏入坟场遇见的第一位亡灵便是那位坐着抽烟的二连三排一班的班副贺有光,唯有靠回忆才能恢复听觉的他就听见贺有光在叫他,“嗨,医疗兵,我快没有烟叶了。最好带些四川崇庆州的‘州烟’来。在四川泸州集训的时候,抽川烟上瘾了。”“好的,老哥子,我明天就给你带上山来。”“中(行、好)。”贺有光用浓郁的河南商丘话说;贺有光的旁边是当年在岔路口杀死日军报务兵的山东籍老兵肖淑贵,此人是标准的山东大汉,他胡子拉碴蹲着在喝酒,“哈哈,土尔吉,你不知道,我昨晚又喝醉了,迷糊中看见我们村的小脚媒婆正牵着我的心上人二妞朝葫芦村赶,心想,二妞不是和我定亲了吗?怎么还跟媒婆勾搭在一起,我气坏了,抄起锄头朝她们追去。
快要追上的时候,奶奶的,二妞没了,我正气不打一处来时,看见小脚媒婆的红裤衩跑掉了,露出圆圆的肥屁股,我的那玩意儿一下子就硬起来了,但就是够不着,你说,急人不急人。”土尔吉笑了笑没有吱声;拐过一个弯,特别嗜睡的湖南籍战士王大憨永远睡不醒似的躺在地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他笑着绕开王大憨;看见贡布习惯性地盘腿打坐,这个坐姿一看便知道是草原人特有的姿势。“嘿,土尔吉,雍金玛带着儿子小贡布来看我刚走的第二天,你说让我高兴不高兴,雪上飞从大面城来看我了……”土尔吉正准备陪着贡布拉拉家常,刚站定就听见躺在坟墓里的战友七嘴八舌地叫他,“嗨,土尔吉今天怎么不理我呢?”“老弟,别急,我土尔吉只有一张嘴啊,马上就来。”“哼,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哩。”“嗨……”“嗨……”亡灵们争先恐后抢着要同土尔吉说话,“别着急,一个一个地来,我土尔吉只有一张嘴啊,伙计们。”他应酬着。
在安抚战友的同时,他感到自己的胳膊肘被一股力量拉扯了一下,不过拉扯的力量并不大,在站稳脚跟后,转身看了看,一张笑盈盈的娃娃脸在他的眼前晃了晃,“嗨,这不是二班的小华仔吗?”土尔吉在叫出他名字的时候,小华仔的面孔消失了,但小华仔的歌声却从遥远的六十年前徐徐朝他飘来,熟悉的歌声在耳际萦绕。土尔吉随着歌声也跟着兴奋地哼唱起来:“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兄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热爱的……”
小华仔这位不到十七岁的南洋华侨的后代,大反攻时随着他的舅舅一起从马来西亚到滇西,这批华侨共两百人参加到大反攻的行列。他们绝大多数做汽车驾驶的教官,专门培训开汽车的驾驶员,当时滇缅公路是唯一的运输线,需要大量的司机,这些从南洋来的机工,许多人懂技术,他们的家园被日军占领后纷纷回到祖国,为抗战效力。小华仔的舅舅被编入运输十二大队,在畹町至下关的三百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段,开着奔驰柴油车运送补给。令土尔吉终生难忘的是,旱季末的一个下午,小华仔的舅舅开的车拉着一车的食品和帐篷被日军的飞机炸弹击中了,他的舅舅受重伤,生命危在旦夕,小华仔急得不知所措哇哇哇地大哭,不停地呼喊救命。当土尔吉赶到的时候,小华仔的舅舅拒绝土尔吉的急救,说:“大陆同胞,我知道我的伤势,我快死了,救也是白搭。”心急如焚的小华仔却跪在地上求土尔吉救救他,他舅舅勉强挤出微笑对小华仔说:“阿仔,谢谢了,记住,舅舅和家里人是怎么死的,是为抗战而死的,中国人是不会做亡国奴的。就像《光华日报》教机工们唱的那首歌。”小华仔含泪点点头。“孩子,振作起来,我们一起来唱。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兄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热爱的……”歌没有唱到一半这位华侨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小华仔突然哭叫着站起身来,“狗日的日本人,老子对你们恨之入骨。”说着抓起枪对低空飞行的日机射击,与此同时,四架机翼上绘有鲨鱼图案的美军飞虎队的P-40战斗机出现在天空,日机仓皇而逃。从那一刻,小华仔说什么也不走了,他被补充在土尔吉所属的三营二连一排二班。在土尔吉对小华仔的最后记忆里,这位塌鼻梁大眼睛的小战士是头部中弹而亡的,当他替他包扎好时,他已奄奄一息了。他对土尔吉说:“你还记得我的舅舅吗?他知道他不行了,所以拒绝包扎,但我还年轻,还不想死啊。我的爸爸妈妈是被日机炸死的,剩下一个妹妹,寄养在舅爷家,我是偷着离开她的,之前答应给她带她最爱吃的马来西亚芒果汁软糖,软糖是用白砂糖、浓芒果汁、棕榈油、柠檬做的,好吃极了。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太爱她了。”说罢开始呜咽起来。当时,土尔吉对他说:“小华仔,你不会死的,为了你妹妹,为了胜利,我们一起唱《祖国我所爱》那首歌好吗?”他们一同唱起来,当土尔吉只听见自己的声音时,小华仔已安静地闭上了眼睛,那张可爱的娃娃脸从此消失了。
在土尔吉眼里战友们的模样依旧清晰,表情像是去参加草原的赛马会,看不见血腥、看不见硝烟、看不见累累的伤痕,唯一跟六十年前不一样的是,六十年后这些昔日的战友个个谈吐非凡,仿佛在曾经是血雨腥风的土地上吸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用年轻的躯体筑起坚硬的壁垒,仿佛生与死的哲学命题在他们的口中已经找到了完满的答案,令土尔吉伸舌敬畏。
一旦步入五六六高地的“乱造坟”,土尔吉的身体就有一种轻飘空灵的感觉,就有一种宁静的亲切感和归属感,生命中的浮尘便在用年轻肉身奉献的土地上一点点滤掉了。在血雨腥风中幸存下来的土尔吉,用了一生的时间思考和实践佛善理念。在对待生命及生与死的轮回命题中,他终于悟出:大地是人的身体和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灵魂和情意的组成部分,是生命永恒的延伸。康巴人根深蒂固的生命理念中,大地等同于人和神,是有生命的,充满了思想和灵性,是自然和人融为一体的境界,是佛的境界。因此,缅甸,这个被称之为“万塔之国”的佛教国度,成为他的理想栖身之地。
每天早上六点半至八点半,老土尔吉都会以军人的时间概念来这里诵经,诵完经后照例同战友们“聊”上一阵。今天也不例外,意外的是他正准备离开时,刚好一只白尾鸟站在写有“中国远征军八八师三二〇团三营全体阵亡将士之墓”的青石碑顶端,当它发出呼朋引伴的鸣叫声时,在上面拉下数粒鸟屎,“秋秋秋(驱赶声),你们这些讨厌的小家伙,拉屎也不选个地方,秋秋。”他用伞在空中比画了几下,受惊的白尾鸟扑棱着湿漉漉的翅膀飞走了。他将雨伞夹在腋下,腾出手来在地上拾起一片干净的树叶,用它仔细地把石碑上的鸟屎擦掉,然后凑近墓碑用手指肚摸了摸刻字凹下去的沟槽,沟槽里用红色油漆填写的字模糊了,显出同青石碑一样的颜色。他自言自语又像是对长眠在地下的战友在说:“等过几天为寺庙打制的铜板雕花换回了工钱,再选择一个晴朗的日子,就去买红油漆把这些字重新填红。”每年一次,这是土尔吉给自己订的规矩,今年是第六十次了,他发誓,只要他活着,战友纪念碑上的字就不会模糊。
土尔吉静静地在墓碑旁站了一会儿,随后平静地朝东边的佛塔走去。佛塔的东面距寺庙有一段距离。佛塔离五六六高地约莫要走半个钟头,围着佛塔转十三圈后再步行一段路程就来到寺庙的正门。他面对正门双手合十深深地三鞠躬便围着寺庙转三圈。六十年来,他从未踏进这座寺庙的大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六十四前自己被绒布寺驱除之后从此不敢再跨进寺庙,担心自己与女人交媾的晦气会玷污寺庙,更何况自己还在战争中“杀”过人。佛规中一系列的禁忌限制了他的脚步,这些秘密一直掩藏在内心深处,只要看见金碧辉煌的庙宇,他就会下意识地望而停步,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永远没有资格进入寺庙的扎洛。
六十年来土尔吉一直守住这一规矩,尽管他知道熊朵草原流传着一个真信佛和假信佛的故事。故事讲一位地位低下的宰牛人至死都认为自己因杀生太多,是一个该下地狱的人,于是抱定一死的决心走下悬崖,这一过程被一个口口声声自诩自己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的人看见了,在自诩者的眼中,宰牛人非但没有掉下悬崖粉身碎骨,而是从天空的云端里伸来一束彩虹,托住宰牛人升到了天国。自诩者眼红了,他顺着宰牛人的足迹纵身跳下悬崖,但他的线路恰恰与宰牛人相反,自诩者摔得粉身碎骨。
他深信宰牛人对佛的心诚与他对佛的心诚是一样的,世俗的眼光是难以剥开真伪的。
回到南兰路自己的小作坊已是十点半钟,照例在小作坊里屋东面的佛龛上点燃一炷香后,便面对升腾的烟柱双手合十祈佑平安。随后来到临街的作坊开始干活。作坊的周围摆放着银匠的工具,与其他银匠铺不一样的是,当过军人的土尔吉,他的作坊是整洁有序的。为了在制作中各种工具伸手可得,他做过精心的安排,哪些位置是放置二十四根圆头的、平头的、空心头的、月牙头的这些专用小钢钎的;哪些位置是放置松香、清油、稀硫酸、白矾水、煤油灯、吹筒这一类的;那些位置是放坩埚、木炭、铁锤、铁砧和铸铁模具的,一切都像当医疗兵时候的医疗箱里的药品和器械的放置,井井有条,每天的工作就在井井有条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