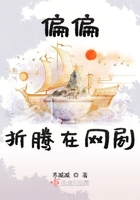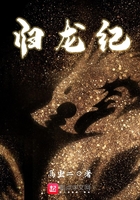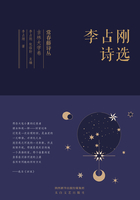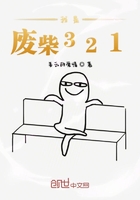春节得暇,随手翻阅近年漏读的小说,不意渐渐读之入迷;一面深悔昔日对一些精采篇章失之怠慢,一面则对流行的“疲软”“停滞”之类大而化之的说法产生疑惑。诚然,如今小说已不复多年前的轰动爆炸之势,也不复几年前的思潮迭起之态,冷清了许多,但是,轰动爆炸需要足够的社会心理蓄势和历史条件的积聚,思潮迭起也是多重原因方可促成,它们都是可遇而不可强求的。因之,倘若不以轰动与否,热闹与否作为评衡创作发展的唯一尺度的话,那么可以说,即使近二年的小说,也依然投有止息它内在的一贯的探索精神。探索的热点可能有所移易,但探索的意向没有变;只是,难度更大了,步伐放慢了,纠缠的创作问题更复杂了,规模缩小了,一时难以形成声色壮阔的阵容。当我读到象《明天的太阳》《无边无际的早晨》《神戏》《狼毒花》《焚烧的春天》《毛雪》《半边营》、《女人秋》《小学老师》《乡村情感》等等作品(这只是一小部分)的时候,怎能不感到严肃的思考、惨淡的经营和鲜活的冲力。无论是乡土小说还是都市文学,都有一张希冀深化的犁铧在艰难地向下掘发着。
当然,不能靠这几部作品来概括创作的全貌,若把新时期小说比作一条河流,如今它的流速无疑是缓慢多了。但就某种意义来说,目前的状态也是一种必然,它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所以,重要的不是寻找词汇给它下个判断,而是要在顾及到小说创作整体流程的情况下,在深入到创作实践的动态中,思索问题。
这是不可能离开新时期小说的总背景的。新时期小说的繁复多样,常使概括者无从下手。近来忽然悟到,十三年来,无非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六大流脉的升沉浮降。所谓六大流脉,有些着眼于题材,有些着眼于思潮,有些着眼于方法,虽时有交叉,但眉目清晰,纵有倒外,也不多,大体可以概括新时期小说的总体流程。倘换个角度,再看创作中的主题取向,也不是不可划分,大致有:政治主题、社会主题、人生主题、生命主题、文化或亚文化主题、非理性主题,历史主题等。这里所说的主题,是指关于价值取向的“大主题”,与具体作品的具象化主题自然有别。在上面列举的每种大主题的下面,都不难开列出一批相应的作品。比如,《伤痕》《重逢》属政治主题,《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属社会主题,《风景》《烦恼人生》属人生主题,《伏羲伏羲》《红高粱》属生命主题,《小鲍庄》《爸爸爸》《棋王》《厚土》属文化主题,《你别无选择》《黑颜色》属非理性主题,《国殇》《诺言》类属历史主题。观察这些主题的演化,交叉,变异也是很有意思的,从中也可理出一条新时期小说衍化的内在线索。
在这里,我们没有篇幅详细反思六大流脉浮沉的前因后果,也无法细致分析各个大主题的演化变迁,那是些大题目,留待日后去做。我之提到这些流脉和主题,无非作为一种背景,免得下面要谈的问题太突兀。下面还是扣紧近几年的创作来谈。在我看来,近几年小说的总势趋,是从“主观化”向“客观化”的过渡,从“观念期”向“生活流”的过渡,从个体生命意识向群体生存本相的过渡。这样的概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囊括纷纭多样的创作现象,但作为一定时期的主导性潮流,似乎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从当前创作中拎出了几个小题目,诸如:对主题意识的再认识,典型境遇和典型状态,自然主义复萌了吗,以及问题小说会不会复兴等。也许,这些问题正可窥见当前小说创作自我调节和演变的某些轨迹。
一、对主体意识的再认识
谁都承认,新时期小说比起过去时期的小说,无论内容、形态、方法、形式、语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缤纷多姿是空前的。那么,变化的原因和核心何在?毫无疑问,主要在作家主体身上,在主体的自如,主体的开放,主体的丰富和多样上。所以,尽管对主体性的认识还有分歧,或不无谬见,但主体意识的强化毕竟是是值得肯定的进步。过去,我们确曾受到过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恩格斯批评过的,旧唯物主义者总是从客体的形式理解事物,总是忘记“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来理解”的情形,在我们这里也多有表现,我们也确曾存在脱离主体的特殊性、能动性而片面强调生活的决定性的倾向。此如,不问不同作家的不同气质、个性、风格和感应范围、感应方式,一齐下去“体验”某一方面生活的现象;在艺术方法的选择,慨括生活的方式,观察生活的视角上的一统化的现象,都曾经有过。新时期前期的伤痕和反思文学,它们的思想艺术成就自是不容否定的,其中生活的密度和体验深度也许为后来的某些作品所不及,但细想起来,它的方法、视角、表现方式倒确实比较单一,基本延续传统写实的道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外来的刺激”打破了原先相对单调的格局,好象在一个早晨忽然冒出许多种“意识”,如现代意识,忧患意识,忏悔意识,寻根意识,未来意识,宇宙意识,审父意识等等,多得难以计数。时髦所及,有些“意识”难免不科学,不准确,边界模糊,各执一端,但都奔涌而出。与此同时,小说创作上的各种“化”也多得惊人,如哲理化,象片化,哲理化,荒诞化,淡化,诗化,散文化等等。那个时候,小说领域确实是极写实的与极空灵的、极荒诞的与极理性的并存,各式各样的小说都出现了。在这旋转舞台后面的,是作家们对生活的感受、理解、评价、把握上的多样选择。先锋往往是牺牲的代词,可资流传的精品或许不很多,但主体的活跃,创新的潮流,则对小说创作思维的开发,视角的变化,方法的选择,起到了开拓和冲创的作用,功不可没。小说的传统定义需要修改,人们开始看到小说表现生活的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按说,小说创作因主体意识的初步强化就此可以节节推进,大幅度向纵深发展了吧?事实却是,前面的路并不径情直遂,繁华热闹没有维持太久,便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小说追求形而上的哲理,却没有足够的感性血肉;有些小说追求多义性的主题,反而变成无法卒读的理念集合;有的小说追求文化意识的显现,却因过分剔除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较为切实的内容变得抽象而空玄。小说固属“无法之法”。伸缩余地极大,但对某些历久形成的可读性因素颠覆过甚,致使有些小说失却起码的传达功能,所以,“小说不好看了”的说法倘不是偏执传统,也不无一定道理。当然,不可否认,另一种情况也存在着,那就是摆不脱固定的视角,打不破积久的模式,永远在自己重复自己。这些不是一时间小说创作的全部,但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过去,那种把小说作为形象地演绎流行政治命题的工具的情形,是一种非小说化,而近年来有的小说成为直接运载文化观念,哲学观念的形象化工具,也是一种新的非小说化。原因何在呢?我们以为,原因仍在作家主体身上。总的来说,主体意识的初步强化带来了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的纷繁多样,但创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特定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以及来自社会和读者的反馈,又把一个尖锐的新问题提到作家面前:怎样深入理解主体意识的强化?什么是主题意识进一步强化,丰富化,深刻化的途径?这是关系到小说创作向深化和宏阔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存在着两种偏颇。一种情形是,误以为主体意识只是作家单方面的孤立的绝对的活动,把主体等同于“自我”的凭空发挥和张扬,出现了割弃客体面对个人的意志和本能的崇拜倾向,结果是“主体”吞噬客体,排斥客体,使其创作日益走向枯竭、重复、空玄和玩弄文字游戏。这不是什么主体意识的强化,而是跨出极限后的主体的泯灭。记得刘恒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他是有憾于抽象观念对文学的强奸而转向生活化、生活流的。为什么看近几年的有些小说,我们常会产生观念、手法上去了,艺术、形象却跟不上去的感觉,好似一个头脑过大,躯体瘦弱的人呢?问题就在,观念不可能代替创作,主体意识在一个作家那里,决不是抽象观念的同义语。还有,对想象力,灵感,“陌生化”也有误解,看不到客体的制约力。我们的小说很长时期缺乏飞腾的想象,缺乏汪洋姿肆,天马行空的奇想,至于“陌生化”这一新型的艺术思维方式,就更隔膜了。新时期一些作家以奇诡的想象,簇新的感觉,让读者在惊讶和出神之迷中刷新对生活的感受,有力地打破了小说刨作的闷局。有的作者借助梦境写出了好作品。但这并非柏拉图所谓的神灵附体,而是自有其情感记忆和情绪记忆的基础、头脑加工厂的复杂运作的。如果由此得出主观可以绝对和无限,可以完全脱离客体的结论,那就只能搞出些荒唐,杂乱,不知所云的东西。
另一种阻抑创作深化的情形是,作家的主体是对外来刺激和信息的被动接受器,他有个已经定型的认识图式和表现模式,不管现实生活如何变化,不管处理何种素材,他永远拿着那个模式来消化一切外来信息,于是,他的作品也永远是一种结构,一种色调,一种味道。这时常被誉为具有稳定风格,其实主体意识酣睡,创作日渐陈旧。
这两种偏颇,即主体吞噬客体和客体压抑主体的现象,虽然只是在一部分创作中表现出来,但它已成为小说创作向纵深发展的障碍。究竟应该怎样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主体意识问题呢?主体与客体之分,其实是人类走出蒙昧状态后的一种觉悟,但在实际上,主体是须臾也离不开客体的。作家的主体能力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对象化的创作活动,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对流过程。主体是主导的方面,它可以创造、建构客体,但同时客体对主体则有制约的一面。马克思说:“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不管多么超逸、奇诡的主体,也不能不借助感性的形式,情感的符号来重现自身,超越自身。所以,主体进入客体的深度决定着主体自身的深度。一个不肯开放,不肯借鉴,不肯吸收的主体,必然是日渐衰竭的主体。主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也就必然是个双向寻找的过程,即寻找自我和发现世界的过程。它们不能割裂,只能在紧紧相依,时时撞击中进行。一旦割裂了,偏畸了,创作就会出现失重和失衡。当然,不同时期倚重点不同,倒也是自然的事。
上面,由于论题本身对科学性,严密性的要求,弄得我不得不做些枯燥的推理,但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意思也是明显的,即作家和创作都需要不断调整。如果说,小说创作一度偏重于发现自我(这是很必要的),相对疏离了对象化世界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在小说创作中的情形也就是必然的。为什么近三年来小说总体上趋向于平实化和生活流呢?为什么原先刻意追求文化意味和哲理意味的作家,转而隐蔽过于外露的自我,更加尊重描写对象,甚至一任生活的自然流泻,而很少表露明确的价值判断呢?为什么很多作品是以原生形态和“困惑”的面目出现呢?这里是不准发现作家对其主体意识进行调节的努力的。那就是试图通过扩大真实的领域和直面生存状态来推动主体的深化。如果原来是侧重主观的观念化革新,那么现在是侧重客观昀生活化的征服。船,总是在一左一右摇橹中前进的。
二、典型境遇和典型状态
有位评论家曾经这样概括新时期小说文体的变化:“生活可以用故事来概括,但又不能仅仅用故事来概括;故事可以用人物来推动,但又不能仅仅用人物来推动;人物可以用行动来说明,但又不能仅仅用行动来说明”(周介人)。这样的概括当然是机智、简括而又思辨的,它用现象概括现象,既肯定了传统现实主义中的情节、人物、行动等要素,又指出这些要素也并非不可或缺。那么,推动这些变化的核心又是什么,他没有回答。我认为核心问题是小说中的典型问题。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在小说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至今也是不可能推倒的,但是,随着哲学、心理学、文化学对文学的渗透,随着现代主义内向化的影响,也随着各种文体“杂交”的成功,人们认识到,典型的内涵和形态是相当宽泛的,不必刻板守一。比如,心理小说中的典型可能是典型心理,诗化小说的典型可能是典型意象,散文化小说的典型可能是典型情绪等。事实上,这类越出规范的形态有些也是早已有之,不同的是,今天人们更加自觉,更多吸纳现代人的感悟,发展得更为繁富了。当然,作为小说的主体,特别是在中长篇小说里,创造深厚而又复杂的,森罗深刻社会历史内容的典型人物,仍然是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勘测一个时期文学深度的标尺。
这些问题其实已被反复讨论过了,无须多谈。重要的是,典型的祥相有如浮标,它往往反映出一个时期文学运动深层的流向和变化。这里,就有一种新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在近年来的一些小说中,作为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疏离,出现了从典型性格的创造转换到对典型境遇、典型状态的绘制。有些作品里已看不到围绕某个中心人物来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刻划了,有些作品的人物近乎符号或类型的代表,于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定义在悄悄地推衍,变异。有些小说,你分不清谁是主要人物,每个人都参与到对一种境遇和状态的经营之中;有些小说,主要人物倒很突出,但小说并不把他作为目的,而是让他去为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还有些小说,也写个性的差异,心理的冲突,但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氛围;氛围酿足了,小说也就结束了,看完后你不再记起人物,倒是那团氛围久久压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