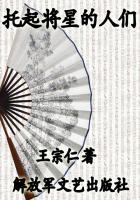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对中国历史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莫过于佛教的传人。而位于丝绸之路咽喉之地的敦煌,则随着佛教的传人,逐渐发展并兴盛起来,成为中古历史上的佛教圣地。
一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佛教是西汉末东汉初经西域由陆路传人中国的。但佛教初传时,似乎并未在敦煌驻足,这使得丝路咽喉之地的敦煌,在佛教的传播上稍异于中原。据《高僧传》记载,直到曹魏时期(244年前后),才有外国僧人竺高座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竺高座是目前所知最早在敦煌传播佛教的僧人。或许在此之前,敦煌就有其他像竺高座一样的僧人活动,但总的看来,佛教在敦煌的传播还是晚于中原内地的。
佛教在敦煌初传时,主要以译经、讲经为主,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竺法护为世居敦煌的月氏人,8岁时出家为僧,拜外国僧人竺高座为师,随师姓称竺昙摩罗刹,汉语称为竺法护。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其师竺高座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36国的语言和文字,并携带了大量的佛经东归。“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①。266年,竺法护到达长安,从事译经和传教工作。284年,竺法护回到敦煌,继续从事传播佛教的工作,在敦煌形成以他为中心的汉胡僧俗佛教集团。竺法护在传教的同时,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译经工作上,在其弟子竺法乘等30多人的帮助下将厨宾(今克什米尔)文士侯征若带到敦煌的梵文《修行道地经》译成汉文,接着又翻译了龟兹副使羌子侯带来的《不退转法轮经》②,另一部重要的佛经《正法华》也是法护于太康七年(286年)在敦煌翻译的。此后,法护又回到长安、洛阳等地,从事译经和传教工作,法护一生译出佛经154部,③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译经大师,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做出了贡献,故《高僧传》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④
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先随师在敦煌、长安笔录译文,后
①梁·慧皎:《高僧传》卷1《晋长安竺昙摩罗刹(竺法护)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58页—15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参阅梁·僧祐:《出三藏集记》卷2,《大正藏》第55卷。
④梁·慧皎:《高僧传》卷1《晋长安竺昙摩罗刹(竺法护)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①在敦煌的影响超过其师法护。法乘对敦煌佛教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修建寺院,使僧俗信徒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二是将佛教的传播对象扩大到一般民众,从而为敦煌后来成为佛教圣地奠定了基础。法乘所建为何寺,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来看,晋代敦煌确已建寺。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前室北壁题《莫高窟记》言“晋司空索靖(239年—303年)题壁,号‘仙岩寺’”,敦煌文献P.3720中的《莫高窟记》则是此窟《莫高窟记》的手写本,据此,该寺就在莫高窟,至五代犹存(P.2963尾题),仙岩寺在晋代情况如何,已难知其详,但它已成为莫高窟开凿的先声。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史称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的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直到北魏灭北凉后,敦煌才又重归北方统一政权之下。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河西地区相对稳定,大批中原人士流寓河西,遂使河西成为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而自西汉以来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开发,伴随着十六国时期中原士人及百姓的流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样一方面是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进步,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始终像阴影笼罩着河西一隅。经济文化的进步,是佛教在河西传播的基础,社会的动荡则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佛教虽以译经、讲经为主,但由于以苦修为内容的“禅定”思想在北方流行,促进了河西、敦煌石窟寺的开凿。
十六国时期的两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和昙无谶都对敦煌佛
①梁·慧皎:《高僧传》卷4《晋敦煌竺法乘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教产生过影响。鸠摩罗什(344年一413年)是龟兹(今新疆库车)人,早年深受小乘佛学的影响,青年时改宗大乘,尔后,主要从事弘扬大乘佛学的活动。他的弘扬活动,曾对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佛教产生过巨大影响。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派大将吕光率军进攻西域,次年,吕光进军龟兹,大破龟兹诸国联军,东归时,将高僧鸠摩罗什带到凉州。途经敦煌时,罗什留下了一个神奇的传说,至今还在敦煌一带流传。传说鸠摩罗什从龟兹去长安传播佛教,他骑的白马到敦煌后,突然病倒了,几天不吃草,也不饮水,罗什心中十分着急。有一天晚上,罗什梦见白马对他说,“我本上界龙驹,受佛主之命,驮你东传佛教。进关之前,因道路险阻,风沙迷漫,难辨方向,故由我伴你而行。现在已经进关,前面便是大道,敦煌是我超脱生死之地,我不能伴你而行了,望你前途珍重!”罗什苦苦哀求,希望白马继续伴他东行,白马见他情真意切,又说“前面不远便是葫芦谷,那里有你新的乘骑,你去吧!”说完,便化作一片彩霞冉冉升起。罗什一惊,从梦中醒来,这时随行的人进来告诉他,白马已经死了。罗什十分痛心,花费重金修建了一座白马塔。此塔至今仍耸立在敦煌沙州古城东南隅。①白马的传说和白马塔的修建,显然是后人为纪念鸠摩罗什而建造的,但也说明罗什对敦煌地区的佛教确实产生过影响。罗什在敦煌稍事停留后,便随吕光到达凉州,从事译经工作,后人长安,继续从事佛经的翻译,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将他和唐玄奘、义净,并称为古代的三大翻译家。
北凉时期的翻译家昙无谶也对敦煌佛教产生过影响。昙无
①参阅敦煌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敦煌简史》第47页,1990年。谶原为中印度僧人,后辗转经厨宾、龟兹、鄯善(今新疆若羌)来到敦煌,在这里熟悉了汉语。沮渠蒙逊灭西凉后,将他作为“圣人”接到姑臧(今甘肃武威),主持翻译了《大般涅槃经》等11部佛经。昙无谶早年学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改习大乘。他翻译的11部佛经,都属于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经。尤其是在《大般涅架经》中,进一步发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说,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这一新的提法,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大般涅槃经》译成后,在河西等地广为抄写流传,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六国时期,凉州是北方著名的译经中心,伴随河西的佛经传译,出现了“西天取经”热。敦煌地接西域,成为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西行求法者,既有河西僧人,又有中原、江南的僧人,东晋著名僧人法显就是从河西经敦煌到达西域的。由于凉州是北方的译经中心,中原、江南僧人也有至河西取经的,河西僧人也东去南下,对中原、江南的佛教产生影响。如北魏太武帝灭佛,至文成帝兴佛,其领导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师贤、昙曜等大多原为北凉僧人,他们对北朝佛教禅学及戒律方面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昙曜与现存大同云岗石窟的开凿与兴盛更是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十六国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佛教,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南北方政治、经济情况不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形成了南统与北统之分,南朝偏重佛教哲理争辩,北朝偏重宗教修行。①当时,北方主要流行以“禅定”为内容的修行方法。“禅”是梵语的译音,意译为“思维修”、“静虑”、“弃恶”等,“禅”又叫“定”,因此称为“禅定”,是佛教所谓“六度”之一,即六种修行方法之一。所谓“禅定”,就是先到佛像前仔细观察佛的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到僻静处(禅室),闭目静坐,抛弃一切私心杂念,苦思冥想,便能心眼见佛,获得悟解,修成正果。这种以“禅定”为内容的佛教修习活动,对河西佛教也产生了影响。前凉时期,敦煌就出现了修习禅定的高僧如单道开、竺昙猷等。北凉时期,就在译经大师昙无谶来到凉州的同时,“特深禅法”的厨宾僧人昙摩蜜多(法秀)也“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静”②。这些高僧的活动为讲求苦修的禅法的流行奠定了基础。“禅定”需要安静的环境,因此禅僧往往选择远离城乡的地方开窟建寺,作为修习场所。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一个叫乐傅的禅僧云游至敦煌鸣沙山一带,当他到达今莫高窟附近时,忽然看见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傅感到有些眩晕。作为禅僧的乐傅以为得到了佛的召示,于是他募人在莫高窟开了第一个石窟。乐傅开窟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禅师,从东边西行到乐傅所开石窟旁边又开了一窟。由乐傅、法良二人都是禅僧来看,莫高窟最早开凿的石窟可能就是专为他们修
①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梁·慧皎:《高僧传》卷3《昙摩蜜多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习禅定的禅窟。①由于年代久远,加之以后各朝代对前代建造的石窟不断进行改造,以及战争的破坏和风沙的侵蚀,乐傅和法良最早开凿的两个石窟已无法查考,整个十六国时期莫高窟开凿的数量也难以知晓。据今人研究,现存确知为十六国时期的洞窟大约有9个,它们的编号分别为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它们大多为北凉时期开凿的②。随着莫高窟的开凿,源于印度的佛教艺术也开始在这里扎根,并和中国本土的艺术相结合,创造出光辉灿烂的石窟艺术。
佛经的翻译和传播,寺院的兴建及石窟的开凿,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在北魏占据敦煌以前,敦煌的佛塔和佛寺已有不少。《魏书·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③。本世纪以来,在敦煌、酒泉等地先后发现12座北凉沮渠蒙逊、牧犍时期(428年一434年)的佛教造像石塔,这些造像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及反映的社会背景,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凉时期敦煌佛教发展的情况。④据敦煌文献S.797号记载,在西凉李暠迁都酒泉的第二年(406年)初,比丘德事占等12人在敦煌城南受具足戒,主持受戒仪式的有僧人法性、戒师宝意、教师惠观。一次受具足戒者有12人,可见当时出家人也为数不少。莫高窟藏经洞中出土的有纪年的佛经,时间在305年至442年问的就有10件,这也是十六国时期敦煌佛教发展的一
①参阅贺世哲:《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与禅观》第123页一128页,《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参阅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45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③参阅《魏书》卷114《释老志》。
④参阅殷光明:《北凉石塔述论》,《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第87页~107页。个证明。①
北魏灭北凉后,曾把很多河西僧人和佛教设施迁到平城,这对内地佛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影响了凉州及敦煌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灭佛事件,也影响了敦煌佛教的发展。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崇信道教的拓拔焘在道士寇谦之、崔浩等的怂恿下大规模灭佛,下令各地捣毁佛像,焚烧佛经,坑杀僧人,一时间,北魏境内佛塔寺庙几乎消失殆尽。这是佛教传人中国后受到的第一次空前规模的劫难,北魏统治下的敦煌,佛教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北魏初期,佛教在敦煌没有多大的发展。
494年至495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中原佛教再度兴盛,仅西域胡僧到达洛阳者多达3000,龙门石窟也开始了大规模兴建。中原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影响到敦煌。孝文帝时为都大将的穆亮,就十分信佛,他的夫人曾在洛阳参加龙门石窟的造像活动。北魏末年在敦煌的统治不稳,派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北魏灭亡后,元荣又继任西魏瓜州刺史。元荣本身非常信佛,他到任后,试图利用佛教巩固在敦煌的统治,于是大兴佛事。531年,他以银钱一千文施入寺院造经。532年,他出资造《无量寿经》100部,《维摩疏》100部,《内律》、《贤愚》、《摩诃衍》、《观佛三昧》、《大云》等经各1部。533年,又出资造《涅槊》、《贤愚》、《法华》等经100卷,这些佛经经文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有10余件。在出资大量写经的同时,元荣还出资在莫高窟修窟造像。在他的带动下,莫高窟掀起了继北凉之后的第二个造窟高潮。莫高窟现存北魏末年到西魏统治敦煌时期开凿的洞窟有10个,这些洞窟都与元荣有直接关
①参阅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第25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系,其中285窟,据专家研究,即是他亲自主持营造的大窟。①继东阳王元荣之后,北周时期的瓜州刺史建平公于义(在任时间约为565年—576年)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在任其间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窟造像活动。据敦煌研究院排年分期,有北周洞窟14个,最大者为428窟,该窟就是建平公于义所建之窟。且从其窟内供养人像多至1200多身的情况,我们也可看出北周敦煌佛教修窟造像活动之一斑。
574年,北周武帝下令废佛灭法,诏令也推行到敦煌地区,瓜州城东的阿育王寺和沙州城内的大乘寺都遭到毁灭。但这次灭佛对莫高窟影响不大,开窟造像活动一直在进行。②
北魏前期,北方仍以禅修思想为主,与这一思想相适应,莫高窟以中心塔柱为主的窟形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窟形。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北方佛教也开始注重对佛教经义的研读和宣讲,和这一变化相关,北周时期莫高窟禅窟已经不见,中心塔柱窟也大大减少,而殿堂窟逐渐成为主要窟形。这种窟内有较广阔的活动空间,便于信徒在这里举行礼拜及其他活动。所以北周时期窟形发生变化,透露出敦煌地区佛教的信仰方式逐渐由禅修变成单纯的供养礼拜。③
可见,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敦煌佛教一开始就受到西域和中原佛教的影响,这就为敦煌佛教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特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①参阅贺世哲:《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壁内容考释》,《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第375页一379页,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
②参阅施萍亭:《建平公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第144页—15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参阅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第42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二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频繁,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敦煌地区的佛教,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阶段。
隋代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南北佛学的统一。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北方佛学在注重禅修的同时,开始了对佛教义理的探讨。隋朝统一的政治局面,为南北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因而也促进了南北佛学的合流,对宗教修行和佛教义理的并重,成为隋代佛学发展的趋势。这种统一后的佛学,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也影响到敦煌。
隋代敦煌佛教的发展,得益于隋文帝父子的大力提倡。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十分信佛,奉佛教为国教,还制定了保护佛教的法律,规定对破坏佛像的人以“不道论”或“恶逆论”。文帝子炀帝杨广更是佞佛。在统治者的提倡下,隋朝佛教很快恢复到北周太武帝灭佛以前的盛况,敦煌佛教亦不例外。601年,隋文帝下令各州建舍利塔,派中使前往瓜州,在崇教寺(寺在莫高窟)起塔。一些隋宫廷成员的写经也流通至敦煌。如S.2514《佛说甚深大回向经》题记是:“大隋开皇九年(589年)四月八日,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流通供养。”s.4020《恩益经·卷第四》的题记是:“大隋开皇八年(588年)岁次戊申四月八日秦王妃崔为法界众生敬造杂阿含经五百卷,流通供养。”这一方面说明统治者对佛教的倡导已远及敦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敦煌在隋代佛教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隋代由于国家统一,丝绸之路畅通,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人、使者、僧人较前代大为增加。敦煌是通往西域的最后一个驿站,出了阳关、玉门关,便是茫茫戈壁大漠,通往西域的路上,随时可能遇到饥渴、迷路、抢劫……的威胁。离开敦煌前向佛寺布施,对于商人、使者、僧人来说,既是对平安的祈求,也是对勇气的鼓舞。莫高窟420窟窟顶东披壁画《观世音普门品》里,就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现实。画面上描绘了商人出发前的祈祷,灌饮骆驼,驼队的遇险,坠崖;货物的散失;强盗的劫掠,官吏的刁难等等,现实生活的内容以宗教题材反映在壁画上,真实地再现了丝路贸易的艰难,以及商旅们为保平安而对佛的祈求。①来往于敦煌的商人、使者,是敦煌佛教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隋代佛教的发展还表现在石窟的开凿大大超过了前代。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信教群众的不断增加,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开凿洞窟看作一项功德而参与其事,因此有隋一代短短的37年中,共新开洞窟110个,这个数量比现存莫高窟早期200年间所开洞窟的总数还多,开窟的速度在莫高窟开凿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石窟艺术也与隋代佛教发展相适应,呈现出上承北朝、下启盛唐的特点。
唐、五代是敦煌佛教鼎盛时期,保存至今的敦煌文献,以这一时期最为丰富,石窟的开凿,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文献记载和石窟开凿互为印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活生生的敦煌佛教画卷。
由于敦煌历史的特殊性,学术界一般把公元781年吐蕃占领敦煌,作为唐代敦煌历史前后期的分界线。唐代前期敦煌佛教的繁荣,是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力量的强大分不开的,同时,敦煌佛教受到来自内地及印度、西域佛教的影响,使敦煌佛教大放异彩。
①参阅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第52页一5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唐代前期,由于丝路的畅通,中印两国僧人也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中国的玄奘、义净、慧超等一大批僧人,不远万里,主要经由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习;印度僧人也纷至沓来,如玄宗时在长安创立佛教密宗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3名印度僧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玄奘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正是由于中印僧人的交往,使敦煌地区的佛教继续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
说到印度佛教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提及唐太宗时期的玄奘法师和外交活动家王玄策。玄奘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俗姓陈,名袆,今河南偃师人,13岁时随其兄出家,在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为了解决佛经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和译经真伪难辨的问题,玄奘决心去印度考察学习。629(贞观三年),他悄然离开长安,独自一人踏上西行之路,不久来到河西重镇凉州。当时由于唐朝初立,为了防止占据西域地区的突厥,在河西一带设防极严,百姓不能随意西行。玄奘到达凉州后,凉州都督李大亮下令他返回长安,玄奘在慧威法师的帮助下,星夜离开凉州,一路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经张掖、酒泉,到达瓜州(今安西县东双塔堡一带)。瓜州刺史独孤达是一个佛教徒,他当着玄奘之面撕毁了凉州都督下令捉拿玄奘的公文,帮助玄奘离开瓜州。玄奘离开瓜州,出玉门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印度。玄奘在印度遍访各地,饱览经书,钻研佛教各宗,学问大增。但是,玄奘身在印度,心却飞向故国,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到阔别17年的长安,路过敦煌时,唐太宗命官吏前往迎接。玄奘回到长安后的19年,共翻译佛经75部,1335卷。由其口授,弟子辨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成为今日研究中亚、印度历史的重要文献。玄奘新译的佛经,也很快传到敦煌,藏经洞中就发现了很多,其中仅《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写本就保存了1000多个卷号。安西榆林窟壁画“唐僧取经图”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
除玄奘大师外,贞观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还出过一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王玄策。从太宗贞观十七年至高宗龙朔三年(642年一663年),王玄策先后4次奉诏出使,往还于大唐帝国和印度摩伽陀王国之间。王玄策奉旨完成使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撰成《中天竺国纪行》一书,详细叙述了中天竺国的地理、地貌、山川、形胜、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社会风情等。《中天竺国纪行》一书问世后,很快受到公私学人的重视和利用,唐代知名画家杨廷光,以其所记内容绘成《西域记图》,画于长安昭成寺的障日之上。唐代晚期,其画影响及于敦煌莫高窟壁画。莫高窟出现的诸多佛教事迹故事画,极有可能就是其画的摹拟。①可惜的是,王玄策所著之书在宋代以后就遗失了,人们只能从其他书刊中对其钩稽、整理,但王玄策的活动及其影响并未因历史的推移而湮没。
唐前期敦煌佛教同时也受到中原内地的影响。首先,长安、洛阳的写经在敦煌流行,大云、灵图、龙兴、开元等奉敕修建的官寺的存在,使长安、洛阳两都新译的佛经也能很快传至敦煌,这在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中有充分的反映。其次,有不少高僧大德来到敦煌弘传佛法,如高僧昙旷就在敦煌居住19年,撰写了不少解释大乘佛教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累世苦修”才能成佛的说教,已经失去了作用,倡言无论贵贱贤愚,只要专心念佛,凡夫皆得脱离秽土,转生净土的净土宗等在中原流行的廉价成佛、快速成佛的佛教思想也流传到了敦煌。与此同时,中原寺院的壁画样稿也随同佛教经典和高
①参阅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17页一32页。僧来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保存了大批由内地传来的经变画粉本,如“弥勒下生经变”、“牢度叉斗圣变”,等等,成为画工创作的依据和参考,为敦煌艺术的辉煌,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印度、西域佛教及内地佛教的影响下,唐代前期敦煌佛教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寺院的数量大大增加,见于记载的就有龙兴、灵图、开元、大云、普光、金光明等寺;信教群众也更广泛地深入民间,各阶级、阶层都有佛教信徒。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和藏经洞写经题记看,唐前期出资开窟、写经的既有僧官、僧尼、男女居士,也有当地的达官贵人,文武官僚、工匠、行客、侍从、奴婢和一些善男信女等;唐代前期,河西、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不少官僚、士卒在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及西州、于阗等地服役,在西出阳关、玉门关前后,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也要向莫高窟布施、礼忏、祈祷,出资开窟造像,希望在佛祖的保佑下早日回还,与家人平安相见。唐代前期,统治者不时提高道教地位,但敦煌地区的佛教,由于群众的普遍信仰,始终向前发展。尤其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出于称帝需要抬高佛教地位,对敦煌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称武则天为了称帝,授意法朗、薛怀义等和尚于载初元年(689年)著《大云经疏》,说弥勒菩萨为化度众生变为女身,“作阎浮提主”,“以继王嗣”,“当王国土”,武则天称帝后,即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并将《大云经》送往各大云寺收藏。莫高窟北大像(即第96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的。P.3720《莫高窟记》载:“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四十尺”,北大像虽经后代重修,但仍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彩塑作品。《莫高窟记》还记载“开元年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南大像即在今莫高窟第130窟。南、北大像的修建,是莫高窟历史上的壮举,也是唐代前期敦煌乃至整个唐王朝繁荣、富强的象征。除南、北大像的营造外,唐代前期是敦煌莫高窟造窟最多的时代,现存洞窟140个,这些洞窟是敦煌佛教和佛教艺术全盛时期的缩影。
安史之乱后,唐大军东调,吐蕃势力趁机进入河西,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抗蕃斗争达10年之久的沙州军民,在得到吐蕃方面不将其迁往其他地区的承诺后,与吐蕃结盟而降,从此敦煌落人吐蕃之手达60余年。
吐蕃时期,沙州佛教势力空前发展。由于吐蕃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僧侣的地位很高,一些高僧甚至可以参预政事。如参预张议潮起义的高僧洪□,吐蕃时代就是“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张议潮之婿李明振的叔父僧妙牟,常在吐蕃赞普左右参与政事,兼“临坛供奉”。吐蕃时期,寺院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到吐蕃后期,只有25000人左右的沙州,寺院已发展到17所,僧尼人数已近千人,足见佛教势力之大。吐蕃时期佛教势力膨胀最突出的一点是寺院经济的发展,当时敦煌的寺院除了拥有田地、果园、粮仓、碾、油坊、牲畜、车辆等财产外,还拥有自己的依附人口——寺户,寺户承担的劳役,据s.542《戍年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口车牛役部》记载,约8大类,40余种。①
吐蕃统治时期,佛教仍受到中原内地佛教的影响。一是在吐蕃委派的掌管宗教事务的蕃都统主持下,组织专门的“译坊’、“经坊”,派人向唐朝求取佛经,进行翻译、印刷。二是延请俗讲僧到河西各汉族聚居区宣讲佛法。俗讲是唐、五代时
①参阅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84页~10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期流行于寺院,由俗讲僧向世俗大众通俗讲解佛经教义,并增加故事化成分,以宣传佛教为目的一种宗教说唱形式。它是由正式讲经转化而来,由于以阐述佛教哲理为主的讲经一般群众难以听懂,于是俗讲这种形式便应运而生。吐蕃统治者把俗讲僧请到河西讲经,就将俗讲形式传到了河西,它对敦煌佛教和敦煌文学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的兴盛,又对吐蕃文化产生了影响,摩诃衍在沙州陷落后,曾奉吐蕃赞普使命,从敦煌到逻娑(拉萨)传授汉地顿悟禅法。另一位敦煌高僧昙旷,曾回答赞普有关佛教顿渐之争的疑难问题。①
三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敦煌大族张议潮,趁吐蕃势力衰弱,唐中央政府准备收复河陇之际,联合当地各族起义,驱逐吐蕃守将,据有瓜、沙二州。接着,张氏扩充军队,且耕且战,又攻克东面肃、甘等州,大中五年(851年),唐设沙州归义军,授张议潮为节度使。从此,敦煌进入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统治敦煌地区近两个世纪。
由于敦煌在佛教传人后始终保持着常盛不衰,加上它不断从中原和西域两个方面汲取营养,这一时期,敦煌佛教已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同时,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又对中原和西域的佛教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如果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一角度去分析,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呈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①宁可、郝春文: 《敦煌的历史和文化》第77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吐蕃统治时期由中原传人敦煌的俗讲活动,晚唐以来逐渐兴盛起来。俗讲内容包括“押座文”、“解座文”、“讲经文”、“因缘”等,是通俗化地宣传佛教的一种形式。“押座文”是俗讲正式开讲之前转诵的一种诗篇,犹如宋元话本之开话诗词,近世弹词之“开篇”小段。押座之“押”与“压”字相同,所谓“押座”乃是一种安定听众,使其息虑收心、专致静听的手段。敦煌文献中的押座文有《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温室经讲唱押座文》、《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等等。解座文是俗讲结束后所诵之文,同押座文一样,多由七言诗组成,解座文分别保存于P.2305、P.3128、s.2440等卷号中。讲经文是俗讲的主要内容,是俗讲的底本,取材全部选自佛教经典。敦煌文献中现存的讲经底本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花经讲经文》、《维摩诘讲经文》、《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盂兰盆经讲经文》、《说三归五戒讲经文》等。因缘,又称说因缘,与俗讲同样是一种在斋会上由僧侣演出的宗教说唱活动,主要讲佛弟子或善男信女前世、今生因果报应的故事。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因缘作品有《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欢喜国王因缘》、《目连缘起》、《丑女缘起》、《四兽因缘》、《佛图澄和尚因缘记》、《隋净影寺沙门慧远和尚因缘记》、《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灵州和尚因缘记》等。其中如《丑女缘起》讲的是波斯匿王有一女因前世不敬佛而生得容貌极其丑陋,丑女长大后痛苦万分,遂焚香礼拜,虔诚奉佛,终于得到报应,容颜顿改,变成了一位美丽妩媚的女子。《欢喜国王缘》主要通过欢喜王与夫人有相生死悲欢的遭遇,宣扬万事皆有因果,人生苦空无常,只有皈依佛门,修行持戒,才能超拔浊世,得生天国。正是由于俗讲、说因缘等所讲唱的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群众,所以更容易为僧俗群众所接受,敦煌文献中大量俗讲文献的遗存,正说明晚唐五代以来敦煌俗讲的兴盛。①
还有与俗讲密切相关的说唱形式——变文,晚唐五代以来,其讲唱范围已由寺院走向民间,出现了许多世俗内容的作品,并且出现了敦煌本地自己创作的变文作品,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这些作品不仅成为中原佛教影响敦煌的历史见证,而且今天已成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中原佛教对敦煌佛教的影响,还需特别提及的是五代以来的五台山文殊信仰的传人。五台山被佛教徒认为是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之地,自北朝以来,五台山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开始兴盛起来,至唐代宗大历年间,宰相王缙于五台山建金阁寺,五台山佛教益盛,声名远扬。但五台山文殊信仰传人敦煌的时间要晚得多。从敦煌文献和其他有关材料来看,在后唐同光年间,五台山才开始成为西北诸民族巡礼、供养的对象。这一时期,随着沙州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重新沟通,有关歌咏五台山圣境的《五台山曲子》、《礼五台山偈》以及各种《五台山赞文》涌入敦煌,很快在这个佛教圣地流传开来,到节度使曹元忠统治时期(944年~974年)发展到高峰。除了“新样文殊”在敦煌雕版印行外,值得一提的是莫高窟第61窟的开凿。此窟以文殊菩萨为主尊,并利用整个后壁,绘制了一幅精细的五台山图。这幅图规模空前,总面积45平方米,是莫高窟现存最大的整幅壁画。图上山峦起伏,五台并峙。正中一峰最高,榜题“中台之顶”,两侧有“南台之顶”、“东台之顶”等4座高峰。五台山之间遍布大大小小的寺院和佛塔约六七十处,其中包括“大法华之寺”、“大佛光之寺”、“大福圣之寺”、
①参阅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第209页~23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大建安之寺”、“大清凉之寺”等16所大寺。中台则有雄伟的“万菩萨楼”和“大圣文殊真身殿”。画部下面还画了镇州(今河北正定)、太原城和五台县等城镇。描绘了其间千里江山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诸如朝山、送贡、行脚、商旅、刈草、饮畜、推磨、舂米,乃至桥梁、店房等,形象真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因此,61窟的《五台山图》不仅是一幅形象的历史地图,而且也是一幅精美的山水人物画,图中山高水远,林木扶疏,道路纵横,殿宇耸峙,云霭飘漾,瑞鸟飞鸣。正是这风景优美的佛教圣地,才吸引了无数佛教徒对它的顶礼膜拜,①亦成为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见证。
五代以来,像唐前期全国统一时那种以中央写经传送地方的文化传播形式已不可能,随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民俗佛教的发展,五台山文殊信仰也从中原传到敦煌。这不仅为敦煌的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同时它所宣扬的救世护民的思想,也影响着敦煌的社会。②
晚唐、五代、北宋初期,中原佛教对敦煌佛教的影响还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五代及宋初,经过敦煌前往印度求法巡礼的高僧,依然不绝于途。敦煌文献S.5981《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智严巡礼圣迹后记》,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临坛持律大德智严,途经敦煌,发愿“故往西天求请我佛遗法”。“智严回日,誓愿将此凡身,于五台山,供养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北京图书馆《敦煌劫余录续编》0002号《妙法莲花经》第2卷尾朱笔: “西天取经僧继从,乾德二年(964年)六月拜
①参阅《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第237页~23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参阅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47页。2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记。”北图收字4号《至道元年(995年)往西天取经僧道猷牒》是寄住于敦煌灵图寺僧人写给当时的归军义节度使曹延禄的。其次,敦煌不断向中原求乞本地已欠损的佛经。敦煌文献P.4962背保存了归义军建立后不久,敦煌佛教教团向中原王朝申请补赐欠损佛经的文稿。s.2140中保存了曹氏归义军初期的《沙州乞经状》。曹延禄时期,又曾向宋朝皇帝求得一部《金字藏》。实际上,敦煌佛教界从中原取回的经典,除了补缺外,还有佛经的注释和偈赞之类的典籍。第三,那些往来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断把中原僧人的佛教著述带到敦煌。如敦煌文献P.3023中保存的《妙法莲花经赞文》,就是北宋开宝寺和尚继从在开封所撰,在他西行求法路经敦煌时作为礼品献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西行求法的僧人有时还将西域取来的佛典留在敦煌,如S.3424背保存的《菩萨戒本》,就是曹氏归义军时期中原僧人志坚从西域取回的戒本抄本。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时期,西川(成都)佛教界与敦煌和西域佛教界的交流也十分密切。当时,四川通西域的道路,也是经过敦煌的。据北图冬号62字背《维摩诘所说经》题记,后周广顺八年(958年),去西天(印度)取经的西川善兴大寺院法主大师法宗,归途中曾在敦煌作短暂停留,将抄写的佛典《维摩诘所说经》献给曹元忠。在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不少依据“西川本”抄写的佛经。
由于这一时期敦煌佛教已形成自己独立的特点,而这一时期中原佛教自唐武宗灭佛后其势已衰,佛教典籍的流失在所难免。因此,在晚唐、北宋时,敦煌保存了不少在中原看不到的佛教典籍。张氏归义军时期,张议潮曾向中原王朝进献在敦煌流行的佛教典籍。在曹氏归义军时期,西行求法的僧人常把从敦煌搜求佛典作为目的之一,如北宋僧人惠銮因见中原流行的陀罗尼译著拙劣,就曾奉皇帝之命赴敦煌搜求较好的译本,在敦煌三界寺观音院抄写了优于中原译本的《大悲心陀罗尼》和《尊胜陀罗尼》。①
晚唐、五代、北宋初期,敦煌佛教既受到西域佛教的影响,又影响了西域佛教。佛教自传人敦煌后,一直保持着常盛不衰的势头。人唐以后,敦煌佛教经过吐蕃时期的推波助澜,又躲过了唐武宗时的会昌法难,使敦煌佛教处于河西领导地位。归义军政权建立后,河西的最高僧官都僧统即住锡沙州,维系着拥有数千僧众的庞大的佛教教团。因此,晚唐、五代以来,敦煌无疑代表了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最高水平。正由于此,敦煌地区的佛教也对西域产生着影响。今吐鲁番地区,9世纪末,西迁回鹘在这里建立了西州回鹘政权,并逐渐信仰佛教。10世纪,佛教在西州回鹘地区迅速发展,佛教典籍也被大量译成回鹘文。而西州回鹘所得到的汉文典籍,则主要来自敦煌。在英藏敦煌文献中,有一件因为背面绘有图画而被作为艺术品存放在英国博物馆中的卷子,该卷编号C11.00207,正面写有《乾德四年(966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功德记》,这件文书明确记载了沙州归义军首脑在请人抄写《佛名经》时,特别为西州回鹘抄写了一部,并派人送去,以补西州《大藏经》所欠《佛名经》,说明沙州官府十分了解西州经藏的情况,也透露出西州回鹘有过向沙州乞经的活动。《妙法莲花经玄赞》是唐代法相唯识学权威、玄奘弟子、慈恩大师窥基(632年~682年)的著作。在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写本中,也有一件《法华玄赞》的抄本(ch.1215r),抄写时代为9世纪至10世纪(Periode D),很可能是从敦煌传过去的。汉文本《法华玄赞》西传吐鲁番,对西州回鹘的佛教产生了直接影响。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发现的回鹘语佛典写本《法华玄
①参阅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第110页~111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赞》,就是根据汉文本《法华玄赞》翻译的。由此可见,五代以来,敦煌佛教对西州回鹘佛教的发展,的确做出了不小的贡献。①
敦煌佛教在对西域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西域佛教的影响,而以于阗佛教的影响最为典型。9世纪中叶,随着吐蕃在西域统治的衰落,处在吐蕃统治下的于阗,脱离吐蕃羁绊,重又独立,恢复了自汉代以来就在于阗当政的尉迟家族王统。于阗偏处塔里木盆地南沿,虽然已独立于吐蕃,并且早已脱离唐朝的羁縻统治,但其国王仍自称为唐之宗属,积极与中原王朝加紧联系,而处在河西的归义军政权,则成为于阗人心目中中原王朝的代表。从901年于阗使者首次来敦煌,到1006年于阗被黑韩(喀喇汗)王朝灭亡之前,于阗与敦煌的使节往来从未间断。
于阗是西域地区大乘佛教中心,在逗留敦煌的于阗使者中,有不少僧人。由于佛教在于阗被尊为国教,所以来到沙州的于阗太子、宰相和一般人员,也有不少是熟谙佛典的饱学之士。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于阗语佛典,有不少是相当完整的文献,它们大多是这些信士从于阗带来或在沙州写成的。藏经洞出土的于阗文佛典,现主要存放在英、法两国。英藏于阗文佛典现存于英国图书馆所属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其中编号为ch.00274《佛本生赞》、ch.I.00216《金刚乘文献》,就是完成于于阗而由张金山在982年出使沙州时带到敦煌的。另外,ch.002"75《金刚般若经》和ch.xlvi.0015《佛说无量寿宗要经》,也是保存完整的于阗语佛教文献。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于阗语佛典P.4099《文殊师利无我化身经》也是写于尉迟输罗
①参阅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377页一3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王在位时期(966年~976年)。P.3513佛教文献集,内容有《佛名经》、《般若心经疏》、《普贤行愿赞》、《金光明最胜王经·忏悔品》、《从德太子礼忏文》,是于阗国从德太子在敦煌期间写成的。从德太子是于阗王李圣天和曹议金女结婚后所生长子,儿童时期(935年前后)就被带到敦煌,966年奉命入宋朝贡。翌年,其父王晏驾,从德作为合法继承人,回于阗即位为王,即尉迟输罗,年号天尊。上述P.3513佛教文献就是从德太子935年至966年在敦煌写成的。而佛教文献《善财童子譬喻经》的于阗语写本(ch.00266,P.2025+P.4089a,P.2957,P.2896,P.2784,P.5536bis,丽字73号),其完成时间也当在同一时期。①10世纪的敦煌,除了长期居留和短期经过的于阗人外,还有不少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文人学士能够读懂于阒文,因此,大批于阗文佛典流入沙州,必然会影响到敦煌佛教。
于阗佛教对敦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佛教典籍流入沙州,而且随着于阗和敦煌联系的紧密,五代、宋初以来,大量有关于阗守护神的瑞像图开始出现在敦煌壁画中。唐、五代、宋初的于阗,关于佛教像法阶段即将过去,末法阶段即将到来的思想在这个佛教国家中广泛流行起来,加上内忧外患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开始企求神灵的护佑,特别是求助于佛典中所记载的于阗守护神们的佑持,这些神灵于是大量以瑞像形式出现。随着敦煌同于阒关系的加强,这些瑞像也传到敦煌,并出现在莫高窟壁画中。敦煌莫高窟瑞像图大多出现于晚唐、五代、宋初,尤以五代宋初曹氏掌权时为多。在瑞像中,释尊等神祗运
①参阅荣新江:《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第111页—119页;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第111页,上海书店1993年版。用神力飞来于阗的瑞像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在这一类瑞像中,牛头山以及与牛头山有关的瑞像占着中心位置。①牛头山在今新疆和田县城(伊里奇城)南偏西20余公里处,相传释迦牟尼自印度腾空而来牛头山结跏七日,牛头山遂成于阒佛教圣地。于阗瑞像在敦煌石窟中出现,不仅说明于阗和敦煌有长期紧密的联系,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于阗佛教对敦煌佛教的影响。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对敦煌佛教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位于丝绸之路咽喉之地的敦煌,其佛教才在西域及中原王朝的影响下开花结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敦煌佛教,成为中原汉化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代表。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无疑代表着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最高水平,成为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
①参阅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第212页一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