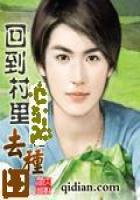第四章蓝色抱负
奉天就是繁华。满清没入关的时候,奉天是他们的都城,后来满洲人进了北京,又把这里当作了留都,由内大臣统辖东北事务。大帅张作霖早年曾投身绿林,其后又拉起了保安队,最后被清政府招安收编,从一个管带做到统带、统领、师长,最后做到东北巡阅使兼奉天督军、奉天省长,成了独霸一方的奉系首领。从满清到大帅直到现在的少帅,对奉天都是钟爱有加、优先发展,满清把它当做了后退一步的老巢,张家父子把它作为争夺中原的大本营,二百多年的苦心经营,使它成了东北的第一大城市,政治、经济的中心。直到去年,少帅张学良改弦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又把奉天改叫沈阳。
从家里走的时候,齐远山就带了很多钱,老爷子发话了,说啥也得让知节上大学。说句实话,齐家上下是真心帮他们,他们看重杨家,更看重知节,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心,谁都看得出,红月心里装的全是知节。送他们走的时候,红月的眼睛湿湿的,知节的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可是两个人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送他们的马车就要走了,红月才懦懦地说了句:“知节哥,别忘了给我婶写信。”说完话,两颗金豆子已经从眼睛里偷偷地滚落下来。知节心里清楚,其实她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给她写信,两个人虽然都没有向对方表白,可他们彼此的心里早已有了冥冥的默契,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能让对方心领神会。母亲和二叔也都盼着知节能上大学、有出息,可是母亲对齐家的帮助却有些犹豫,她并非不愿意接受,她只是想靠自己的劳动,给儿子创造一个上学、深造的机会,这样才会让自己更加心安理得;二叔、二婶却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遇,二叔告诉知节:“知节,你就安心的上大学念书,钱就算咱们借你大爷家的,这个家有我在你就放心,明年咱们多种点地,供你上学还不成问题。”知节心里却有自己的打算。
到了奉天,齐远山领着知节先去他姑姑家,他姑父在沈阳开了几家商号,是沈阳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两个表弟林南帮着父亲打理生意,林北在奉天省政府司法厅供职。大老远的亲侄子来了,老太太可高兴坏了,赶忙的吩咐厨房做几个好菜,问这个问那个,收成好不好、日子都咋样,半个下午谁都插不上话。吃饭的时候,远山提起知节的事,老爷子一听非常高兴:“远山,你们爷俩这事办的对,这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我也听说了,这个东北大学是大帅活着时候办的,在全国那都是数得上的。”林南接过来说:“听说张家爷俩最舍得往这里花钱,当初日本人笑话中国人办不成好学校,大帅跟日本人较劲,说了‘就是少养五万陆军,也得办好东北大学。’这学校条件那可是一流的,现在有三千多学生,请的教授有好几十个都是留洋回来的。”齐远山问:“学校离咱们这多远?”林北说:“东北大学有两个校区,南校区在大南关沈河那边,北校区就在咱们后边北陵这儿。我跟教育厅的厅长王永江认识,他原来就是东北大学的校长,明天我先领你们找他。”
三个人边说边走,刚走到太平寺北大街口,看见前边围了一帮人,仨人挤进去一问,是一辆拉菜的驴车刮了一个日本女人,也就是蹭了那么一下,和服的衣襟弄上了一些土还有点大葱的绿浆。赶车的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汉,跟日本女人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有一个穿着和服,腰里挎着一把东洋刀,说话叽里呱啦,也就能听懂一半,看出来就是个日本人,还有一个穿西服的,说话倒是挺溜,看不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穿和服这个拦着驴车不让老人走:“这个的,坏了。那个的,坏了……”连说带比划,说了半天也说不明白。那个女人看样子不会说中国话,跟穿西服的说了半天,大伙问穿西服这位:“这俩日本人说的啥呀?”西服说:“这个女人说没事,回去洗洗就好了,那个叫西村四郎的不干,非要让老人赔钱。”大伙说:“你问他要赔多少钱哪?”西服回头跟这个四郎一问,这小子叽里呱啦地伸出十个手指头,大伙说:“他要十个铜钱啊?”西服眼睛一瞪:“啥?十个铜钱。他要的是十个银元。”老人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大爷,你行行好跟他说说,我一个乡下人,哪来的那么多钱,这一车菜再加上这头驴也值不上十个大洋啊。”西服嘴一撇:“日本人说话谁敢反驳?要说你自己说吧。”大伙都说:“这不他妈讹人吗?啥衣服值他妈十个大洋。”西服又他妈一撇嘴:“你知道啥呀,这衣服是九州上等的真丝做的,给你十个大洋你也买不来。”这个西村四郎哇哩哇啦一个劲地比划,日本女人不停地劝着。齐远山有点气不忿,拨开人群进去跟西服说:“你跟那个什么四郎说,别他妈在这撒野,衣服又没坏,要那么多钱不是讹人吗,我给他一个大洋,找地方把衣服洗洗得了。”林北上去劝他:“大哥,咱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不知道,日本人在咱们这儿横行霸道,老百姓没少吃他们亏,别说是咱们,就连少帅都不敢得罪他们。”旁边有人说:“可不是,那铁道线都是日本人的,到跟前看看都他妈不让。”另一个接着说:“别说铁道线,就连过铁道的桥都他妈不让过,前几天我那表侄打那桥上过,生生让小日本用刺刀给挑了。唉!那叫一个惨呐。”西服跟日本人嘀咕了半天,回头跟齐远山说:“西村说了,这衣服是外务省次长的夫人赠的,少一块都不行。”齐远山一听更加来气,冲着西服说:“我不管他什么省什么长的,谁赠的不就是件衣服吗,钱是有,不是他妈白给的。你跟那小日本说,就给一块大洋,要不行他妈一个都没有。”大伙也跟着说:“上奉天来讹中国人,真他妈骑到脖子上来了,不能便宜了东洋鬼子。”西服回头跟小鬼子一说,这小子当时眼睛就瞪起来了,也不知道哇啦两句什么,噌一下就把东洋刀抽出来了。不少人吓得撒丫子就跑,齐远山告诉老爷子:“大叔,你赶紧赶车走,这事就交给我。”老爷子说:“这哪儿行啊,咋也不能连累你们那。”大伙都说老人:“你在这能管啥用啊,有人管你就快点走吧。”老人赶车一走,小日本更急眼了,举起东洋刀就冲着齐远山劈过来,林北急得直喊:“大哥,小心!”知节一看,火儿腾一下就起来了,上去拽住小日本就抢他手里的东洋刀,也就刚搭住手,小日本一翻腕抓住知节小臂,一撤步、一发力,把知节踉跄着摔出两米多远。大伙一看,这小日本是个练过的,弄不好俩人就得吃亏,旁边几个年轻人噌噌就蹿上去,拽胳膊的拽胳膊、抱腰的抱腰,把小日本的东洋刀抢下来,按到地下一顿胖揍。大伙正揍的来劲,有人喊:“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众人哄的一下跑了个干净。
跑出去一条巷子,林北就跑不动了,他喘着粗气说:“咱们站下吧,没事了。”齐远山说:“你没听警察还吹哨呢。”林北说:“那是吹给日本人看的。”接着又说:“你们俩倒是出气了,说不上又给谁找麻烦了,这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齐远山说:“看你也跑累了,要不咱们坐黄包车去吧。”知节说:“大爷,咱们别去了,我不想上学了。”齐远山一愣:“咋了?”知节说:“大爷,在家时候我就想好了,或者上学或者找事做或者投军,哪条路适合我我就走哪条路,有没有出息不在做什么,关键在怎么做。本来我还没下定决心,今天看见日本人在咱们地盘上这么放肆、这么撒野,真是欺负到咱们家门上来了。陈二虎一次次找上门我都能忍,那只是我们俩的事,小日本欺负咱们我绝不能忍,这是两个民族的事。”齐远山说:“小日本欺负咱们我也看不惯,可就连少帅都不敢管,咱们老百姓能有啥办法?你年纪小,还是上学要紧。”知节说:“大爷,我也知道,就凭我一个人斗不过小日本,但是要有一千个一万个像我一样的人,大伙都抱成团,小日本就没啥可怕的。”林北说:“这孩子说的有道理,小日本这么猖狂就因为咱们中国人太熊了,又不团结,就知道自己窝里斗。”齐远山说:“这事是不是回去跟你妈还有你二叔商量商量?”知节说:“没事,我妈和我二叔他们知道也会支持我的。”林北说:“你们不知道,这当兵也不是谁想去就去的,得有地方的证明才行。”齐远山说:“那咱们就先回去,写个证明拿来。”林北接过来说:“你们要回去开证明还得浪费时间,这样吧,上我那去,我给你们出个证明。”
北大营就在城外三四里地,差不多一个屯子那么大,里边是东西向的三溜平房,跟老百姓那些青砖红瓦的平房不同,这是三溜铁皮盖的房子。围墙又高又厚,上边还有铁丝网,四个转角各有一个望楼,大铁门紧紧地关着,塔楼的枪洞里隐约露出机枪的枪口。角门两侧各有一个拿着枪的哨兵,齐远山和知节走到门口,一个哨兵过来问他们:“老乡,你们找谁?”齐远山拿出林北开的证明:“我找你们的长官,我侄子想当兵,这是奉天省司法厅开的证明。”哨兵说:“你们先在这等一会,我进去通报一声。”不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位个头不算太高的军官,头戴蓝灰色大沿帽,一身蓝灰色的军服,身材略有点胖,但是精神头十足。出来就问:“是哪一个要当兵啊?”齐远山赶紧过去,把林北开的证明递过去,说:“是我侄子要当兵,这是我表弟司法厅林北给开的证明。”军官看了一眼,说:“林北,听说过。你们进来吧。”进到里边,军官自我介绍说:“我叫王铁汉,620团团长,今天我们旅长不在,本来不敢做主,看你们是林北介绍来的,我想旅长知道了也不会怪罪,我就帮他收下了。”里边一位军官插话说:“听说太平寺那边出事了,有两个人把小日本给打了,就是一个大个的中年人和一个小伙子。”王团长上下打量着两个人,笑着问:“不会是你们吧?”知节说:“不瞒王团长,就是我们。”王团长哈哈大笑:“是个汉子,解气!这样的兵才是我要的兵,收下了。”里边那个军官说:“王团长,日本人挨了打能善罢甘休吗?现在警察正满大街找人呢,把他放咱们这儿不行,要是有人知道了管咱们要人,咱们也抖搂不清。我看要不这样,一会儿咱们这儿有车上新民,你给李团长捎个话儿,让他上独立团得了。”王团长笑了:“不愧是参谋,就是鬼点子多,日本人想找也找不着。”回头跟两个人说:“那就上新民独立团吧。”
出新民西门不远就是独立团驻地,有前后两个营盘,前边驻扎的是团部、一营、工兵连、骑兵连、炮连,后边是二营和三营。东北军最精锐的就是驻扎北大营的第七旅,有三个团七八千兵力,每个团都配备12挺重机枪、6门迫击炮还有4门平射炮,每个连配备120只德国步枪,每个班都有一挺轻机枪,还有12辆德国FT—17坦克。谁想到九一八那一夜,六百多关东军如入无人之境,一道不抵抗的命令让多少壮士成了禽兽刺刀下的冤魂,一个旅的精良装备拱手送给了日本人。独立团虽然比不上第七旅,可也是少帅张学良的嫡系心腹,是少帅亲手组建起来的,曾跟随少帅南征北战,在东北军那也有响当当的名号。知节他们到的时候天儿还没黑,押车的军官把他送到团部,团长李东海听说是王铁汉团长送来的兵,看样子很高兴,跟押车的军官说:“回去告诉王团长,这个兵我收下了。”回头吩咐:“通讯员,领他去后大营,交给三营长郑三河。”
郑三河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浓眉毛、大眼睛,脸略有点黑,说话瓮声瓮气,到了三营,正赶上开饭,郑营长爽朗地笑着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算你们有口福,王干事今天出去打了几只山鸡,你俩就在这儿吃吧。”回头招呼警卫员:“三铁子,去把二连长韩远给我叫来。”不一会儿,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进来一个白白净净的军官,个头儿不高,圆脸,小眼睛。进门就笑了:“我听说王干事打回山鸡来了,这把我馋的,差不点没上厨房偷去,这回不用了。”郑营长笑了:“你小子他妈借好人光了,你以为没事我会请你呀。”回头给他介绍:“这个是新来的兵,叫杨知节,吃完饭把他安排到你们连。”韩连长一个敬礼:“是!”回头笑嘻嘻地说:“不管借谁光,能吃着山鸡才是真格的。”
吃完饭,韩连长带知节领了军装、行李,又带他进了一个宿舍。宿舍里有十四五个人,有的歪在那儿歇着,有的坐一块儿神侃,屋里挂着一盏马灯,缭绕的烟雾几乎看不见人,一股刺鼻的旱烟味迎面而来,。看见连长进来,中间铺上站起来一个人,啪一个敬礼:“报告连长!二连一班正在休息,没有人缺席。”其他人都赶紧站起来、敬礼,就门口一个人叼着旱烟袋,倚在行李上没动。韩连长给大家介绍:“这是你们班的新战士,叫杨知节。营长说了,现在没有新兵集训,你们平常训练的时候多教教他。”班长又一个敬礼:“是!”韩连长回头跟知节说:“这个就是你们班长,朱希文。”知节赶紧跟班长还有大伙打了招呼。
连长一走,朱班长看着知节的行李,自言自语地说:“你住哪儿呢?”知节赶忙说:“班长,我住哪儿都行。”里边有人说:“让他挨着谢老兵。”朱班长眼睛里诡谲地一笑:“我看行。”回头拿过知节的行李,放到门口叼着烟袋那个人的下面,说:“那你就先住这儿吧。”回头招呼其他人:“下面的都把行李动弹动弹,紧紧铺,给杨兄弟倒个地方。”谢老兵这回坐起来了,吐了一大口烟雾,懒懒地说:“让他住我这儿,我往下住一位。”朱班长又闪了一丝诡笑:“谢老兵,你不挨王大脚了。”谢老兵也没吱声,把行李卷起来挪到下面,这样,知节就住在第二铺,把门口的就是朱班长说的王大脚。借着昏暗的灯光,知节看了看他即将开始生活的环境,整个屋子有两间大小,进门是一张桌子,上边放着三个暖瓶和一溜杯子,南北各是一溜板铺,屋子中间是一张大桌子,整齐地摆着一圈书、本,墙上贴满了条幅和宣传画,最里边靠墙整齐地摆着一溜枪。他也留神看了看即将生活在一起的战友,特别是挨着自己这两位,王大脚真是长着一双超人的大脚,大个、大眼睛、长脸、长腿,看着就是个憨厚的人;谢老兵是个胖乎乎的中等个,看样子有四五十岁,窄窄的脑门,脖子有点短,有点象肿了一样的鹅蛋脸,一双鼓鼓的黑鱼眼,从知节进来就没看见他嘴里离开烟袋。朱班长是个刀条脸,尖尖的下巴,一双三角眼,正和几个人品着烟卷,还有几个人叼着旱烟筒子,七八张嘴、七八双鼻孔不时地冒出一缕一缕的烟雾。
外边当当当敲了几声像是镐头一样的铁器,里边铺有人喊:“张大海,起来起来,打水了。”朱班长说:“杨兄弟,以后你也每天跟着打水去。”回头跟里边说:“马武,以后你就不用去了。”张大海穿上衣服从里边拿出几个脸盆,递给知节两个,王大脚拎上暖瓶、水桶。知节和王大海一人端了两盆热水,王大脚一个人左手拎了三个暖瓶、右手拎了一桶凉水。回到宿舍,他们几个又把水兑好,给人家端到跟前,大伙洗完了脚,又是他们三个一桶一桶地倒脏水。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朱班长发话了:“肃静,都别说话了,有没有没回来的。”里边有人回答:“没有,都回来了。”朱班长说:“熄灯,睡觉。”刚说完,外边传来一阵悠长的号声。
知节这一天除了走路就是坐车,感觉胳膊、腿都酸酸的,可是他睡不着,第一次单独的离开家、离开母亲,就这样开始了一种陌生的生活,他有些兴奋,军营是男子汉的天地,有血性的男人才配得起扛枪、上战场。他知道,做一个军人,就要经历生与死的考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做一个有血性的军人,闯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为了家、为了恨、为了爱。他想到了红月,她那份浓浓的爱意,还有那热辣而又含羞的眼神,无时无刻不让他魂牵梦绕,为了这份真挚的爱,他要拼搏、要努力,他绝不会让心爱的人伤心、失望。
屋里有俩人在那小声地嘀咕着,朱班长说:“别说了,早点睡吧。”里边有人说:“哎,今天咋没听着大脚打呼噜呢?”又一个人说:“大脚不打呼噜你还睡不着啊?”王大脚翻了个身,说:“杨兄弟第一天来,我怕他睡不着,没敢睡。”有人吃吃地笑。知节说:“没事,你睡吧,我不怕呼噜。”又有几个人跟着吃吃地笑了。这句话起了作用,一会儿的工夫,王大脚那边就有了动静,开始声儿还不大,呼呼地抽了一小阵儿,翻了个身,吧嗒几下嘴,没了动静,其实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半睡状态。又过了一小会儿,呼噜声起来了,这次的呼噜好像没有了任何顾虑,从开始就那么慷慨奔放,呼……呼……呼……每一个呼噜都那么洪亮而又绵长,似乎还有固定的节奏,每个呼噜的结尾都有一个长长的停顿,好像在积聚着下一次的能量。下边的谢老兵也及时的发起配合,他不是打呼噜,是哼哼,每次先长长地抽一口气,停住,然后连续地哼哼出来,但是音量跟王大脚那就差远了。不一会儿,王大脚进入第二种模式,先是长长地、长长地呼……了一声,然后一个急刹车、停住,一点动静都没有,似乎是呼吸已经就此停止,让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好一会儿,才声嘶力竭地发出啊……的一个长声,实际已经远远超越了呼噜的范畴,那完全就是在喊。家里边爷爷、父亲和二叔从来都是文睡,知节从没见过这种武装睡法,真不愧是军队、军人。就这样,在一左一右两位哼哈二将的伴奏下,直到天儿都快亮了,知节才算勉强地进入了梦乡。
朦胧中听到一阵号声,大伙争先恐后地爬起来,急急忙忙地整理行李、洗脸,朱班长不时地催:“动作快点、动作快点。”还不时地提醒:“今天在后操场,训练队列队形。”王大脚快速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一边整理还一边教着知节:“杨兄弟,你看看,就这样叠。”一看知节还是叠的不行,又赶紧过来帮他。又一阵号声响起,紧接着东一个西一个响起口哨声,大家鱼贯着站成两队,跑步进入了操场。知节仔细地观察,他们连是光着手出来的,一个排站了一个方队,练的就是班长说的队列队形,另外还训练器械和体操;有的连是拿着枪出来的,练的是刺杀和射击;还有的连背着枪、背着行李,看样子是要到野外进行训练。韩连长过来把知节和朱班长叫了过去,韩连长对知节说:“杨兄弟,部队每天早晨都要早起训练,是要吃很多苦的,你能不能受得住啊?”知节学着别人敬了一个礼,说:“报告连长!没问题,我来参军就是准备吃苦的。”韩连长回头又跟朱班长说:“朱班长,杨兄弟是新来的,部队的规矩你都跟他说说,训练的时候你们都帮着指导指导。”
吃完早饭,大家都回到宿舍,朱班长跟知节说:“杨兄弟,念过书没有。”知节说:“念了七年私塾。”朱班长三角眼一挑:“哎呀!那应该算是中学生了,这可是咱们这儿的高草啊,这么多墨水咋还来当兵啊?”陈东山在里边转出来,眯着小眼睛,拍了拍知节的肩膀,说:“你们知道啥呀,咱们杨兄弟可不是来当兵的,是来当官的。哎,杨兄弟,赶明儿当了大官可别忘了咱们这帮兄弟。”知节笑了笑,没说什么,可是知节对这个陈东山有一种从心里往外的膈应,这小子长的倒是白白净净,可是眼睛里总有那种让人非常不得劲的奸诈和狡黠,说话还总是阴阳怪气。朱班长拿过来几本书,说:“你自己认字那就好说了,省得还得用人教你。这是咱们新兵必须学的几本书,有空你就自己看看吧。”回头又说:“马武,你这几天领着杨兄弟前后转转,认识认识咱们军营。”马武赶紧过来,说:“杨兄弟,我先领你去看看咱们这些营房。”马武是个中等个,圆脸、大眼睛,不怎么爱说话,看上去就很面善,他着领知节把整个大营转了一圈,挨个的告诉知节哪儿是营部、连部,哪儿是伙房、仓库,哪儿是厕所、宿舍,平时站岗都在哪儿设明哨、在哪儿设暗哨、在哪儿走流动哨,又跟他说了些队伍里的规矩,知节都一一地记下了。
开饭的时间到了,中午是二米饭、大豆腐,一人两个二大碗,一个碗盛菜,一个碗盛饭,知节还真是觉得有点饿了,早晨训练了一个多小时,又跟马武转了整个一个上午,吃完一碗感觉就像刚垫了个底儿,他拿着碗又去盛饭,那边陈东山和几个人看着他偷偷地笑,知节也不知道他们笑的是啥,到那一看才知道,两个饭盆里都没了饭,而且干净的连底都没剩下,他根本不明白咋回事,以为是伙房这顿饭做的少了?也没敢多问,只好回来吃剩下的豆腐,陈东山、刘四水他们几个还是偷偷地笑。没想到晚饭又是中午情景的重演,当他吃完第一碗饭又去盛的时候,饭盆里早已经是干干净净,陈东山他们几个又是偷偷地看着他,在底下吃吃地笑。回来一看,大伙碗里都有饭,正在那儿大口地、津津有味地吃着,知节小声地问王大脚:“王哥,今天饭咋这么少呢?”王大脚说:“不少啊,哪顿饭都是这些。”抬头一看知节手里端着空饭碗,王大脚急忙说:“杨兄弟,你就盛着一碗饭吧,你要是不嫌乎把我饭给你拨点。”知节赶忙说:“不用了王哥,我吃饱了。”第二天早晨吃馒头,菠菜豆腐汤,知节想起了昨天的事,赶紧用筷子串回来三个馒头,心里想,这次总不会挨饿了,还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可是吃完了一看,案子上的馒头还有剩的,这真让他有点摸不着个头脑。可是一到中午和晚上吃饭,他就算加快速度吃,结果也是每顿都吃不着第二碗。这天,马武又找知节出去转转,马武问知节:“杨兄弟,是不是这几天你都没吃饱饭哪?”知节说:“马哥,这几天我正想跟你说呢,每天早晨都能吃饱,就是中午饭和晚饭吃不饱,也不知道咋回事,等我吃完第一碗再去盛饭就没有了。”马武说:“就因为你不知道我才想告诉你的,部队规定不许浪费,宁可不够吃也不许剩饭,所以伙房每顿饭都不会做太多。大伙吃饭的时候都有窍门,吃第一碗饭不但要吃得快,而且不能盛满,盛的太满就会浪费时间,等到盛第二碗就得盛的越满越好。你刚来不懂这里的窍门,所以就盛不着第二碗饭,陈东山他们天天看你笑话,还不让大伙告诉你,你知道了就行,别说我告诉你的。”知节一下子恍然大悟,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中的数学,任凭知节这么聪明却不会变换,只有实践经验丰富才会把它算的精准。
要不说中国人的奸诈、狡猾闻名于世界,从抗日战争时期汉奸、伪军的数量就能看出来,有的说是两百多万,有的说是三百多万,还有的说是四五百万,咱们就说有两三百万,其数量也足以让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民族望尘莫及。1945年小日本投降那时候缴械的人数才120多万,可是给日本人卖命的孙子、狗比他们爷爷、主子还多两三倍,你说日本人还用自己动手吗?九几年我们学校有个老工友(已故去),每次值班时候我都愿意跟他唠嗑,他跟我说,日本人进巴彦县城那年,住的就是他们家西院的一个大财主家,第一天进城的能有三四十个日本兵,有骑马的、有走着的,扛着枪在巴彦大街小巷一转,吓得老百姓都不敢出屋。第二天早晨,从城外大摇大摆又进来二三十个;第三天早晨,又进来二三十个。连续七八天都这样,老百姓一算得有二三百,更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老头告诉我,其实是日本人耍了个障眼法,总共就他妈第一天来那三四十个,后几天进来那些都是半夜偷偷出去的,日本人住那院中国人不让进,一般人不知道根底。一人传话、百人传讹,老百姓却是越传越玄乎。老头跟我说,就这事以前都不让乱说,要是跟人家书本上说的不一样那就坏了,最轻的也得批斗你两三年,搞不好就是个***。就这三四十个鬼子统治了巴彦十几年,巴彦县几十万中国同胞,都用不着枪炮,一人吐一口吐沫都能把这些鬼子淹死,但是巴彦人没这么做,以多欺少那显得咱们中国人多不厚道,反倒有成千上万的孙子给小日本做事、当兵、当警察。可怜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就连日本人长啥样都没看见几回,就让这些汉奸、卖国贼坏了性命。
有人认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种族的天性,这我不敢苟同,什么叫天性,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本性,难道在几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跟欧美人的祖先会是不一样的猿猴?扯淡!也有人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的,这里我有同感,你看看我们上至王公下至庶民、两千多年推崇备至的《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再看看我们的三十六计,有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无中生有、顺手牵羊、偷梁换柱、浑水摸鱼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在告诉我们什么?从这里我们会学到什么?两千多年的实践告诉人们,取‘诡道’者,得其势、得其利;取‘正道’者,亡其势、亡其利。这样的权衡,结果可想而知。亏他蒋公介石还进过保定陆军学堂、日本振武军校,案头还经常摆着《孙子兵法》,却完全没有领会孙子的‘诡道’,四百三十多万军队,八年抗战让他糟蹋的就剩了二百八十多万。再看我们的伟大领袖,既没有进过军校,也没有整天的研究兵法,长征结束陕北红军剩下三四万人,南方游击队还有个一两万人,可老人家用的却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此十六字真言与孙子的‘诡道’何其相近,甚至就是现代的‘诡道’。八年的‘诡道’,使八路军、新四军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到一百八十多万人。从这儿其实就已经看出了两位总经理的差距,可是蒋公就是不服气,非要支巴支巴,结果成了独守孤岛的千古流寇,搞得华夏骨肉至今不能团圆。其实小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就应该成立联合政府,还提什么他妈政治分歧、文化分歧,你看看六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岸有啥本质区别吗?谁走在谁的后面了?都是一样的面子,只是里子不一样罢了,都是糊弄老百姓的事,为了那点主义竟让几万万同胞血流成河,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想当年我就是没赶上,要是有我在就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们摆开,亲兄弟打架谁他妈不看热闹,关人家外人啥事?明明不是什么道理,非要没理辩三分,最后谁便宜了?黎民百姓多受了四五年的战火蹂躏,有多少青壮男儿为两位老总赴汤蹈火,又有多少城池、古迹毁于那场硝烟,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五年,可是这场战争规模之宏大、争夺之惨烈都可以排在世界战争史的前列,就算八年抗战两家也没下那么大力气。当其时就应该刀枪入库、联合执政,暂由蒋公做总统,毛公为议长,周公为总理,我想两党的制约程度要远比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更会有效。真要是这样,中国现在应该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知节看得出来,王大脚、张大海、马武都是老实厚道的人,陈东山那些人经常欺负他们,扫地、打水、倒脏水桶,这些零碎的活都是他们几个干,陈东山、刘四水他们整天围着班长,不是抽烟就是喝酒,你想想,班长肯定偏向着人家几个。知节看不惯他们那种谄媚的嘴脸,还有那种奸伪的假笑,有两次陈东山叫他一块出去喝酒,知节一口就回绝了。说句实话,对那些奸佞小人,你真不能给他好脸,给他脸他就往你鼻子上抓挠,小人与君子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修养,这种东西小人是永远也学不来的,就算偶尔装个一两次看着反倒恶心,我从来就不怕得罪小人,生活本来就很累,我没有闲心经管、搭理那些小人,要是受到小人的疏远、指责,我会更加心安理得,如果有个君子指出我哪怕一毫的缺点,我都会战战兢兢,把自己从里到外翻过来,仔细地检查三天。知节没事就愿意跟几个老实人在一块,几天下来,班里的这些人基本上都认识了,部队的情况也了解个差不多。独立团是少帅张学良一手拉起来的部队,就是当年卫队旅的老底子,团长李东海多少年就跟着少帅,打了无数的大仗、恶仗,立功的小本本摞起来得有一尺高,是从一个小兵一路摸爬滚打才到当上这个团长的。一营和骑兵连那是团长的心尖,骑兵连人人都是双枪一刀,一营差不多都是德国步枪,轻重机枪也比二、三营多,就连伙食都比二、三营强。三营装备虽然差点,但是满编满员,他们班加上知节总共15个人,郑营长和谢老兵当年都是跟李团长一块进的卫队旅,郑三河那也是一员猛将,大大小小也立了无数的战功,就是书念得少,做事还一根筋。最值得一提的是谢老兵,他从小就没了爹妈,除了队伍上认识的这些人,再也没啥亲戚朋友,谢老兵是个机枪手,打起仗来不要命,第二次直奉大战的时候,他们一个排阻击吴佩孚一个营,打了九个多小时,敌人都没前进一步,最后打得就剩下他们两个人,等到增援的部队上来,把敌人都打退了,谢老兵还瞪着眼睛在那端着机枪突突,大伙把他拉下来一看,机枪前半截都红了,一颗子弹从他胳膊穿过去他都不知道。按功劳他早就应该混个营长、团长的,可他这人一个大字不识,看见酒还没命,喝完酒就得闹出点事来,立一次功就得闹两出事。他自己也不愿意当官,退伍还没个地方去,他自己说了,这辈子就跟他们张家爷们混了,给他一挺机枪就行,可是有一样,别说连长、排长,就是营长、团长也得高看他一眼,但是,别看他平时吊儿郎当的,可是出操、训练哪样他都不落后。
到独立团已经十来天了,知节往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母亲和二叔,一封给齐远山,刚来那几天就想写信,因为还没有完全熟悉环境,写完了也怕说不清楚。他每天都在想着家人,母亲一定特别的记挂他,这一年多,突遇天灾、祖父离去、二慧子失踪、父亲病逝,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不知给母亲添了多少痛苦与悲伤,自己本来应该守在母亲的身边,可他深深地懂得,这样的乱世,隐迹村野几乎就等于任人宰割,那样就更不是母亲所愿意看到的,母亲、二叔和二婶一定还在忙碌着,为了这个家、为了自己,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他也想杨跃和玉兰,杨跃一定每天都背着书包去上学,放学回来还要赶着他那群小鹅,玉兰欢快地跟在后面,她一定每次都要下河去抓鱼,而且每次都是差一点就抓到。还有红月,她一定还会每天都去找玉兰玩,她现在最盼望的应该就是自己的消息。
知节是个新兵,每天都要增加训练时间,这是营长交待过的,知节也愿意多练练,他也想尽快赶上那些老兵。每天出完早操,知节都要吃点‘小灶’,每次单独训练,都是朱班长做教官,这小子故意使坏道,他根本不按人体承受力安排训练时间,也不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安排训练进度。有一次练习引体向上,本来这个动作的训练应该是逐渐加量,而且训练周期应该是十到二十天才可以考核,练到第三天,朱班长就要求知节一次做满30个,说句实话,知节练了两天就已经能做20多个,已经是很快的进度了,做30个实际就是在难为人,其实心里最明白的应该是朱班长,知节试了几次都没做满。按理说这时候就应该下杠休息一阵然后再练,可是朱班长不让知节下杠,非得让知节连续做。那天正是个大热天,知节浑身那汗就像下雨似的,眼前一阵阵发黑,可他硬是不告饶,就那么咬着牙坚持。每次训练朱班长都这么故意刁难,知节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后来马武告诉知节是因为没给他送礼。
部队除了训练也没什么事,一个星期还有一天休息,勤快点的都在这天洗洗衣服、行李。这个休息日正好是个大晴天,张大海、李铁和马武忙活着打水准备洗衣服,知节也想把衣服洗洗,就跟着他们打水、泡衣服。每次有人洗衣服都给班长带着,今天班长把衣服给了李铁,张大海问谢老兵:“老兵,有没有衣服拿来我给你洗。”谢老兵乐了:“我这衣服,一年洗一回就行,谁像你们年轻人成天洗,我呀,有酒就行。”王大脚手大脚大,拿枪、扔手榴弹都行,就是不会洗衣服,知节问他:“王哥,把你衣服拿来我给你洗洗。”大脚有点不好意思:“每回都是你们给我洗,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李铁打趣地说:“知节给你洗衣服,你把呼噜打轻点就行了。”大脚更不好意思了,边拿衣服边说:“杨兄弟是个干净人,还有文化,挨着我算是遭了罪了,我真恨不得把自个堵上,可就是说啥都控制不住。”马武说:“知节,晚上你预备个辣椒,他要一张嘴啊啊的你就给他抹上。”知节乐了:“刚来那几天好几宿都没睡好,这些天好多了,他打他的,我睡我的。”陈东山眯着小眼睛过来了,拿两件衣服,笑嘻嘻地跟马武说:“马兄弟,我衣服埋汰了,帮我洗洗呗。”马武有点不愿意,犹豫了一下说:“那就拿来吧。”刘四水在铺上起来,翻出两件衣服,大大咧咧地说:“哎!马武,把我衣服也给我洗了。”马武也没回头、也没吱声,刘四水有点不高兴,骂骂咧咧地:“马武,我跟你说话**没听着啊?”马武站起来,擦擦手说:“没工夫。”刘四水有点挂不住:“咋的马武,给他妈别人洗就不给我洗,你看我来气咋的?”马武今天也有点火了:“就看你来气,咋的?”朱班长站起来说:“四水,吵吵啥,你自个衣服自个洗得了。”刘四水却好像满身是理,从里边出来说:“不是他妈洗不洗衣服的事,这小子他妈看人下菜碟儿。”马武也脖子粗脸红:“**嘴干净点,平日欺负人欺负惯了,整天给你们打水、洗衣服,今天我就不伺候你你能咋的?”刘四水没想到马武这么老实的人今天还会急眼,把他顶的实在没了面子,跳着脚骂:“**的马武,我他妈今天非得收拾收拾你。”说着话就要伸手。马武也没服他那个劲:“你以为我怕你呀,**过来。”大伙赶紧把俩人拉开。看着就算没事了,陈东山在里边说:“马武你也是的,不就洗两件衣服吗,都是一个班的哥们,至于他妈急皮酸脸的吗?”知节一听这话不是味,接过来说:“陈东山,别他妈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这事都在这儿摆着呢,马武哪儿不对了?你是不是有点欺负人欺负惯了?”刘四水噌一下站起来:“杨知节,你个新兵蛋子,哪儿有你说话的份,找收拾是不是?”陈东山也撸胳膊挽袖子:“**的,收拾他。”朱班长假惺惺地劝:“有话好好说,别打仗。”实际上他已经让开了身子,意思就是让他们上。王大脚一看急眼了:“咋的,欺负人是不是?谁敢动我杨兄弟先他妈问问我王大脚。”张大海也急了,一脚把水盆子踢了个底朝天:“对,也他妈算我一个。”这俩小子一看马上就熊了,哪儿还敢吱一声。朱班长赶紧和稀泥:“都是自己兄弟,打啥仗打仗,散了散了,自己忙自己的。”知节说:“朱班长,咱们班的事你最清楚了,他们欺负人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人再老实也不能往泥里踩吧!既然这样了,有个事咱们今天必须说道说道。”朱班长说:“啥事,你说吧。”知节说:“咱们宿舍里扫地、打水这些事不能总一个人干吧?我们几个整天像奴才似的干活,最后还没捞到一个好,反倒像我们应该似的,从今天起我们不干了,有活大伙轮着干。”朱班长笑嘻嘻地:“应该,应该。”回头跟大家说:“杨兄弟说得对,从今天起咱们轮着值日。”
<ahref=http://www.*****.c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