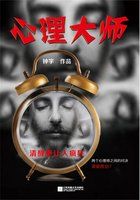然而,各处涌流的泉水,使人联想起女乳的温暖和丰足,这种女性般的温暖与丰足,正是伊豆的生命。尽管田地极少,但这里有合作村,有无税町,有山珍海味,有饱享黑潮和日光馈赠、呈现着麦青肤色的温淑的女子。铁路只有热海线和修善寺线,而且只通到伊豆的人口。在丹那线和伊豆环行线建成之前,这里的交通很是不便。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的公共汽车。走在伊豆的旅途上,随时可以听到马车的笛韵和江湖艺人的歌唱。
主干道随着海滨和河畔延伸。有的由热海通向伊东,有的由下田通向东海岸,有的沿西海岸绵延开去,有的顺着狩野川畔直上天城山,再沿着海津川和逆川南下……温泉就散缀在这些公路的两旁。此外,由箱根到热海的山道,猫越的松崎道,由修善寺通向伊东的山道,所有这些山道,也都把伊豆当成了旅途中的乐园和画廊。
伊豆半岛西起骏河湾,东至相模湾,南北约五十九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三十六公里,面积约四百零六平方公里,占静冈县的五分之一。面积虽小,但海岸线比起骏河、远江两地的总和还长。火山重叠,地形复杂,致使伊豆的风物极富于变化。
现在,人们都这么说,伊豆的长津吕是全日本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整个半岛就像一个大花园。然而在奈良时代,这里却是可怕的流放地。到源赖朝举兵时,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幕府末期,曾一度有外国黑船侵入。这里的史迹不可胜数,其中有范赖、赖家遭受禁闭的修善寺,有掘越御所的遗址,有北条早云的韭山城等。
请不要忘记,自古以来,伊豆在日本造船史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正因为伊豆是大海和森林的故乡啊。
无知的快乐林德(爱尔兰)
林德(1879~1949),爱尔兰散文家。出生于贝尔法斯特,就学于女王学院,后去伦敦生活。曾多年担任《新闻年鉴》的文学编辑,并以笔名“YY”给《新政治家》周刊撰写散文。他在恢复查尔斯·兰姆风格的散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英国散文界颇有影响。较着名的散文集有《无知的乐趣》、《蓝色的狮子》、《我战栗地想》、《生活中可爱的怪东西》等。
陪伴一个普通市民在乡间走路——尤其或许正赶在四五月间——对他什么都不知道的巨大范围无论如何不可能不感到万分惊讶。就是自个儿在乡间散步,对自己知之甚少的巨大范围也不可能不感到难以置信。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生生死死一辈子,竟会不知道山毛榉和榆树有何不同之处,听不出是画眉在欢叫还是乌鸦在歌唱。兴许,在一座现代城市里,能够听出画眉鸣叫或者乌鸦欢唱的人就是凤毛麟角了。问题不是由于我们不曾见过这些鸟儿。问题只是由于我们没有注意过它们。我们一辈子被鸟儿们包围着,可是我们熟视无睹,视有若无,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分辨不出是不是苍头燕雀在叫唤,或者说不出布谷鸟长得什么颜色。
对于布谷鸟总是一边飞一边唱还是有时落在枝头上唱,我们如同小孩子一样争论不休——同样搞不清楚查普曼是凭借想象还是知识写出了下面的诗行:
布谷鸟在橡树绿色枝条间唱起,正是人们在明媚的春天沐浴时。
然而,这种无知现象倒也不全是痛苦。由于无知,我们才获得了不断发现的快乐。如果我们真的相当无知,那么每到春天我们就会领略到自然的每一处气息,窥见露珠儿还在上面驻足。如果我们活了大半辈子还不曾见过布谷鸟,只把它当作空中回荡的声音,那么我们看到它在树间飞来飞去时那种惊飞样子更加津津有味,认识到它会酿出祸害,并且欣喜地看到它同鹰一样凌空翱翔,长长的尾巴瑟瑟抖动,然后贸然落在山脚的杉树上,也许种种伺机反扑的天敌正潜伏在什么地方。不能不说,博物学家观察鸟儿的生活一定会得到许多乐趣,但是与一个人清早起来第一次看见一只布谷鸟,发现世界充满新奇,兴致油然而生,两者相比之下,博物学家的乐趣只是一种见怪不怪的乐趣,差不多就是一种清醒而吃力的职业罢了。
说到这点,连博物学家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他的无知,这种无知留给他新的世界去征服。在这类书本中,他也许对知识的细端末节都了如指掌,但是只要他还没亲眼见证一下每种截然不同的东西,那他仍会觉得只是知道了一半。他一心想亲眼看看那只雌布谷鸟——实在难得一见啊!——把蛋下在地上,用嘴衔到窝里,最终在窝里酿成杀害幼鸟的现象。博物学家会日复一日坐在地头用望远镜观察,亲自肯定或打破盛传的说法,即布谷鸟确实把蛋下在地上,而不是窝里。如果他吉星高照,在布谷鸟下蛋时发现了这一鸟类最难得一见的行为,那他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搞清的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多不胜数,例如布谷鸟的蛋是不是与它弃掉的窝里的别的鸟蛋总是一种颜色。可以肯定,从事科学的人没有理由为他们失去无知而伤心流泪。如果他们看样子无所不知,那只是因为你我知之甚少而已。在他们翻出来的每一个事实下面,总会有一笔无知的财富在等待他们。塞壬向尤利西斯究竟唱了支什么歌,他们永远不会比托马斯·布朗爵士知道得更多。
如果我借助布谷鸟说明一般人的无知,这并不是因为我对这种鸟儿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这仅仅是因为在非洲一个好像所有的布谷鸟都闯进来的教区里度过一个春天,我认识到我对它们了解得少而又少,我所遇到的人也无不如此。但是,你我的无知还不仅仅局限于布谷鸟。我们的无知关系到所有上帝创造的事物,上至太阳和月亮,下至百花的名字。一次,我听见一个聪明的女士打问新月是不是总在一周的同一天升起。她还说也许不知道更好,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在天空的什么地方能等到月亮,那么月亮的露面迟早都是一种令人快活的惊喜。
但是,我估计新月即使对那些深谙其升落时间的人,它挂在天空也同样会令人惊奇。春天的到来与花潮的到来,也无不如此。我们看见一枚早到的报春花会欣喜不已,是由于我们对一年寒来暑往习以为常,知道迎春花应在三四月间而非十月间开放。我们还知道,苹果树的花开在果子之前而非之后,但是我们在五月的果园度过一个美好节日时并不会因为只见花不见果而减少欣喜。
同时,每逢大地回春,重温许多花卉的名字也许会有一份特殊的快活。这好比重读一本几乎忘掉的书。蒙田告诉我们,他是忘事佬儿,重读一本好书时总感觉是过去压根儿没有读过的存书。我自己的记忆也靠不住,跟筛子差不多。我读《哈姆莱特》和《匹克威克外传》,总觉得它们是新作家的作品,从印刷厂出来还油墨未干,它们的许多内容在一次阅读和另一次阅读之间会变得模糊不清。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记忆是一种苦恼,尤其你一心想把事情记得准确无误的话。不过这种情形只是在生活追求目标而非娱乐时才会有的。仅仅就贪图奢侈而论,坏记忆会夸夸其谈的东西倒不见得会比好记忆少多少。你要是有个坏记忆,不妨一遍又一遍阅读普鲁塔克和《一千零一夜》,读上一辈子。许多细端末节也许会粘在最坏的记忆里,正像羊群一只接一只挤过篱笆的空隙,树刺上不能不挂住几缕羊毛一样。但是,羊群本身挤过去了,伟大的作家挤过无所事事的记忆如同羊群穿过篱笆,留下的东西少而又少。
如果我们能把书忘记了,那么把月份以及月份过去后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忘掉也是很容易的。这会儿我跟自己说,我了解五月如同乘法表一样清楚,关于五月的花卉、花开的样子以及品级也不怕别人考一考。今天我敢肯定毛茛有五个花瓣(也许是六个花瓣?反正上周我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明年也许我就算不清花瓣有多少,不得不再温习一遍,当心别把毛茛与白屈菜搞混了。到那时,我会用一双陌生人的眼睛,再次把世界看作花园,对那五彩缤纷的田野惊讶得透不过气来。我会情不自禁地纳闷儿是科学还是无知,认定雨燕(那种黑色的鸟,比燕子大,与蜂鸟同属一类)从不在窝里栖息,而是在夜里消逝在高空。我会带着崭新的惊奇了解到,唱歌的是雄布谷鸟,而非雌布谷鸟。我还不得不再次了解清楚,别把剪秋罗叫成老鹳草,重新按树类的规矩弄明白白蜡树出叶早还是出叶晚。有一回,一个外国人问一名当代英国小说家,英格兰最重要的庄稼是什么,他连想都没想就回答说:“黑麦。”无知到这种程度,我倒觉得达到了卓越不凡的地步;不过,就是无知的人的无知也一样深不可测。平常人拿起电话就打,却说不清电话的工作原理。他认为电话就是电话,火车就是火车,莱诺铸排机就是莱诺铸排机,飞机就是飞机,如同我们的祖先把《福音书》里的神迹当作神迹一样。
他用不着发问,也不必理解。仿佛我们每个人做过调查,只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事实组成的小圈子。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识在多数人眼里只是装点门面的玩意儿。可是我们不断在我们的无知面前作出反应。我们时不时醒过劲儿来,进行推测。我们乐此不疲地遇事就进行推测——推测死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推测那些据说连亚里士多德都解不开的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午间到午夜打喷嚏是好事,而夜间到午间打喷嚏就倒霉”。人类知道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在寻求知识过程中这样飞跃到无知状态之中。说到底,无知的巨大乐趣是寻根问底的乐趣。谁要是失去了这种乐趣或者把这种乐趣换成教条的乐趣,即回答的乐趣,那他就已经开始僵化了。谁都会对周伊特这样一个凡事爱问为什么的人肃然起敬,此公年届花甲才坐下来学习哲学。我们大多数人远不到这个年龄便丧失了我们无知的感觉。我们甚至会为我们松鼠储粮般的知识洋洋自得,把岁数增长本身当作一门大学识。我们忘了苏格拉底之所以智慧留名,不是因为他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认识到他活到古稀之年仍然一无所知。
论宽容福斯特(英)
福斯特(1879~1970),生于伦敦,是20世纪英国着名的作家,其作品包括六部小说、两集短篇小说集、几部传记和一些评论文章。
福斯特的作品语风清新淡雅,虽然人物的个性很容易被把握,但命运安排往往令人不可预测却又铺叙自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莫利斯》和《霍华德庄园》都被成功地搬上银幕,使福斯特的作品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重建。我们的敌人在规划以其秘密警察来维持欧洲的新秩序,为此提出了各种方案,而我们这边在谈论重建伦敦,重建英格兰,甚至重建整个西方文明,并且对如何达成目标作出了设想。这一切真是不错,可是当我听到这类谈论,看到建筑师削尖铅笔,承包商搞出预算,政治家划分出势力范围,每个人都开始为此各尽其力时,不由想起了一句名言:“除非上帝想要使房建成,否则建房人只能是白费力气。”这句话有涛一般的意境,然而却隐含着铁一样的科学真理。它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拥有健全的心态和正确的心理,否则不可能建成或者重建任何能够长久存在的事物。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不仅适用于基督徒,而且适用于所有建设者,无论他持有怎样的世界观。我们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托恩必博士在他的《文明盛衰史》中将此话作为卷首语,其中自有深意。毋庸置疑,一个文明唯一可靠的基础就是健全的精神状态。建筑师、承包商、国际经纪人、营销委员会和广播公司仅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新世界,那真是痴人说梦。他们必须被一种适当的精神所激励,而他们所为之工作的人们也要拥有这种适当的精神。比如说,有朝一日人们会拒绝住在丑陋的房子里,而在此之前我们不会拥有一个美丽的伦敦。现在的人们并不在意丑陋,他们要求舒适,但不关心城市的美化,因为他们的确还不具备审美能力。我自己就住在一幢奇丑无比的单元楼里,可我并不因为它的丑陋而觉得烦恼。不等到大家都为此而感到烦恼的那一天,所有想要重建一个美丽伦敦的规划注定都要失败。
不过到底什么是适当的精神呢?我们可以达成下面几点共识:问题的根源在于心理状态;只有上帝参与,建设才能保持长久;先要拥有一种健全的精神,然后外交、经济学和贸易会谈才能起作用。不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是健全的呢?
在这一点上我们产生了分歧。假如问,重建文明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素质,大多数人会说,我们需要的是“爱”。照这种说法,人们要彼此相爱,国家亦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制止正在对我们产生毁灭性威胁的一系列灾难。
对持以上观点的人们我表示敬意,却不敢苟同。在个人事务中,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事物;但是在公共事务中,爱却于事无补。它曾屡次尝试过:先有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其后的法国大革命又从世俗的角度重申了人类的亲情。然而,爱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徒劳。想让国与国之间相爱,想让商业财团或者营销商们相爱,想让一个葡萄牙人爱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秘鲁人,这种想法不仅荒谬、虚妄,而且有害。它使我们陷入迷茫而危险的多愁善感之中。“我们所需要的是爱!”我们这么唱着,唱过了就算完事,任由世界照老样子延续下去。事实在于一个人只可能爱他自己所认识和了解的那些有限的人和事。在公共事务中,在文明的重建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不像爱那样戏剧化、感情化的东西,那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很乏味的美德。它让人厌烦,它比不上爱,向来没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它是被动的,它只是要求你去容忍别人,去忍受别的事物。从未有人想到要为宽容写赞歌,或者为它塑像。然而,宽容正是战后我们所需要的品质,正是我们所寻求的健全的精神状态。只有依靠它的力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才有可能聚在一起为重建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