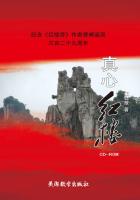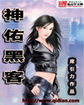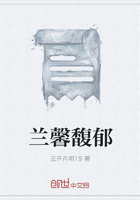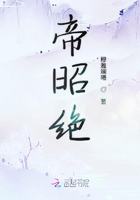和朋友们相约雅集的那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桑葚的芬芳飘荡在泥土之上,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竹林漏到溪水边,使弯曲的流水变成一条斑驳的花蛇。光线晶莹通透,饱含水汁。落花在风中出没,在光影中流畅地迂回,那份缠绵,看着让人心软。所有的刀光剑影都被隐去了,岁月被这缕阳光抹上一层淡金的光泽。唯有此时,人才能沉下来,呼应着自然的启发,想些更玄远的事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从这文字里,我们看到王羲之焦灼的表情终于松弛下来。我们看见了他的侧脸,被蝉翼般细腻和透明的阳光包围着,那样柔和。他忽然间沉默了,他的沉默里有一种长久的力量。
在那一刻,谢安、孙绰、谢万、庾蕴、孙统、郗昙、许询、支遁、李充、袁峤之、徐丰之一干人等,正忙着饮酒和赋诗,他们吟出的诗句,也大抵与眼前的景象相关。其中,谢安诗云: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物景,微风扇轻航。醇醪陶元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
孙绰诗云: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婴羽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望着眼前的灿烂美景,王羲之在想些关于短暂与永久的话题,也快乐,也忧伤。儒家学说有一个最薄弱、最柔软的地方,就是它过于关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协调人的关系,而缺少宇宙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它所建构的家国伦理把一代代的中国士人推进官场,却缺少提供对于存在问题的深刻解答,这一缺失,直到宋明理学时代才得到弥补。而在宦海中沉浮的王羲之,内心始终缺了一角,此时,面对天地自然,面对更加深邃的时空,他对生命有了超越功利的思考,他心灵中缺失的一角,仿佛得到了弥补,那份快乐自不必说,对于渡尽劫波的王羲之来说,这份快乐,他自会在内心里妥帖收藏;而他的忧伤,则是缘于这份“乐”,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人的生命,犹如这暮春里的落花,无论怎样灿烂,转眼之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花朵还有重新开放的时候,仿佛一场永无止境的轮回,在春风又起的时候,接续它们的前世。所以那花,是值得羡慕的。但是,每当春蚕贪婪地吸吮桑叶上黏稠甜美的汁液,开始一段即将启程的路途,眼前这些活生生的人们,可能都已不在人世了。一如我们今日重返兰亭,看得见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唯有永和九年那一班名人雅士去向不明。我们摸得到阳光,却摸不到他们曾经真实的身体。
王羲之特立独行,对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包括官场的进退、得失、荣辱,但有一个问题他却不能不在乎,那就是死亡。死亡是对生命最大的限制,它使生命变成一种暂时的现象,像一滴露、一朵花。它用黑暗的手斩断了每个人的去路。在这个限制面前,王羲之潇洒不起来,魏晋名士的潇洒,也未必是真的潇洒,是麻醉、逃避,甚至失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不见得比王羲之想得深入。
所以,当参加聚会的人们准备为那一天吟诵的S7首诗汇集成一册《兰亭集》,推荐主人王羲之为之作序时,王羲之趁着酒兴,用鼠须笔和蚕茧纸一气呵成《兰亭序》。全文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文字开始时还是明媚的,是被阳光和山风洗濯的通透,是呼朋唤友、无事一身轻的轻松,但写着写着,调子却陡然一变,文字变得沉痛起来,真是一个醉酒忘情之人,笑着笑着,就失声痛哭起来。那是因为对生命的追问到了深处,便是悲观。这种悲观,不再是对社稷江山的忧患,而是一种与生俱来、又无法摆脱的孤独。《兰亭序》寥寥S24字,却把一个东晋文人的复杂心境一层一层地剥给我们看。于是,乐成了悲,美丽作成了凄凉。实际上,庄严繁华的背后,是永远的凄凉。打动人心的,是美,更是这份凄凉。
四
由此可以想见,唐太宗之喜爱《兰亭序》,不仅因其在书法史的演变中,创造了一种俊逸、雄健、流美的新行书体,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赵孟頫称《兰亭序》是“新体之祖”,认为“右军手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欧阳询《用笔论》说:“至于尽妙穷神,作笵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个而已。”),也不仅因为其文字精湛,天、地、人水乳交融(《古文观止》只收录了6篇魏晋六朝文章,《兰亭序》就是其中之一),更因为它写出了这份绝美背后的凄凉。我想起扬之水评价生于会稽的元代词人王沂孙的话,在此也颇为适用:“他有本领写出一种凄艳的美丽,他更有本领写出这美丽的消亡。这才是生命的本质,这才是令人长久感动的命运的无常。它小到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它大到由无数生命个体组成的大千世界。他又能用委曲、吞咽、沉郁的思笔,把感伤与凄凉雕琢得玲珑剔透。他影响于读者的有时竟不是同样的感伤,而是对感伤的欣赏。因为他把悲哀美化了,变成了艺术。”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迷恋权力的人,玄武门之变,他是踩着哥哥李建城的尸首当上皇帝的,但他知道,所有的权力,所有的荣华,所有的功业,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他真正的对手,不是现实中的哪一个人,而是死亡,是时间,如海德格尔所说:“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作为这种可能性,死亡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悬临。”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则说:“死亡是行为的停止,是具有表达性的运动的停止,是被具有表达性的运动所包裹、被它们所掩盖的生理学运动或进程的停止。”他把死亡归结为停止,但在我看来,死亡不仅仅是停止,它的本质是终结,是否定,是虚无。
虚无令唐太宗不寒而栗,死亡将使他失去他业已得到的一切,《兰亭序》写道:“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句一定令他怵然心惊。他看到了美丽之后的凄凉,会有一种绝望攫取他的心,于是他想抓住点什么。他给取经归来的玄奘以隆重的礼遇,又资助玄奘的译经事业,从而为中国的佛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无法判断唐太宗的行为中有多少信仰的成分,但可以见证他为抗衡人生的虚无所做的一份努力,以大悲挥洒自然是一个不可不觑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它道出了人生的大悲慨,触及了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就是存在与虚无的问题。在这一诘问面前,帝王像所有人一样不能逃脱,甚至于,地位愈高、功绩愈大,这一诘问,就愈发紧追不舍。
从这个意义上说,《兰亭序》之于唐太宗,就不仅仅是一幅书法作品,而成为一个对话者。这样的对话者,他在朝廷上是找不到的。所以,他只能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这张字纸上。在它的上面,墨迹尚浓,酒气未散,甚至于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的阳光味道还弥留在上面,所有这一切的信息,似乎让唐太宗隔着200多年的时空,听得到王羲之的窃窃私语。王羲之的悲伤,与他悲伤中疾徐有致的笔调,引发了唐太宗,以及所有后来者无比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唐太宗宁愿把它当作一种“正在进行时”,也就是说,每当唐太宗面对《兰亭序》的时候,都仿佛面对一个心灵的“现场”,让他置身于永和九年的时光中,东晋文人的洒脱与放浪,就在他的身边发生,他伸手就能够触摸到他们的臂膀。
另一方面,它又是“过去时”的,它不再是“现场”,它只是“指示”
(denote)了过去,而不是“再现”(represent)了过去,这张纸从王羲之手里传递到唐太宗的手里,时间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它所承载的时光已经消逝,而他手里的这张纸,只不过是时光的残渣、一个关于“往昔”的抽象剪影、一种纸质的“遗址”,甚至不难发现,王羲之笔画的流动,与时间之河的流动有着相同的韵律,不知是时间带走了他,还是他带走了时间。此时,唐太宗已不是参与者,而只是观看者,在守望中,与转瞬即逝的时间之流对峙着。
《兰亭序》是一个“矛盾体”(paradox),而人本身,不正是这样的“矛盾体”吗?--对人来说,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出世与入世、迷失与顿悟,在生命中不是同时发生,就是交替出现,总之它们相互为伴,像连体婴儿一样难解难分,不离不弃。
都难免有感而发。但唐太宗不同的是,他能动用手里的权力,巧取豪夺,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从辩才和尚手里骗得了《兰亭序》的真迹,唐代何延之《兰亭记》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从此,“置之座侧,朝夕观览”。还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临摹,分赐给皇太子和大公大臣。唐太宗时代的书法家们有幸目睹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份真迹也不再仅仅是王氏后人的私家收藏,而第一次进入了公共阅读的视野。这样的复制,使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一次在世间“发表”,只不过那时的印制设备,是书法家们用于描摹的笔。唐太宗对它的巧取豪夺,是王羲之的不幸,也是王羲之的大幸。而那些临摹之作,也终于跨过了l000多年的时光,出现在故宫午门的展览中。其中,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摹本是虞世南的摹本,以白麻纸张书写,笔画多有明显勾笔、填凑、描补痕迹;最精美的摹本,是冯承素摹本,卷首因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半玺印,而被称为“神龙本”,此本准确地再现了王羲之遒媚多姿、神清骨秀的书法风神,将许多“破锋”“断笔”“贼毫”等,都摹写得生动细致,一丝不苟。
而王羲之《兰亭序》的真迹,据说则被唐太宗带到了坟墓里,或许,这是他在人世间最后的不舍。临死前,他对儿子李治说:“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他对儿子最后的要求,就是让儿子在他死后,将真本《兰亭序》殉葬在他的陵墓里。李治答应了他的要求,从此“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或许,这张茧纸,为他增添了几许面对死亡的勇气,为死后那个黑暗世界,博得几许光彩,或许在那一刻,他知道了自己在虚无中想抓住的东西是什么--唯有永恒的美,能够使他从生命的有限性中突围,从死亡带来的巨大幻灭感中解脱出来。赫伯特·曼纽什说:“一切艺术基本上也是对’死亡‘这一现实的否定。事实证明,最伟大的艺术恰恰是那些对’死‘之现实说出一个否定性的’不‘字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