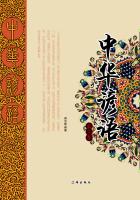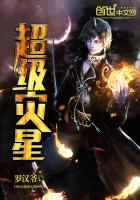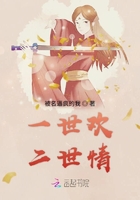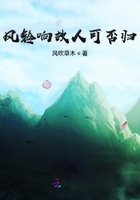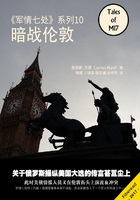在20世纪20年代,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先生开的主要普通课程有: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金刚经之研究、高僧传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识十二论校读等。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讲述西洋各国对于东方学之研究,凡西人关于中国国学之重要著述皆为之介绍及给予评说。演讲此课时,陈先生讲到某国学者及其著述,便使用那个国家之语言讲述。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以教读梵文金刚经为主,并以汉文及藏文译本作比较之研究。陈门弟子姜亮夫回忆清华研究院时说:“寅恪先生讲《金刚经》,他用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来看中国翻译的《金刚经》中的话对不对,譬如‘金刚经’这个名称,到底应该怎样讲法,那种语言是怎么说的,这种语言是怎么讲的,另一种又是怎样,一说就说了近十种。最后他说我们这个翻译某些地方是正确的,某些地方还有出入,某些地方简直是错的。因此寅恪先生的课我最多听懂三分之一(而且包括课后再找有关书来看懂的)。除此以外,我就不懂了。”(见《清华旧影》,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高僧传之研究,以近年中亚考古学、东方语言学所得之材料及研究之结论与中国旧籍互相印证,藉供治中国中古文化史者之参考,是为研究院学生和大学部学生开的共同课。还为北京大学讲授过佛经翻译文学、蒙古源流研究等课。他讲课,广征博引,中西融会,严谨缜密。但学生由于外语所限,听课颇为吃力,有时甚至听不懂。蓝文征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亡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追忆陈寅恪》第86页)陈寅恪先生在教学中经常对学生说:“做论文要有新材料,或新见解,如果材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论文大可不做,做了也没有什么益处。”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又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果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1926年入学的清华大学第二级历史系学生罗香林回忆说:“这句话含有很重要的意义,有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昔年和我讨论陈师的名言,他说这句话给他印象很深刻,影响很大。”(《追忆陈寅恪》第105页)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时写了一篇论文,交给导师赵元任审阅,赵元任阅后批曰:“言有易,言无难!”对导师的教诲,王力“一直铭记在心”。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上,通过课堂讲授、专题指导、言传身教,培养出一代酷爱传统文化、醉心传承国学的名师大家。陈先生的业绩人们将永矢弗谖。陈寅恪先生造就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别的不多举,著名学人季羡林教授不仅出其门下,而且还得到陈先生的扶持。季羡林写道:“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季羡林自传》,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西北历史地理,这是晚清的一门显学,对此陈寅恪先生有论述:“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162—163页)由陈寅恪所论知悉,他研究西北史地是由时势之使然。在史学研究方面,当时因为国势日渐衰落,内忧外患,遂导致具有爱国意识之学人对边疆史地,尤其是西北历史地理的重视,陈寅恪就是其中之一。他从事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是继沈子培和王国维之后而更上一层楼。沈子培是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老朋友,在光绪初年即开始注意蒙古历史地理。沈子培的博学,具有国际声誉,日本学人西木白川、俄国学者楷萨林伯爵、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皆十分重视沈子培。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金明馆丛稿二编》)就是他根据《蒙古源流》的两种蒙文本和满文译本及中文译本互勘、比照、参校,最后考证出了这三个地名。这几种本子是他刚从故宫博物馆发现的,遂进行考证,写出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由于陈寅恪掌握了蒙、满、藏等诸多语文工具,故他可以做到的,其他学人未必能做得到,这就是陈寅恪治西北历史地理高人一头之地方。
中国与印度之间交往为时很早,各国间在文化交流上相互融会、相互贯通。在佛教文学方面,陈寅恪先生指出《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故事,是《大庄严论》中顶生王造草桥抵达楞伽城的故事;这个故事与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猿猴造桥渡海,直抵楞伽城的故事及《贤愚经》中顶生王欲独霸天国同帝释搏斗的故事合并而成。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过莫贺延迹,即古流沙河,逢诸恶鬼,则改编为流沙河遇沙和尚的故事。陈先生指出这个故事其中有荒诞无稽之处,他用《波罗密多心经》比照,指出“梵文对音下所注之中文,意义往往舛,句读离析,亦多未当。”陈寅恪认为传文实际受到《心经》的影响,“若序文中所言观音化身,保卫行途,取经满愿,后复于中天竺摩竭院国那烂陀寺,现身升空等灵异,则皆后来附益演变之神话故事,即唐三藏取经诗话,销释真空宝卷,西游记等书所从出也。”(《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197-193页)这些皆是佛教文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对佛教文学渊源的考辨,还有许多方面,此不赘述。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造诣很深,然而倡导以诗证史,并把它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陈寅恪的确是首开其端。他50年代完成的《元白诗笺证稿》可以说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典范,在中山大学讲授唐代乐府和唐诗证史,曾经非常系统地阐述了以诗证史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关于唐诗的史料价值,陈寅恪首先注意唐诗的作者的广泛性。他说:“唐诗有很多材料,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唐诗有种特性: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黄萱50年代听课记录,收入《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第476页)流传至今的唐诗作者共有两千多人,他们的作品不但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内容,也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思想和生活状况,这是魏晋六朝诗所没有的特点。陈寅恪认为魏晋六朝诗的作者大多属于社会的最高层,因而诗的内容不如唐诗丰富。陈寅恪还列举了唐诗可以证史的几个方面:一、纠正历史上记载的错误;二、说明历史上的真相;三、别备异说;四、相互证发;五、增补阙漏。他认为武宗以后的历史就有很多缺漏,唐诗完全可以增补这种缺漏。例如李德裕死在海南岛,其柩被运回,就可以证明有李商隐的《无题》诗;李、牛两党玩弄权术,其实是两党宦官的争斗。宣宗本是皇太叔,他即位牛党得势,贬李德裕于海南岛,大中三年李德裕死,遂将李柩运回洛阳。宣宗虽不以李党为然,忽然发现李德裕的旧功,所以把李德裕之柩运回。此事从出土的碑文与唐诗可以互相参补。他认为唐诗咏事者甚多,年月事例具体,往往可提供确切的史料,校正史籍记载的讹误。历代所修之正史皆属官书,不免受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思想影响,对皇帝劣迹诸多掩饰,对朝廷和“德高望重”者亦多回护,使后世者不能明了其真相。他说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三个人虽然很友善,但却是政敌,韩愈就被贬过三次,其一是谏迎佛骨;其二是宫市,或云天旱。天旱未能其确解;宫市是说德宗的宦官买东西不给钱,或者是给很少的钱,史书里对于韩退之被贬的原因说得含糊其辞,不知所云,但从韩愈途中寄给王涯的诗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陈寅恪认为唐诗很多皆是纪实的,有些是谣言,不可信;但民间的传说很多却是事实。例如杨贵妃之死,史书与小说、诗,各有不同的说法,各种记载可供考证。一般说杨贵妃之死,皆以为缢死于马嵬,但刘禹锡的《马嵬行》却有“贵人饮金屑,倏忽英暮”句,说杨贵妃吞金而尽。陈寅恪认为此说不一定可靠,大抵唐代流行这个传闻,刘禹锡根据社会上的传闻而作,故《马嵬行》不失为保存异说的诗篇。在陈寅恪开辟的以诗文证史的领域,他还提出应着重考证时、地、人之关系。他认为只有确定时、地、人的关系,史事的真相才能大白。在此方面他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果的探索,《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是逐步完成的,而《柳如是别传》则是一气呵成,首尾相应,可以说是陈寅恪先生史学方法的集大成者。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的第一章“缘起”便写道:“咏红豆并序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始发旧箧,此豆尚存,逐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笺释之者趣及所论之范围云尔。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柳如是别传》上,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月版,第l页)这部巨著的原拟名为《钱柳因缘诗释证稿》,这是陈寅恪在目盲体衰中开始撰写的,继而又伤腿,即失明膑足,以“扶病披寻强不休”的毅力“燃脂瞑写”,终于完成了这部巨制。黄萱在给蒋天枢的信中写道:“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沈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76页)陈寅恪在答老友吴宓的诗中有句云:“老来事业未荒唐。”所指的即是晚岁撰写《柳如是别传》;为此,吴宓在他的日记中也谈及此事:“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必爱陈子龙,即其嫁牧翁,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吴宓与陈寅恪》第145页)《柳如是别传》通过对钱牧斋、柳如是两人的诗文的笺释疏证,具体而有系统地勾勒出明末清初的社会面貌。陈寅恪晚年穷十余年之力,撰著《柳如是别传》这部80多万言的巨著,其中虽有因为自己研治领域与钱牧斋约略近似,诠注钱集“欲自验所学深浅”的因素,更有运用诗文系统地考订一代史事的用意。这部著作虽以钱柳为主体,而明末清初的重大事件,诸如复社事迹,钱谦益投清的背景,郑成功复明的活动等等,本末甚详,且有许多为正史所不载,故亦可视为陈寅恪以诗文证史,自验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著作。陈寅恪认为中土旧诗与西诗最大之不同点,乃在于其大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极大之史料价值,可用于研究历史并补史籍之缺。陈寅恪对各种材料之使用是相当慎重的,在“以诗证史”之先,必先对各种诗的写作背景、素材渊源以及写作意图来一番研究,确定该诗的素材来源的真实可靠性和时间性。再依据当时发生的情况,人与人的交往和每个人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感情,来断定这一资料是否可用。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对中国学界后世影响极大。
关于突厥语在唐代历史文献中的遗存,陈寅恪的研究同样具有开山的示范作用,如他对“纥逻敦”和“唐家子”所作的勘同与考证。自居易在《阴山道》一诗中有“纥逻敦肥水泉好”之句,陈寅恪对此解释道:“纥逻敦一词不易解。疑‘纥逻’为”Kara之译音,即玄黑或青色之义(见RadlOff突厥方言字典贰册壹叁贰页)。‘敦’为Tun之对音简译,即草地之意(见同书叁册壹肆肆拾页)。岂‘纥逻敦’者,青草之义耶?若取‘草尽泉枯马病赢’旬之以草水并举者,与此句相较,似可证成此说也。然欤否欤?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62-263页)
突厥文《阙特勤碑》和《暾欲谷碑》,皆称中国为tabrac,并搭配成下列词组:tabracal(中国朝廷)、tabracbudun(中国百姓)。陈寅恪在校读新、旧唐书时,多次批注这个突厥字是当时俗语“唐家”的对音,《旧唐书》卷一九四和一九五,共有四处“唐家”字样,在《新唐书》中全被删除。对此,陈寅恪先生作出明确判断:“唐家二字,新书删,新书之删去,足征其为当时俗语,与阙特勤碑突厥文合。”(《读书札记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8页)陈寅恪拥有丰富的突厥语知识,但他并不滥用对音。相反,一旦涉及突厥语与汉语的勘同,他总是持之以谨,多方求证,决不轻下断语。在一些考证方面,往往可下断语,但他仍写上“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的批语,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于一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皆是值得永久学习的榜样。
陈寅恪先生一生治学范围十分广泛,在许多学科领域皆做出了后人无法企及之成就;著述亦甚丰,仅2001年至2002年三联书店陆续出版的《陈寅恪集》即达十三种十四巨册,总字数400多万。他晚年整理就绪准备出版的文稿,于文革中全被查抄,新时期拨乱反正后,虽两次收回诗文稿,但仍未全部归还。即便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授课、研究之讲义、资料等,亦未曾得见。总而言之,散落在各处的文字,迄今尚有不少未能获见,这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但从以上谫陋的文字述介中,我们对这位学术巨人也能略知一二了。
鸟瞰当今海内外学术界,“陈学”已成一门显学,它的意义非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当下的文史之学面临许多问题,且不说发扬光大,连能否传下去皆成为问题。当今学界,滥竽充数之教授、学者比比皆是,我们传统的文史之学的确面临极其严峻之考验。在如此之学术环境下,谈谈“陈学”,谈谈先哲之道德文章,实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