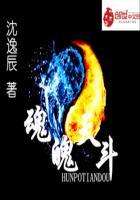康子仑双膝跪地,鲜血从两侧锁骨和左心处缓缓流出,刺进眉心的那截短刃不知何时已被取出,握在手里。此时,他的眼神已不再空洞,脸色也呈现出反常的红润。
“出来吧。”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寂后,从黑暗中走出一位黑衫男子。男子蒙着面,看不清神情,但那双像苍鹰一样的眼眸中散发出凛冽的杀气。
康子仑站了起来,转身面向陌生男子,讥笑道:“连半个时辰都等不了。”
“等一个将死之人毫无意义,我只是好奇......”话未说完,陌生男子突然朝着康子仑奔去,右手一记‘镇岳’拍向眉心,左手‘撼山’,砸向肩头。
康子仑向后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陌生男子并未追击,接着道:“到底是谁教的你这门秘术--献祭?”
康子仑吐出一口血水,神色坦然道:“你觉着我会说吗?”
不会。”
“那你还问?”
“事情没结束之前任何结论都只是假设。”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我还有希望杀掉你。”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盲目的乐观终究会将你吞噬。”
康子仑单手握住残存的剑尖,将握住剑尖的手横放胸前,剑尖朝外,另外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戳向眉心,释怀道:“浮沉数年,终不相欠。”语罢,干瘦的身体向后方倒去,那残存的剑尖却依然停留在空中,仿佛凝滞了一般。
陌生男子朝向那截剑尖走去,走得极慢,男子往前踏出一步那截剑尖就震颤一分,当男子距离那截悬浮在空中的剑尖不足一丈时,剑尖颤若雷鸣,隐有紫光。
就在陌生男子想要再往前踏出一步的时候,三道劲风从后方疾驰而来。
陌生男子弯腰向一侧翻滚,与此同时那截一直被压制的剑尖消失在这虚妄的空间里。
陌生男子半蹲在地上,看了眼地上外圆内方的暗器,朗声道:“夺命阎王既然来了,为何不出来小叙一番?”说着,眼光不经意瞟向赌坊。
“不用看了,赌坊的人已经都死绝了。”说着,从赌坊里走了出来一位黑衣老者。
“生死门的墨月原来只会捡漏,墨月索命,不过尔尔。”
名为墨月的陌生男子桀桀笑道:“杀手不属于江湖,谈不上浪得虚名,我们只不过是完成任务的工具,是杀人的利器。”
不待墨月说完,夺命阎王钱坤,已将手中的纸币射向墨月。
墨月双手持指虎躬身前冲,躲开暗器,想拉近距离。面对钱坤,距离远一分,他活下来的几率就小一分。
钱坤像鬼魅一般往后方飘去,手中的纸币不时射向墨月。
当钱坤退到赌坊旁边,已是退无可退,倘若进了赌坊那狭小的空间,钱坤将毫无优势可言。
墨月看了一眼钱坤,狞笑道:“送你一程。”猛然加速前奔,向前撞去。
钱坤那沧桑的老脸上古井不波,吟诵道:“百代过客去无踪,千金散尽还复来。”毫无章法飞出去的纸币,从墨月后方以更快的速度射了回来,仿佛长了眼睛一般,封住了墨月所有的退路。
墨月嘴角冷笑,面目狰狞道:“且看我破去你的天罡七阵。”双手上的指虎散发着火光,愈打愈快,天罡七阵像洞庭湖的湖面一般,随着墨月的快速出拳,水面已不复先前的平静。狂乱的气息像锋利的剑气,切割着周围的一切,整个空间都扭曲了起来,看着极不真实。
墨月的蒙面黑布早已支离破碎,脸上的血槽也越来越深,手臂也开始往外渗血,套有指虎的左拳可见森森白骨。
半炷香后,墨月猛然跳起,右拳向下猛力砸去,怒吼道:“金刚碎。”湖面破碎,钱坤整个身体向后飞去,撞碎了赌坊的墙壁。
墨月转身看向废墟,冷声道:“砧板鱼肉,任人宰割。”
钱坤从废墟中艰难的站了起来,七窍渗出黑血,惨然笑道:“无心之人说的话可信吗?”
墨月双目暴睁,缓慢低头看了一眼插在左心处的那截剑尖,仰身向后倒去。
---------------------
当朝阳冉冉升起,一抹晨光照耀在东方的天空,黑夜退散,九州的大地又再次恢复了平静,一片祥和。
“咚...咚...”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打破了这难得的平静。
“谁?”
甄真在门外故意压低嗓音,调皮道:“客官可有什么需要?”
中年儒士无奈的打开了房间的木门。
“康叔叔?”
甄三千面无表情道:“他走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他的归处。”
甄真虽然已经猜到了结果,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免有些伤心。
甄三千习惯性地看着窗外,平淡道:“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生老病死皆是人之常情,没必要长吁短叹。”
“道理我懂,但我还是有些难过。”
“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普通人那般寿终正寝。”
“可是.......”
甄三千转过身看向甄真,笑意温暖道:“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平日里待你很好,所以心中不免有些难过。”
甄真眨了眨那双水灵的大眼睛。
甄三千脸上的笑意慢慢消散,冷声道:“你看到的表象未必是真的,相反,真相一般都隐藏在暗处。倘若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刺杀你......”
甄真脸色煞白,沉默半响,不禁痛苦道:“为什么世间人皆要披一张虚伪的面具。”
“最好的面具不过是自己的面皮。”
“死士就一定要绝情吗?”
“在别人眼中他们不过是执行任务的工具,他们早已把自己当作杀人的利器,又何谈感情。好比一把佩剑,佩戴多年,你可能会对它产生感情,但配剑不会。一位不珍惜自己生命的死士又怎么会珍惜别人的生命。”
甄真垂下头,咬了咬嘴唇道:“康叔叔葬身在了哪里?无论如何我想临走前去看一眼。”
“我也不知道。”
甄真歪着脑袋,疑惑地看着甄三千。
“康子仑修习的《沅花剑录》,一共九式。前八式剑法,轻巧灵便,剑剑封喉,只求剑招而不求剑势,是我亲手所教。最后一式剑法反其道而行,只求剑势而不求剑招,名曰《残剑》。比起前八式而言,最一式剑法更具有杀伤力,但是最后一式剑法却并不完美,有瑕疵,这也是我自己也没学最后一式剑法的原因。”
“还有父亲学不会的武学?”
“倒不是学不会,只是《沅花剑录》的第九式剑法一辈子只能用一次。”
甄真张大了嘴巴,惊讶道:“难道是献祭?”
“所以,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了,他走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他的归处。无论事情结果如何,康子仑都不可能再回来了。至于他葬身在何处,我不知道,也毫不关心。”
--------------------
位于兖州闹市的一家酒楼内,一位花甲老者坐在二楼雅间独自饮酒,不时用手抓粒花生丢入嘴中。老者面相平常,举止打扮也中规中矩,眼睛特别小又总是眯着眼,给人一种老人迟暮的感觉。
一位中年木讷男子走进了了雅间,男子身量八尺,面色黝黑,双臂过膝,肩膀显得尤其宽阔。
老人背对着中年男子,并未转头,自顾自道:“人世浮沉如潮起潮落,前些时候还风头无两的血衣侯,这会就茫茫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说着老人往酒杯里丢进一粒花生,抿了一口酒,陶醉道:“冷水寒派出暗影、墨月、忘川、黄泉四大死士,不过是为了还个多年前欠下的人情,至于傅帷是否能活着抵达青州,不是他关心的事情。甄三千出面是哪方势力授意虽不清楚,但他的目的肯定不仅仅是拦截傅帷。趁火打劫,削弱生死门的势力才是他的初衷。步步占先者,必有人挤之;事事争胜者,必有人挫之。这十五年来生死门的发展有些过于风调雨顺了,是时候有人浇盆冷水了。”
中年汉子像一座小山似的,站在老人身后,既不随声附和也不妄下言论,神情木讷,眼神虽不呆滞但也谈不上炯炯有神。
老人依然背对着中年汉子,笑骂道:“你就是块榆木疙瘩,真不知道你长那么大个颗脑袋干什么用,里面都是浆糊。”
中年汉子咧了咧嘴,沉声道:“我只需要记住您交代的任务,其余的一概不想、不问。”
老者眯了眯那双本就不大的眼睛,阴声道:“这才是你应该做的。大智若愚,不过如此。”
又是一阵良久的沉默,期间老者又喝完了一壶佳酿,已有些许醉意。
“人有逆天之时,天无绝人之路。看似必死的棋局往往能绝处逢生。傅帷如今处境微妙,身处多方势力混战的漩涡之中,但实际上他却是最安全的。”
“九州大地,五代十国,王朝总是在分离中走向统一,在繁荣中走向衰亡。每个朝代的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有两件事却是恒古未变的。其一,折戟沉沙,成王败寇。其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大梁如今的局面就像是一潭死水,四方势力相互制约,谁也不敢率先打破这层平静。而傅帷的存在就像是一颗石子,份量虽不大,却刚好能打破这看似平静的水面,掀起涟漪。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有太多的豪门望族、军阀势力、江湖门派需要假借傅帷之手来搅浑这潭清水。所以,现在的傅帷死比活着还要难。”
“二十万南蛮士卒偷袭扬州军镇,无论公良几到底知不知情,他肯定摆脱不了嫌疑,而傅帷正是当时抵抗南蛮军队的主将,为了避嫌,南若聚散厅肯定不会趟这趟浑水。所以,现在的局势就很明了了,生死门是蝉,浮沉殿是螳螂......”
老者不知喝了多少酒,说话含含糊糊,颠三倒是,不一会就趴在了桌子上。
中年汉子一直站立在老者身后,纹丝不动,既不劝酒也不答话,只是在等,不知是等老者醒酒还是等老者下达的命令。
半个时辰后,老者猛然从桌子上惊醒,一脸茫然地望向中年汉子。可能是醉酒的缘故,老者的眼睛显得尤其浑浊。半响,老者那苍老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活着回来,能杀多少杀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