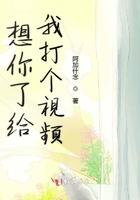“什么?”
安苏看着傅砚川,手里的酒精瓶身生了微微暖意,她一下子疑惑在那里,傅砚川的语气轻的好像自言自语,安苏一时竟不知道傅砚川到底是在同谁讲话。
“没事,没事。”
傅砚川在很久后开口,语气轻缓的不可思议。他的语调在静谧的空间里娓娓传入安苏耳中,竟让她觉得他的话里都是浓浓的叹息,他像是作好了某种决定,又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自我安慰而已。
安苏目光一时停在他的身上,周围都是暖意煦然的光,吊顶琉璃灯洒下的灯线直直的打在他的轮廓上,莫名的失意却也好看的让她一时失了神。
“你先出去吧。”傅砚川而后沉缓开口,语调已经恢复如往昔,冬季的空气里,他的音质像是贴近于若水一般的清冷。
傅砚川伸手将锦被往上拉了一些,又曲着身把身下那人的被子揠了个严实。
安苏回过神,就看见傅砚川站起身来的时候将挽起的衣袖放下,正好盖住了他手臂上那道不小的伤疤。
安苏下意识的皱了眉,她看着傅砚川身姿挺拔往床脚边走,丝毫不在意自己的伤口,“傅先生,您的手....我还是给您包扎一下吧。”
“出去。”
傅砚川径直往外面走,他的语气却算不上好了,脸色也在一瞬间变得克制而压抑。
傅砚川目光望着她,安苏在他深邃而狭长的眼里撞见了一丝不耐烦的情绪,可是很快就消失殆尽了。
她一时间有些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微微呆愣了一会儿才把酒精放回医疗箱内,随后转身准备出去。
傅砚川先出的客房,安苏在他后面紧接着也出了房间,客房门在她的背后缓缓闭合,安苏看着走在前面的傅砚川,房间里灯光的余亮照在他的西装背岭上,咉得他的背影伟岸而高大,气质清冷不沾人间烟火的模样。
作为北城矜贵,傅砚川算是屈指可数的温雅清隽,儒雅一类的人。众人曾这样形容过他,公子明华,如切如磋,安苏起初刚刚见到傅砚川时觉得世人这样评价他,丝毫不为过,他无论是在待人还是接物上,永远都一幅温文尔雅的模样,让人觉得安心而体贴。
可安苏想起刚刚他语气里的隐忍克制却突然觉得世人传闻到底是有些三人成虎,少了些真实性。
或许自己都被他的外貌给骗了吧,因为他也的确生的太过美好,叫人忽视了那个人的真正内心。
安苏离开的时候是在临近傍晚的时候了,她随傅砚川离开客房后,因为傅砚川担心廿十廿长时间不醒,所以她才会又被多留了一会儿在半庭居,其实一会儿也很久,久到她等到廿十廿终于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几个小时后的事了。
不过这期间出了些小插曲,倒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廿十廿还没醒来的时候,安苏见到傅砚川曾接过一个电话,那之前安苏见傅砚川一直有电话进来,可最后都被傅砚川挂断了。
起初,安苏还以为是陌生电话,多次以后,她却看见傅砚川最后接了被挂断又即刻响起的电话,最后神色平静的进了二楼的书房。
电话,是廿博岑打来的。
在临近六点的时候,距离廿十廿醒来不过就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而已。
傅砚川的电话很少有人知道,所以廿博岑打来电话时,傅砚川曾经挂断过两次,只是后来陌生号码一直打进来,他才接了。
至于后来怎么了,安苏是不知道了,因为那时傅砚川去到了书房,等到他再出来时,廿十廿就醒了,而傅砚川也在那时进了客房。
廿十廿醒来的事,安苏是不知道的,她在楼下等到了六点四十五,最后还是从二楼下来的管家华珍告知可以走了才离开的。
等到安苏走到雕花铁门前时,回过头时正好望见二楼落地窗傅砚川的身影,窗纱微微卷开,被卷成很好看的弧度,正好露出傅砚川工笔如画的侧脸,从外面看就像一幅落拓的水墨画,好看的不可思议。
那人脸上缱绻着柔意,是外人不可一见的特列,玻璃上氤氲着雾气,显露他不经意的温柔笑意,安苏不知道那人在笑什么,为何而笑,只是那时她心下砰动,心跳如鼓,又像是心被藤蔓缠住,心跳郁结而慢了下来。
等到小雪飘飘然落下,安苏终是回了头,她敛了神色朝外面走,一步一步消失在路的尽头,终于淡在最后的雪景里。
彼时,二楼客房,温意脉脉。
“你是不是在牛奶里加了东西?”廿十廿没想到自己一觉醒来就是快晚间的时候了,明明她今天早上还准备回廿家去的,可后来她自己都不知到怎么又睡着了,而且这一睡就睡了整整十个小时。
廿十廿从床上坐起,将一旁的软枕捏在手里,满脸的怒意和指控。她只微微一想就忆起早上傅砚川给她喝的牛奶,她长时间的失眠,不可能会睡得这么沉,更何谓还是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
“傅先生,我不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但我真的要回去了,麻烦你出去,我要换衣服。”廿十廿看着站在她面前的男人,手心越发用力,她冲着男人说,语气急切而气恼。
傅砚川望着她,嘴角却挂上了笑,是很显而易见的弧度。
床上刚刚睡醒的人,脸上还带着熟透的醺红,明明说着最气人的话,可她现在的模样,用手悄悄揪着怀里的软枕,可爱的像一个糯米团子,着实让人生不起气来。
“请你出去!”她一字一句的说,面色染上愠怒,可语调却因刚睡醒而软糯得不可思议,她喊他离开,那人却还在笑,好不气人。
“出去!”可廿十廿面前这个男人却纹丝不动,这叫她愈发觉得气恼,廿十廿将软枕撒手一放,作势就要掀开被子起来,可还没等她把脚放下来,傅砚川就先她一步蹲了下来:“生气归生气,要把鞋穿好。”
傅砚川替她穿好鞋,抬头对上廿十廿的眼,笑意仍在:“你看,今天太晚了,我们明天再回去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