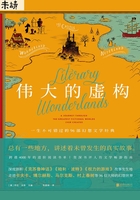在梦里,那个村庄又出现了,随着次数的增多,它的轮廓由模糊而清晰,由凌乱而变得有层次了。我在努力想它的存在和来历?
于是我想起与我的血脉相关联的那个村庄。那个名叫郝洞的村子(听起好像是韩国的地名)正是我的故乡。郝洞的“郝”发音很特别,当地人管“郝hao”说成“郝ha”,用太原话,则为“he”,这样的发声界定了晋中一带方言发音上的差异,邻近县的方言怎么念,我不大清楚,按普通话的发音该是念“(郝)hao”。
毫无疑问,这个名叫郝洞的地方是我在履历表上填写过无数次的祖藉,它就在距省城太原不远的平遥县,平遥是一座历史名城,不过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它也只是个地名而已。
我第一次回到故乡是在六二年放暑假,父亲带了我回老家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乘火车,火车还是那种原始的蒸气机车,开动起来“哐哐哐”的,响动很大,在火车上父亲买了一样食品,即“太谷饼”,那糕点的样式很古朴,吃着有些发甜。我们从一个叫洪善的小站下车,跨过铁道一路往东,沿着乡间小路走了大约二三里的样子,那个被称为老家的村庄出现了,它和我在梦里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进村后,一路上有人跟父亲打招呼,看来父亲在村里的人缘不错。走进我家的老宅,先看到是门前那棵老槐树,院子里的老宅、枣树和井台都一一呈现……天黑时,屋里点起了煤油灯,油灯如豆,悠悠的散发出一股油腥味儿,我躺在土炕上闻着那浓浓的乡间气味,当时我清楚的意识到,这就是我的老家了。第二天起来在院子里我看到空地上的那几十棵枣树,树下的空处栽种着一些瓜豆之类的作物。父亲说这院子久未有人住了,平时靠一远房亲戚过来打理,秋天收下的枣儿什么的就算是给人家的报酬了。我想,秋天时,枣树上会结满了玛瑙一样的红枣,绿树上颗颗诱人的红枣,放在嘴里会是很脆很甜的;院子里还有一眼水井,井台由青石垒成,井边还架着陈旧的辘轳……我想,这么大的院子里总该养些鸡鸭或羊什么的,至少也该喂两头猪吧,然而,没有,那院子因没有家禽之类的活物存在而显得有些冷清。
第二次回郝洞是在六八年的夏天,那年我已长到十六岁,算得上小伙子了。那次是和母亲一道回去的,当时我们回乡的目地只有一个,就是想找村里的亲戚们帮着给买小麦以添补家用。那一年的年景不错,却赶上文革动荡,平遥城里的两派搞武斗,动枪动炮的,人们谈及心里不免惊慌,出门办事都很小心。回到村里时天色已晚,就在一同姓大姐家吃了饭并住在她家里,那屋子里新盖的瓦房,炕却是砖砌的土炕,炕上铺着一大块绿色的油布,倚墙摆一溜大红色的炕柜,一看就是平常农家。
听母亲说明来意,那位姐夫就连夜出去张罗着买回两百来斤新收的麦子,第二天没事,就顺便去看望了那位本家亲戚润爷,润爷身体硬郎,他专门把家里的白面拿出来,烧了葱花烙饼让我们吃。下午正好有辆山西机床厂的卡车在村里办事,就去跟人家商量,请求帮着把二百斤小麦捎回太原。对方竟爽快答应,条件不过是给司机塞了两盒香烟而已……
那次回乡后我才知道村里还有一座很大的寺庙(当时也没问一下这庙叫什么名字),在一亲戚的陪伴下,管事的特许我们进庙里去转了一圈(用现时的话说叫“参观”),由于文革的关系,那庙宇是被封着的,因属封资修的东西,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时有人企图冲击这个寺院,被村里的族人给拦住了,从此庙门贴上封条,任何人都不许进去。那寺院后来就成了生产队的库房。我们进去参观时见大殿里面堆满了杂物和粮食。那位管库的亲戚向我们介绍了庙里的佛、菩萨、金刚等塑像,还有墙上精彩的壁画,由于匆忙,当时并没把它们的历史价值放在心上,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家郝洞村还拥有一座著名的庙宇,它居然是隋唐后五代的珍贵文物。
经查阅资料得知:平遥郝洞镇国寺,原名京城寺,创建于五代时北汉天会七年(公元963年)。京城寺的寺名,到明代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被“镇国寺”所取代。明、清时,寺庙倾颓,清代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才重修万佛殿,重修后的殿宇,仍保持了原来的风格。前院居中者为万佛殿。这座殿宇造型独特,平面近正方形,屋顶为单檐歇山式,出檐深远,庞大的七辅作斗拱,总高超过了柱高的2/3,使殿顶形如伞状,在历代寺庙建筑中颇为罕见。此殿,始建于五代,殿貌奇古,结构奇特,从建筑的艺术上别具一格,是国内现存五代时唯一的木构建筑……
面对这样珍贵的文字记载,我心中除了自豪便是深深的愧疚了。
也许是一种感应吧,每当父亲的村庄在眼前渐渐清晰,我心中便涌动着一股异样的情感,我的祖藉有座闻名天下的镇国寺,在历经一千多年风雨苍桑的今天,依然如故,1988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而多年来由于我的失敬和慢怠,居然这么多年都远远地离开它,每想到这些,就深感沉重,我想,不管我承认与否,在我的血脉里流淌着一千多年以前生活在这儿的祖先们的传承。
原载于2011年3月4日《太原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