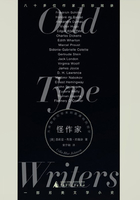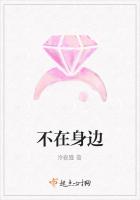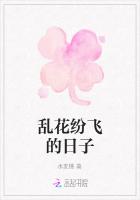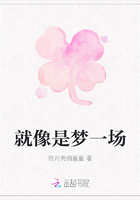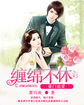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期间,于授课之余,并对研究生作专题研究时进行个别指导。门人姚名达在《哀余断忆》中追忆王国维指导他研究《史记》之经过。姚名达追忆道,在王国维将要跨入五十岁的时候,他欲研究《史记》,遇到一些学术问题,到王国维家晋谒求教。王国维悉心指导,并授予自己毕生学术研究之所得,共讲了两种研究方法:“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目,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并勉励姚氏以读《诗》、《礼》,厚根柢,勿为空疏之学。(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498页)由此可知,王国维对学生之指点是非常精到而又具体。其一是可用寻源工夫,比照磨勘;二是可以漫无目的地精读,等有心得时,再自拟题目,做研究,撰写论文。关于第二种研究方法,王国维认为,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想不到之创获。说是不悬目的,而又慢慢努力;这个努力不就是为着达到某种目的而才去努力的吗?故人生之大目的、大志向还是要有的,否则,如何去努力呢,如何去精读下去呢?但又不可抱定某一目的或某一大志非要弄出个金娃娃来不可。事情的结果往往是想弄的弄不出来,不想弄的却反而出来了。此即不悬目的而目的自生,乃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也。当然,有心栽花,花未必不开,无心插柳,柳亦未必成萌。王氏早就有言在先矣,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先要独上高楼一立大志。王氏此前后两种说法,当不矛盾。王氏教弟子做学问之办法,本身即是情操之陶冶,性情之历练,意志之磨砺。对王国维来讲,他的学术活动,就是生命活动;如果不做学问,则无异于生命活动之停止。这是很高的境界。不久,王国维又写了一篇文字,足见其人生———学术境界。蒋盂50岁时,王国维撰《寿序》赠之。这一年,蒋氏很倒霉,生意做砸了,藏书抵押殆尽。王国维在《寿序》中以示大寿大贺,安慰老友。文中说:“余家无书,辄假诸居士,虽余椠明钞,专一力取之,俄顷而至。癸亥春,居士编其藏书目既成,又为余校刊《观堂集林》,未就,而余奉入直南斋之命。居士颇庄余行,余甚感居士意,而义不可辞,遂夙驾北上,逾年而遭甲子十月十日之变,自冬徂春,艰难困辱,仅而不死,而居士亦以贸迁折阅,至乙、丙间,遂亡其书。余在海上时,视居士之书犹外府也。闻其书亡,为之不怡者累日。顾苦无语以慰居士。……盖往而必复者,天之道也,困而后作者,人之情也。自宋以来,吾浙藏书家以湖州为最盛,然其聚散亦屡矣,居士之先世亦曾亡其书矣,居士勤勤搜讨,二十年问,蔚为大家,有光前人,故余曩为居士作《传书堂记》,谓石林直斋之书,久为煨烬,而今有张、刘诸家;茹古精舍求是斋之书,十不存一,而今有居士;盖一乡一家之遗泽,虽百世而未有艾也。今居士之书虽亡,而嗜书之心未衰,又嗜书之人继居士而起者,固已崭然见头角矣。然则居士他日之所获,安知不倍蓰于今之所亡。如密韵楼之于茹古精舍者乎?爰书是以寿居士,并以为之券,居士闻是言,其莞尔而尽一觞乎?”(《观堂遗墨》卷上,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478-479页)应该说,此篇《寿序》写得十分深情练达,并非客套,更不像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之临终诉说;而且显得格外平静,叙述幽缓,似乎是在调适自己那颗动荡不安的心,慰藉震颤不已的灵魂。他之所谓“盖往而必复者,天之道也,困而后作者,人之情也”之喟叹叹,是否即是“知天命之言”之流露?先不赘言,但对缓解跳动不已之心,唤起人之精神,的确很有用。悲观亦非纯粹之悲观;因为悲观里仍含有希望之情愫,恐怕这悲观与希望是并存的也很难说,否则为何这悲观不悲,绝望不绝呢?也许,王国维真是到了“知天命”之关头,悲观也好,绝望也罢,一切皆由不得自己,只有“听天由命”吧。当友人蒋孟经商之时,还是1924年9月,王氏去信安慰说:“委心任运,不动天君,是处困第一善法,亮兄必能得此诀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3—404页)俗语言:圣人知天命不可违,因而制之。果能如此,悲观主义辄可休矣。学问之道,用于人生复能如何?王氏谈学问之道,直言无目的精读,常不悬目而目的自生,有大志者未必成功,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既知此道复行之,当可安身立命矣。以学问为生命,以学问之道,作为安抚灵魂之道,当属自然。但王国维最后的岁月里,安身立命之道日渐不灵,震颤之灵魂更加颤抖不已;无论你开出任何灵丹妙药之方,皆无济于事。是的,人在困中是很难受的,尤其是灵魂受到折磨的时候,任何道理亦无补于事。
王国维之精神打击即要降临了。
四、最大的精神打击
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之子王潜明在上海去世了。得的是伤寒症,享年只有28岁。堂堂男子,风华正茂。王国维在北平闻讯儿子病危,立即偕夫人乘车南下,到上海时,潜明既病人膏肓,无可救药矣。死时,遗孀罗曼华年仅24岁。罗振玉在天津听到噩耗,亦前来沪上料理丧事。办完后,带着女儿罗曼华先回天津了。此事令王国维很懊恼。10月15日,王国维启程返京,两天后抵京。复过一周,遂致罗振玉一信,痛心地诉说了家变。王国维说:
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媛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媛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六]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为感激也。此次北上旅费,数月后再当奉还。令媛零用,亦请暂垫。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43~444页)
王国维与罗振玉自1898年结交,即相伴相偕,共历三十载之久,是中国近代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有成就的少数学者中的两位,他们共同创立的“罗王之学”,取得了令世人惊奇之卓越成果。罗在学术上识断过人,精力旺盛,多有开创之功;而王则承继其后,展开精湛深邃之研究,将诸多学科推进到更高的水平。罗振玉王国维两人之终生交往,优长互补,为他们空前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之基础。罗之女乃王之媳,二人又是亲家,朋友加亲戚,同志加兄弟,至此将要酿成分手之悲剧。此悲剧种子可能早已种下,政见不和当属其中之一。丧事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抵触,尚不可知,但罗氏将女儿领走,王氏肯定不高兴。当然,从情理上讲,罗氏领走女儿固无不可,做父母的怎能不心疼女儿。也许是没打招呼,或许没有商量好。但从上引王氏致罗氏信可知,罗王两家因儿女细故而生误会,以致王氏在沪处理丧事后北返途中过津,亦未能实现亲家聚首。王氏在信中还告知已将亡儿的包括抚恤金在内之全部遗款共洋银三千元全部汇至罗家,“求公代为令媛经理”,“亡男在地下当为感激也”。但王国维此函甫发,即于10月25日接到罗振玉之手书,其中有“虽已遵来示告小女,而小女屡次声明不用一钱”(《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659页)之语,王国维颇为恼火,当即复信:
令媛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媛,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媛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者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44-445页)
时局变化非常之快,俾王氏心情很是不好,加上丧子之痛,处事急躁或过火一点,乃人之常情;而罗振玉亦心情不佳,本身亦有头昏头痛之病。王国维早在一个半月前给神田喜一郎的信中即谈到此点,说罗氏“意兴不如前日,亦时有头痛头昏之病,殊可念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42页)两个人皆在心情欠佳之时,来这么一件丧事,打击当然不轻,罗氏情急之下带走女儿,王氏顿时不解,心急火燎,亦当属情理之中也。那么王国维为何要把儿子遗款汇给罗氏呢?要是换了别人可能不这样,你既然把女儿领走,那我即把钱扣下。可王氏偏偏不这样,你既然把女儿亦领走了,干脆连钱款亦一并拿走,了个干干净净。可见罗王闹矛盾,亦大有君子之风度,但罗振玉仍是不收。王国维更加火冒三丈,于10月31日再致信罗振玉:
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媛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期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期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45页)
先哲就是先哲,连闹别扭亦与常人有天壤之别。他们之间之争,往往不是为着钱财去争,更不是为着名誉去争,而是为人格去争,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在王国维的“人格”面前,罗振玉终于有所让步。11月11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说:
奉手书敬悉,亦拳拳以旧谊为言,甚善甚善。弟平日作书下逾百字,赋性简拙,从不与人争是非,矧在今日尚有是非可言耶?以来书严峻,故尔云云,殊非我心所欲也。此款既由弟代管,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异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662页)
12月2日,罗氏再次致辞信王氏,对二人之情谊与失和之原因,谈出个人之见。信说:
弟与公交垂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知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至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妇所能,与尊见恰得其反。(《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866页)
很明显,罗振玉对王国维抱有某种埋怨之情绪,由此而对王氏进一步产生了偏见。“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罗氏亦未做到,何以要求王氏去做呢?亦由此,罗王数十年之往来通信至此而绝。
儿子不幸病逝,儿媳不辞而别,复失去多年好友,雪上加霜,何以受得了。王国维最难熬的日子来了。
五、最后的岁月
1927年,王国维既进入5l岁。这是他最后之岁月。门人姚名达追忆说:“12月3日,即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实为先生五秩初度之辰,先生方以理长子丧事自南归未久,同人展拜于堂,未暇有以娱先生,仅倩贵阳姚茫父绘画为寿。又七日,先生招同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本相示,同人啧啧嗟赏,竞提问语,先生辩答如流,欣悦异昔,始知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也。自是吾院师生,屡有宴会,先生无不与。”(《哀余断忆》,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97页)五十而知天命,王国维的确显出一些豁达的样子;是以会友、赏画、宴请来排遗心中之郁闷,大有借酒消愁之味道。大概王国维此时或许看清了很多问题,故才显得有些潇洒。
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载,1927年2月15日,溥仪在天津张园做寿,王国维前往“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喀血之症。”(转引自《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686页)当天,罗振玉亦赴园拜寿,二人相视而过,既未接谈,亦未寒暄。北伐军节节胜利,引起北方各界人士之不安。清华园中亦激起反响,粱启超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中写出了自之不安:“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3、1122页)即凭王国维之敏感,他对时局之体验一定不比梁启超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两人的感觉亦会一样。尽管两人之政治观点有差异,但他们所处之环境、社会地位与学术声望几乎是一样的。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亦记载道:“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其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70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5-1146页)此即王国维当时之心态。时局虽俾王国维焦躁不安,但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并未终止,一如既往。1月,撰《周之琦鹤塔铭手迹跋》,后收入《观堂别集》卷三;2月,与日本友人藤田丰八通信讨论“字之音读问题和《鞑靼考》中之问题;3月,撰《金长城考》,后改为《金界壕考》,跋校《水经注笺》;4月,翻译日本箭内亘《鞑鞑考》、津田左右吉《辽代乌古敌烈考》及《室韦考》;5月,改汀蒙古上世考———辽金时蒙古考———为萌古考,撰《蒙古札记》、《尚书诂序》,等等。此亦可足见王国维心态之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