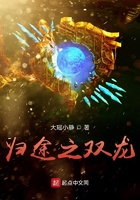小乔猛然睁开双眼,右眼黄金瞳缓缓渗出金黄色的血液,“烂斧柯,王积薪便是当年的王质,那施叔便是当年的那名稚童。”说着,转身看向站在一旁的施襄夏。
此时的施襄夏,早已变了模样,正是当年那名身量中等、洒脱不羁的男子,只是岁月未曾在其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迹。倘若非要说岁月的沉淀到底在哪里,那便是那双仿若看透世间万物的双眼,是那样的通透清澈。
施襄夏轻轻一笑,朝身边的人一一点头之后才开口道:“我不是当年那名稚童,王积薪也不是王质,我只是我,施襄夏。而他,也只是王积薪,那个在不知名的小渔村长大的王积薪。”
王积薪此时也从混沌中醒来,只是眼角泪痕尚未干涸,站起身朝门外走去,“因果循环,你我二人也算是两不相欠。至于傅公子,权当王某人从未来过便可。”
傅帷一脸惊愕,这一切的变化,似乎有些过于迅速,也有些...莫名其妙。因为王积薪的内心世界,除了小乔,其余人一概不知。
傅帷看向小乔,而小乔并没有任何动作,只是怔怔地看向施襄夏。
施襄夏点了点头,“缘起、缘灭就是这般迅速,四十年,也不过是一个晃神。今日你我缘分既然已断,以后便再无任何牵扯。”
玩世不恭的人皮下面,都有一个无处安放的灵魂。沉沦的俗世并不是真正的炼狱,空虚的内心才是无尽的深渊。
待王积薪走后,白朴悄然走进了房间,轻轻关上了房门,身上的气质也是陡然一变。气势虽不胜,但是内敛的光芒却是所有人都不能比拟的。霸道如熏黛,此时气机竟也有些紊乱。傅帷更不用说,面无血色。
施襄夏看向白朴,点头笑道:“好久未见。”说着右手轻轻搭在小乔的肩膀上,小乔并未言语,只是轻轻擦了擦从嘴角渗出的鲜血。
白朴没有答话,只是站在傅帷身后二尺的位置,不动如山。
傅帷心里渐渐有些不安,而熏黛也是一脸的沉重。
小乔抬头看向傅帷,虚弱地点了点头,示意傅帷放心。
突然,门口又出现了两个身影。
施襄夏看向门外,依旧是笑意温润,“齐兄既然来了,又何必如此小气,何不现身一见?”
门被轻轻推开,齐石缓缓走了进来,只是手中并没有折扇,有的只是一支淡金色的画笔,而画笔的笔尖未染笔墨。
“一别数载,却仍记得我齐石,劳烦施兄费心了,愧不敢当,愧不敢当。”说着,双手抱拳朝施襄夏拱了拱手。
傅帷将目光瞟向门外,一个双手环胸站立在门口的身影除了墨竹还能有谁,这局面,的确让人吃惊。
一直缄默不语的小乔突然开口道:“既然施叔不是那名道童,王积薪也不是当年的王质,那施叔到底是谁?”
“很重要吗?”
“本来不重要,只是因为这件事情,瞎了我一只右眼,总得知道到底是为了谁吧?”
施襄夏缓缓坐到了小乔的对面,通透清澈的双眼看向小乔的右眼。小乔的黄金瞳随着金色血液的流出,变得越来越淡。
“闭上左眼,用你的黄金瞳看向我。”
小乔缓缓闭上左眼,右眼依旧是血流不止。
“看得见吗?”
“看不见。”
“听得见吗?”
“当然。”
“好,不要闭上黄金瞳。”说罢,施襄夏转身看向齐石,“齐兄,且借画笔一用。”
齐石有些犹豫,不过还是将金黄色的画笔掷给施襄夏。
施襄夏接过画笔便迅速在桌子上写下四个大字,只是画笔并未沾染墨汁,桌上也没留下任何痕迹。紧接着,施襄夏将画笔抛向齐石,双手飞速结印,吐出一口淡金色气息,四个金色的印记在桌面上一闪而逝,化作一缕缕的气机,卷入小乔的黄金瞳之中。
当最后一缕气机消失,小乔也昏迷了过去,只是黄金之瞳依旧张开,光芒璀璨。
“八世轮回?”
施襄夏一脸惊讶地转头看向傅帷。
此时的傅帷不知何时已经将左眼的眼罩取下,露出和小乔黄金瞳十分相似的左眼,但若仔细观察还是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
施襄夏很快便从适才的震惊中缓过神来,轻笑道:“原来傅公子也是黄金之瞳。”
“这四个字代表着什么?”
“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离别、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每一苦,便是一世,谓曰八世轮回。”
“她会怎样?”
“不好说。”
“哦?”
突然施襄夏爽朗笑道:“怪不得适才总觉着小乔说话怪怪的,一反常态,原来是小乔一直在窥探你的心思,替你而言。”
“一心不侍二主,这是她应该做的。”
“应不应该都是她的事情,与我无关。只是小乔完全凭借本能,这般过度地使用黄金瞳,很难不被反噬。不过,这件事情毕竟因我而起,我也不能袖手旁观,所以送予她四个字,至于结果会怎样,是好是坏,就看她的造化了。”
施襄夏说完,环顾了一下四周,虽不至于剑拔弩张,但是氛围的确是有些莫名的紧张,不由笑道:“门口那位也进来吧。大梦春秋,一梦十年。浑浑噩噩了十年之久,还不至于一清醒便打打杀杀,尚未到达如此丧心病狂的境界。”
门口的墨竹依旧未有任何动作,施襄夏也不觉尴尬只是将昏迷的小乔放到一边,坐在了小乔的位置上。
“诸位真心不必如此,毕竟吃了白夜行十年的口粮,怎么说也有十年的情分。”
傅帷没有理会施襄夏的插科打诨,开门见山道:“你是施襄夏,那原来的那位施襄夏又是谁?”
“原本便是一个人,又何有我他之分?”
“无论多高明的易容术,能易其容,却独难易其神。”
施襄夏看向熏黛,“劳烦熏姨拿一壶好酒。不,拿一坛。往事就酒,越聊越有。”
熏黛出奇地没有动手,只是转身朝门外的墨竹喊道,“劳驾了。”熏黛终究还是不放心。
待不多时,施襄夏品了一口陈年老酒,咂摸咂嘴,“上次喝到如此佳酿,还是在十年之前,我十年前便是这幅面容。”
“是吗?”
“傅公子倘若不信可以询问白朴、齐石,毕竟当年他们俩也都在场。”
傅帷笑容玩味地看了白朴、齐石一眼,“不知当时是在何地?”
“傅公子应该也曾去过那个地方,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彭城第一楼。”
“明月楼?”
“对,当时可不止齐石、白朴在场,鬼手刀何陌也在场,白夜行三十二天罡来了十七位,其余死士谍子更是不计其数,声势不所谓不浩大。当然,他们也只能站在一旁,真正能与我对饮的也只有明月楼的掌柜一人而已。”
“声势的确不小,只是不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施襄夏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右手轻轻拍在桌子上,颇有说书先生的气势,“十年之前,因为一些俗事坏了道心。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彭城便遇到了宫六。谁曾想,贪杯一时欢,归来时,已是数年。”
“以你的修为,不应如此。”
“你又怎知我的修为如何?”
傅帷看了看旁边昏迷的小乔,“小乔适才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烂斧柯,王积薪便是当年的王质,而你则是当年的那名道童’。虽然不知道小乔通过王积薪看到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一点,你几十年前应该就是这幅面容了,甚至更久。任昉的《述异记》中记载过烂斧柯的典故,已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施襄夏唏嘘一声,“当年我若是执意想走,也不无可能。只是,有些时候,被动的逃避会让人感到心安理得。况且,就算我能走出明月楼,又能如何?”说着,施襄夏又看了一眼齐石和白朴,自我宽慰道:“当时的情况,也不能算是逃避,毕竟宫六的心思太过缜密了,百密而无一疏。”
“哦?我倒是很好奇宫先生到底做了什么,能让你如此左右为难?”
“倘若单论布局,十年前的宫六,无人能出其右。至于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以后你就会慢慢知道了。非是我卖关子,只是我看到的都是他想让我看到的。这句话对你而言,依然如此。当然,此番非是挑拨离间之计,我施某人,还不至于此。”
“可是,凡人皆有一死,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施襄夏眯眼看向傅帷,揶揄道:“你不必试探我,小乔看到的东西很多,等她醒来即使你不想知道都难。”
“你刚才也说过,小乔最后会怎样,连你都不知晓。倘若她一睡不醒,又当如何?”
“想得太多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
傅帷喝了口酒,叹气道:“我也不愿这般市侩,只是从头到尾,我都不知情。这也就罢了,偏偏宫先生又让这些人站在我的身后。无论是为了自己也好,为了不辜负宫先生的期望也罢,都不得不为之。”
施襄夏缓缓转动着酒杯,“你信命运、缘分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吗?”
“不信,便是子虚乌有。信,便不是子虚乌有。”
“废话。”
“你既然问了,这便是我的回答。”
“很有禅理,既然傅公子如此有慧根,何不随我回武当山,闲云野鹤,逍遥自在?”
“武当山的莲花峰,他日一定登门拜访。”
“十年前,宫六也说过这般话。”
“我想宫先生也有他的难处。”
“的确,他是为了今天。”
“倘若不是白朴、齐石、墨竹的出现,我的确相信今日之事,只是巧合。”
“这便是命运。”
“可是,倘若在青州的叹春院未曾遇见小乔,亦或者小乔未曾随行,又当如何?”
“这便是缘分。”
“宫先生应该不信这些。”
“不准确,他自己的确不信,但是,他相信别人信。”
傅帷轻笑道:“很是狡猾。”
“对于乡野村夫来说,这便是狡诈。可读书人的事怎么能说狡诈呢?这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宫六只是太聪明了。”
“如此聪明的人,怎能把成败的关键交付于一个不确定的人身上呢?”
施襄夏笑骂道:“非得要我亲自说出来才肯罢休?”
“愿闻其详。”
“十年前,齐石能逼我自闭一窍。那十年后的今天,齐石便能解开那一窍。”
傅帷有些不解,“既然如此,又何须这般麻烦?”
“因为宫六知道我信宿命。”
“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能与人言一二三,幸也。”
施襄夏擦了擦嘴角的酒渍,轻笑道:“宫六真的不是你的师父?你与宫六皆是这般,明明是自己求别人,但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自己吃亏了一般。”
“亦师亦父。”
“得了便宜还卖乖。”
“总不能得了便宜还哭吧?”
“是这个理。”
“那我委屈几分,且听你言。”
施襄夏认真道:“傅公子为我之事,亲自走了一趟烂斧柯,请来了王积薪,解了我一桩心结,这便是我施某人欠了你一份人情。至于小乔,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终归是因为此事而遭此劫难,我自然不会放任不管。至于我所说的小乔最后的结果如何,全凭她造化,非是我故弄玄虚,只是我能给她的只是一份契机,我不是她,自是无法左右她的选择。但是,无论她的选择为何,都无性命之忧。百年一回首,回首便是一世。一世缘,一世了。”
傅帷狡黠地摸了摸下巴,“简而言之便是你欠了我傅帷一份人情,而且这份人情你还一定会还。”
施襄夏一副明知上当还坦然受死的样子,“道不同不同为谋。”
傅帷收起狡黠的表情,站起身敬了施襄夏一杯酒,“且敬你以德报德。”
施襄夏并未起身,只是看着傅帷将杯中酒饮尽,静待下文。
“不知以何报怨?”
“傅公子觉着呢?”
“古书云云,君子以德报德,以德报怨。只是,我不是你,无从探知。”
“你又会如何?”
“我只知道我不是君子。”
施襄夏眼睛闪过一道精光,“巧了,我也不是。”
傅帷凝眉沉思,不知在想些什么。
半响,傅帷突然开口问道:“不知施襄夏这一世还有多少年?”
“哦?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百年一回首,回首便是一世,这是你说过的。”
施襄夏点了点头,不得不承认,年方二十四的傅帷的确有其过人之处,“还有十年。”
“既然一世缘,一世了。那我便帮你了却这个心愿,十年内,不对宫先生动手,这个人情还算是好还吧?”
“的确,只是这般不白白枉费宫六这十年的布局?”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施襄夏眯眼道:“宫六只需要好生堤防我便可了,而我还是会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还你一份人情。”
“的确很诱人。”
“你不心动?”
“心动。”
“那又为何这般妇人之仁?”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汉子。”
“堂堂血衣侯?”
“区区血衣侯。”
“孺子不可教,粪土之墙不可污也。”
“绝大多数人不具有改变局势的实力,所以才需要学会去适应,我也不例外。可是,无论如何去随波逐流,如何去放逐本心,终究有些东西,坚若磐石。”
“宫六对你真的这般重要吗?”
“宫先生不仅是宫先生。”说着,傅帷朝地上敬了第二杯酒,“宫先生身上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倘若精气神散了,有再多人也是枉然。”
“亦友亦师,亦师亦父。且不论宫六这一辈子还有多长,但凭你父子二人,值了。”
傅帷第三次敬酒,只不过这次既没有敬施襄夏,也没有敬六尺之下的亡魂,只是将酒杯举过头顶,“且敬明天。”
“或许,会更好。”
傅帷朝身后挥了挥手,“普陀山的无禅和尚曾经说过,‘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信。十年之后,倘若我还活着,而你也不再是施襄夏,但愿你我还能相遇。”
“那将不是一场重逢。”
“对,那是一场相遇。”